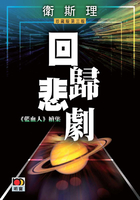有人说剧本是为舞台演出或者电影、电视剧拍摄而写的,不是写来阅读的,算不上纯粹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写剧本的作家很难或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一流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剧本是为演出或者拍摄而写的这是对的,但剧本如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形式的一种;既然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便有可阅读性。老实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包括郭沫若、曹禺、老舍的剧作我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从舞台或者银幕、屏幕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书本上的的剧作打动了我,激励了我,启发和提高了我,怎么能说剧本只是写来演出而不是写给人们阅读的呢?至于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是否能够进入一流行列,更是与他们熟悉和使用的文学形式无关。有谁能够说,凡是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有谁能够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郭沫若、曹禺、老舍,不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一部《红楼梦》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窦娥冤》同样使关汉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诗垒起的,也是用新编历史剧垒起的。老舍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闻名中外,也因《茶馆》而中外闻名。所以,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需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有人觉得自己是写小说或者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作品可以不读。我不这么认为。写剧本必须多读好剧本,但多读好剧本的结果就远不局限于剧本写作本身了。我的小说甚至于包括报告文学、散文之类作品,都特别注重可读性,特别注重情节、情绪、气氛甚至于语言的起伏跌宕,不能说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影响无关。剧本强调悬念和情节,强调性格的鲜明性、复杂性、微妙性,强调“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在小说创作中同样重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种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说,离开这些戏剧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张小说要返朴归真,但返朴归真并不等于平实、寡淡,并不等于与戏剧性相互抵牾,并不等于不能够在融会贯通中放射出新的光彩。是不是呢?
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给予我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当属雨果了。而雨果打动和影响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和生动性。我曾经说过,有的作品刚读时感觉不错,但读过之后很快就模糊甚至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作品读过之后,给予你的是震撼,能够一下子烙进你的心扉,即使多少年之后也还会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谓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这与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与作品具有不具有戏剧性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点好剧本,受一点好剧本的影响,无论对于写什么作品都是有益的。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得之见。
有人问,有的作家一辈子固守一种文学形式,比方只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等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我对这种说法,即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主要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或者只在某一种文学形式中成就比较突出,但一辈子仅仅固守于一种文学形式,对其他文学形式不感兴趣或者完全没有涉猎的作家,起码是我没有听说过。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过是一道矮矮的篱巴墙,抬抬脚就可以过去。剧本的那道篱巴墙即使高点、厚点,也不是绝对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亚的剧作闻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诗同样流传久远。托尔斯泰以小说著称于世,但也写过剧本。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精彩动人,他的《墙头记》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人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兼备剧本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倒是许多大家共有的特点。当然作家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爱好,切不可用一个标准要求和评判;只要是好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值得赞赏和鼓励。
这里要说到“触电”了,而一说到“触电”有人就难免心惊肉跳。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对“触电”我是既怕又不怕。二十几年前,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怕的概念。可眼看被列入拍摄计划的剧本,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拍摄计划中“开除”出去,那“怕”便不请自来了:那是将近两年的心血呢!正是由于怕,由于要避开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我毅然退回八百多年,写起了《岳飞》。可没有想到《岳飞》写好,并且受到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和诸多电影界前辈的好评,却又由于经费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被迫搁浅。后来剧本虽然发表,却越发让人怕起来。而这一怕就是许多年,《骚动之秋》和几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后来写《原野风》完全是为了配合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剧本得奖了,小说出版并且受到了好评,电视剧、电影却被拍得走了样儿……如此反复,说不怕肯定是假话。可从1994年起,几位朋友和领导多次请我出山,我婉拒过、抵抗过,却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操旧业。好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现在我只是把剧本当作文学作品来写,至于拍不拍、怎么拍、拍到什么程度,因为说了不算、想也没用,干脆就不去说不去想了。这就是所谓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有人把今天的时代说成是电视传媒的时代,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权且不论,但确是说出了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一名作家完全顺应时代难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为也难。电视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广阔的前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视,或者因为怕,远远地躲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成一时之盛,其创作成就和水平之所以形成高峰,与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发展,与作家的集体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觉得,电视剧本的创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时代和社会推上了前台,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并且付出自己的那份艰辛与努力,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就完成可能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电视剧发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至于说到以后,我是以创作剧本为主还是以写小说、诗歌、散文为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即便是且恨且爱的剧本也是如此。
附记:这是作者为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和《黄河之水天上来》所写的后记。
新松恨不高千尺
新年伊始,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又收到了荒煤同志的信,望着他那熟悉俊逸的笔迹,我心如潮涌,感慨万端。作为著名前辈作家和文艺界领导人,荒煤同志在这次作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位普通的青年作者。
1978年我在部队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上下集的电影文学剧本《岳飞》。1982年剧本在《中外电影》杂志上发表后,一位导演朋友建议让我寄给长期负责电影工作的荒煤同志看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我照办了,并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罗马大战》,自己的《斯特凡大公》和《萨拉丁》的意见。荒煤同志是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当时又正在主持筹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我的本子长达八万字,他有没有时间看,就算看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或态度,我心里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荒煤同志收到剧本后很快便回了一封信,告诉我剧本正在请人先看,让我放心——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撤销,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信是几经周折才转到我手里的。与此同时,著名导演林农也把荒煤同志请他看剧本《岳飞》的情况告诉了我。这已经使我大喜过望,没过多久,荒煤同志看过剧本后又写来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信中对剧本给予了热情肯定,同时详尽而具体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投入拍摄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且征求我是否同意把剧本送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再看一下。读着这封意重情厚的的信,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不为荒煤同志礼贤下士、提携后进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荒煤同志当时正患着病,他是带着病读完剧本写来长信的。不久他住进医院,但在病榻上,他还让秘书及时把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对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转告给我,并且向前去探望他的李存葆同志关切地询问起我的情况。
1984年4月我因公晋京,荒煤同志当时出院不久,正在参加电影“政府奖”授奖大会。我打电话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约我等会议结束后去他那儿谈一谈。但由于单位领导催我返济,我没能如约。直到同年六月,荒煤同志来济南参加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在下榻的宾馆里我才见到了他。那天晚上,我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对我的创作设想提出中肯的意见,也谈到了他对济南的怀念和正在写作的文学生活散记——1937年他同荣高棠、张瑞芳等同志曾在济南演出过宣传抗战的戏。他像慈父一样和霭可亲,也像严师一样认真诚恳。他从古装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到电影事业发展的前景,从当时那股“清除”风讲到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我仿佛面对一片渊深浩瀚的大海。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对后代人的期望。他说:“我今年七十多岁了,该退位了,将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说:“你们老一辈人不知培养了多少人,你们的功德是会铭刻在后人的事业中的。”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荒煤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把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概括为“写人、感人、树人”六个字。他说:“我从解放以来就搞文艺工作,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左’的影响,不讲人学,一谈人情就是资产阶级人情论;一谈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艺术永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永远发展不起来。”我觉得他的主张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创作实践都有着指导作用。
荒煤同志回京后,得知一位导演有心要拍《岳飞》,又特意来信嘱我把剧本改好,并让我把他提的意见转交给那位导演看。虽然时至今日,《岳飞》的拍摄仍在酝酿之中,但荒煤同志对于我的关怀和教育,荒煤同志那种“新松恨不高千尺”、“化作春泥还护花”的精神,却时刻地激励着我。为了繁荣文学事业,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我当加倍努力!
荒煤的“呐喊”
听荒煤同志说,因为小时候不愿意写毛笔字受到过父亲的打骂,他一生都很少拿毛笔,更少有用毛笔为他人题词的时候。我的书房里却真真实实地挂着一幅他的墨宝。
那是1990年8月,荒煤同志应邀到济南参加我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研讨会。《骚动之秋》写的是农村变革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后,一次我给荒煤同志讲了小说中的两个情节,他高兴得咯咯直笑,当即答应要为小说写一篇序言。序言写好正赶上政治风波,荒煤同志得知有人不准他以后再发表文章的消息后,立即给出版社写信,说为了不影响作者和小说的“前程”,要把自己的序言撤回去。由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坚持他才只得做罢。没多久序言在文艺报、大众日报和当代杂志上发表,使《骚动之秋》未经面世,便赢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小说出版要开研讨会时,大家都希望荒煤同志能够出席,可七月的济南遍地流火,荒煤同志又是七十七岁的老人,来得了来不了谁也说不准。然而当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转达了大家的期待,他二话没说便应下了,说:“好,去,我去!”
济南是荒煤同志的故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和张瑞芳等人曾在那里从事过进步文艺的宣传活动。在济南的几天里他访故地,会文友,观名胜,看农村,我一直陪同在身边。言谈中他讲的最多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文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他在《骚动之秋》序言中提出的要我接着写下去,“期望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的心愿。他举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够写出那样几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那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研讨会开过,荒煤同志离开济南前忽然提出要到我家里去看一看。那时我的家很小,又在四楼,便推说来不及了,以后再说。荒煤同志不肯,说:“我来了,怎么能不到家里去看一看呢?”我见如此,只得赶紧叫来了汽车。沿着狭长的楼梯,推开简宜的铁门,荒煤同志屋里屋外看过一遍之后,又特意对我爱人小孔说了一番意重情深的话:希望她能够支持我,尽快地把《骚动之冬》、《骚动之春》写出来。正是从我家回到宾馆之后,荒煤同志爽快地拿起毛笔,为我写下了这张“为骚动之秋呐喊 盼骚动之春早临”的条幅,并且特意在条幅末尾加上了一行“玉民同志留念并请小孔多助谢谢!”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