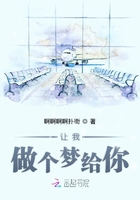身为左相、总领朝纲的罗灵,把休养生息、革除积弊做为既定目标:劝农耕桑、抑制兼并,改革吏制、裁减冗员,发展盐铁、打击私商,改革赋税、严禁豪富把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库得以充塞丰实,皇帝的日子也过得滋润舒坦多了。
那天皇帝高兴,又想起封赏罗灵来了。
罗灵还同往常一样,恭恭敬敬却又不容置疑地谢绝了。
皇帝有些不高兴地板起了面孔,说爱卿功在社稷德在人心,寡人屡次封赏均不被接受,可是嫌弃封赏太薄的缘故?
罗灵说死罪死罪,下臣得蒙皇上厚恩,粉身糜顶难报万一,功且不敢夸耀一句,哪里会有嫌弃封赏太薄的道理。
皇帝说既是这样,今天的封赏是再也不能推拒了。再推拒就是藐视寡人,就要降罪了。
罗灵说,既是如此,下臣单有一事恳请皇上恩准。如不蒙恩准,下臣是甘愿领罪也不敢从命的。
皇上说,爱卿有什么事寡人应承也就是了。
罗灵说下臣一介山野村夫,能有今日,除了皇上的恩德,仰仗的全是驼来峰和老白果树的灵光紫气。皇上屡次封赏下臣屡次谢绝,实在是因为不敢贪天之功的缘故。今日皇上如执意封赏,下臣只请皇上封赏驼来峰和老白果树。倘使故乡灵苗得蒙圣光普照,下臣之愿足矣。
朝廷大臣寸功不取,却要封赏故乡山水,这可算是前无古人的奇事,但皇帝思忖了思忖还是应允了。于是,驼来峰先被尊为大宋王朝十大“圣地”之一,随之,毁于大火的金羊庙由朝廷派员重新进行了修建。只是因为皇上信奉沙门,重建时庙中增加了几位佛家子弟,土生土长的方老被外请的高僧取代了。但庙中祭祀的仍然是金羊;由于金羊曾在昆仑山中修炼多年,昆仑山与天竺之国一脉相承,金羊无形中也被披上了一层佛陀之光。
那是重建的金羊庙落成和牧羊人的亡灵过三周年的日子。消息早早就从京城传来,说是罗宰相要亲自带着皇上的封诰返回故园。故园的官吏百姓因此也早早就做好了迎接皇上封诰、迎接罗宰相荣归的准备。那真是千载难逢的喜庆时刻,州、府、县的官员们冠袍齐整、森森列队,迎出不下二十几里;圣树屯、驼来峰周遭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地穿起紫衣,顶起花环,打起锣鼓,跳起秧歌;那情那景,使不知经过多少大场面的罗宰相,也禁不住把两汪泪水噙在眶里,久久不忍抹下。
第一天是祭祖拜灵。按照诰命,牧羊人得以享受国戚之礼,罗丝被赐予一品命妇之尊。牧羊人的墓被重新修过了;驼来峰上那座焚于大火的阁楼也因此得到了重建:那已经远不是当年看山人的阁楼,而是一座精巧典雅的纪念性建筑了。罗宰相与几位兄妹搀扶着他们的母亲——当年的小新媳妇儿、如今的干瘦干瘦的小老太太,依次焚香礼拜、歌恩颂德。那些州、府、县的地方官员们只有毕恭毕敬随后而行的份儿,一口大气也不敢多喘。第二天金羊庙开山门、老树王封禅大典,地方官员们的能耐就显示出来了。灯笼花红、彩旗锦带、锣鼓鞭炮、人山人海……金羊庙匾额出自罗宰相之手,“天下树王第一”六个浓墨金字则是皇上的御笔。其他,如颂词赠诗、书画碑刻一类,则琳琳琅琅数不胜数,不是出自皇亲国舅、文臣武将之手,就是诗画名家、金石高手的杰作。
高潮是在为老白果树披红结彩上。按照封诰,老白果树被授予“天下树王第一”的称号,准予披红挂彩百年,以示荣耀尊崇。当“天下树王第一”的金匾当空悬起,当震耳欲聋的锣鼓骤然刹住,欢呼雀跃的人群敛声息气、齐刷刷跪了满山遍野,罗宰相一步一拜来到老白果树下,双手轻轻地拉动了一条紫色金线。于是,十几条五彩绸带云霞似地凌空飘落,顷刻之间把一棵傲然挺拔、饱经风霜的老白果树,打扮得花枝招展、金碧辉煌。
老白果树向天而歌,舞影婆娑;满山的松柏、槐杨、花草向天而歌,舞影婆娑;遍野的獾、兔、虎、雀和众多生灵向天而歌,舞影婆娑……
泪水洒了一地,鲜花撒了一地,荣耀和自豪洒了、撒了一地。那泪水、鲜花、荣耀、自豪刻进了人们的记忆,融进了人们的血液,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繁生,以至时止20世纪末叶,在圣树屯的那个有名的“瞎话篓子”的“瞎话”里,人们还能耳闻目睹般地感受到当年的那股感人肺腑的气息。
那一夜羊角号响了一个通宵。那光彩夺目的锦云、欢乐热烈的号角,使罗宰相和成千上万的官员百姓,如登春台如沐春雨。那一年,人丁出奇的兴旺,草木、稼禾、五畜、鱼鸟……出奇的繁茂繁盛。老白果树的花开得也出奇的多、出奇的香。花香传出几千里,一直传进了开封城,传进了宰相府和皇宫。罗宰相和皇上,还特意把一班文人学士召集到龙庭后院,举办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千里品香会”。
罗宰相的新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相当一部分豪强官吏的反对,随着新政的深入,朝廷大员们的切身利益也受到威胁时,右宰相和原本支持罗灵的一班官界朋友,也站到反对的立场上了。他们四处串通,收集罪证,大加攻伐。原本性情懦弱、对新政时而积极时而消沉的皇上担心出乱子,日益采取退缩姿态;一向视新政为洪水猛兽的徐太后乘机发难,使新政连连受挫,成果日渐丧失。罗灵心力交瘁,自觉回天无力,只好上书请退。皇上顺水推舟,改任右宰相担任左相,总揽朝纲。新左相上任不几天,便废除了罗灵苦心经营多年的各项政策。于是,豪富官宦弹冠相庆,百姓社稷重陷困境。罗灵悲愤不已,断然谢绝一切“恩宠”,重返故籍,做了金羊庙主持海玉和尚的门客。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短短几百年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教。海玉和尚本是南宗高僧,那年罗宰相出巡时与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金羊庙重建时就被特意请来了。他精于佛法、通达世情,把金羊庙治理得井然有序;闲暇时则以诗词唱和、书画互赠为乐。诗词唱和、书画互赠,奥妙乐趣全在“唱和”、“互赠”上,小小一座金羊庙里哪儿来的对手?罗灵返乡,可说正应了他的心愿。
按照海玉和尚的意思,罗灵只管做为金羊庙的贵宾住下去就是。罗灵不肯,为了表示与尘世断绝的决心,那一日点起一把火,当着海玉和尚和庙内众僧的面儿,把满头的白发黑发一忽隆烧了一个精光。使海玉和尚大为惊骇,感佩之余,这才不得不为他换了一身僧衣。
沙门之内原本清净,罗灵又谢绝一切应酬,每日念念经拜拜佛之外,就是与海玉和尚口吟笔耕、披剖切磋。几年下来,诗文书画无形中融进了两人的日思夜梦、血液肌髓,成了滋润两人心田性命的雨露。艺海无边,两人过去虽也通晓一二,终是岸边观潮,难得领略浪里风光、水底滋味。此时专心无二,穷博尽览,探幽求微,才真正品出了那种海阔天空、曲婉绮丽的意趣。
“世间如此之大,艺海如此之深,师文习艺的人如此之多,其中珠宝玉翠如此之丰饶,竟然找不到一部论述艺文原理的著作,实在让人惋惜。”一次晚间闲步,来到老白果树下时,罗灵发着感慨。
“是啊,倘若能有这样一部纵论诗文书画之善恶、美丑、高下及其来由、根据的书,你我就大可不必走这么多弯路苦路咯。”海玉和尚也深有同感。
“不过依我看也未必就是坏事。慧能祖师有句名言,老宰相还记得否: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唔……记得倒是记得,只是这可不同于作几首诗画几幅画,只怕罗灵力小才微,徒劳无益呢。”
“岂有此理!以进士翰林之才、一代名相之身,说出这等话来,日后别人哪个再有这种心思,岂不得割了舌头去?”
“唔……法师言重了,言重了。……”
尽管罗灵没有明言应承,从那天起,他确是把主要心思用到了著述上。老树遗精古庙生华,佛光灯影一伴就是6年,一部洋洋30余万言的《诗心艺韵》手稿终于交到海玉和尚手里。海玉和尚视若经典,精心揣摩珍藏,终于在罗灵仙逝7年后,使之得以面世。而一面世,就受到朝野称颂,被视为文坛上的千古绝笔;以至代代相传,不绝如斯,罗灵当年住过的小屋和死后留下的墓地,也成了驼来峰和老白果树下的一处圣迹。
9
罗宰相还乡皈依佛门,罗宰相的子孙们一直被留在开封。罗宰相有三儿四女,三儿四女各自又生下三儿四女,如此这般,不过几辈功夫,罗家林林总总已是不下百十口子的样子。名门之后再出名门,这是时尚,历朝历代无不如此。罗宰相虽说得罪过一批官吏豪富,却也留下过不少恩德,按说子孙中有人弄个或大或小的官儿当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然则不然,罗家家道一直算得上富裕兴旺,可也一直富而不豪、旺而不达;百十口子人中经商的有,为文的有,入了空门当和尚道士的也有,唯独没有做官的:芝麻眼儿大小的官儿也绝对没有一个。不仅宋朝没有,后来朝代几经更迭也还是没有。开始没人说得清是为的什么,直到海玉和尚留下的一册记事录被发现,那谜才解开了。原来那正是出于罗宰相本人的意愿——他深感政治腐败、官场险恶,返乡不久,便请人把自家一处“最发富禄”的风水变了样儿;临死前,又特意精心布设,有意堵断了后人求官问爵、进入仕途的路。这一堵就是几百年,直到罗家传到第14代孙时,才出了一名进士,出了一名七品芝麻官儿。
那第14代孙名叫罗世功,从9岁时开始苦守孤灯,一直守到两鬓花白才算是戴上了一顶微平展角的进士巾,穿上了一身广袖不杀的青罗袍,佩起了一副与六品以下官员一模一样的槐木笏。那要算是极其幸运的了。科举科举,不科不举,登不了金榜就永远得不到任用,得不到出头之日。因为这,穷经到老,赶考到老,终生无成,以至悬梁跳井、疯痴呆傻的,天知道有多少。那御赐巾袍确是恩光宏照,罗世功原本有些昏黄的双目一时光彩奕奕,原本清瘦苍白的脸面泛起一层红润,连两缕稀疏淡白的胡须也仿佛比往日飘逸了许多。但那巾袍只穿了几天,上过表谢过恩,拜谒过先师行过释菜礼之后,便又交回了国子监:中了进士还只是得了一个出身和资格,朝廷不放任,仍然算不得官儿,仍然算不得功成名就。可放任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罗世功又穿了5年常服,苦熬了5个春秋,才被赐予一身梁冠赤罗衣、二色绢革带外加银佩药玉、白袜黑履等一应官服官饰,放回祖籍做了知县。那时他刚好过了第55个生辰。
驼来峰、圣树屯所在的这方地面,古称盛邑、盛阳郡、盛阳州,明朝宣德年间改州为县,于是罗世功便成了大明王朝的第7任盛阳知县。
作为罗宰相的后代,罗知县果有先祖遗风。上任时不事声张,只带了两只毛驴和一个名叫王凤的老家人。风尘千里,踏上盛阳地面时天上正下着小雨,他衙门未进,先上了驼来峰。对于老白果树和金羊庙他可谓向往日久,不少故事他甚至耳目能详。但开封城与驼来峰关山千重,能够回到祖先故里,实地瞻仰、参拜老白果树和金羊庙,实地瞻仰、参拜先祖的故居和陵墓,对于他实在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运。
尽管他在55年的人生中,尤其是前来上任的一路上,已经不知多少次地在心目中描绘过老白果树伟岸、恢宏的气势、形貌,可当他真正站到老白果树面前时,还是觉出了自己的渺小,觉出了想象力的贫乏。他让王凤把毛驴拴到远处,一步一拜来到老树前,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这才细细打量起来。
正是孟春时节,满树新叶撑开一把烟霞般的巨伞,把满天的小雨遮了个滴水不漏。白果树的叶子天生就是一种艺术品:半月形的、精巧绝伦的扇面;扇面上一幅幅天然而又绝妙的图画;举起扇面和图画的青绿细挺的长柄;由扇面、图画、长柄构成的一只只双翅招展的绿蝶。绿蝶一丛一簇,丛丛簇簇布满古干新枝,把一棵雄飞高举的老树王打扮得花枝招展、蔚为壮观。更奇的是那叶子光滑而又洁净,无论怎样的风尘都沾染不了,无论怎样的病虫灾害都奈何不了。老白果树的叶子比起一般白果树的叶子格外阔大、丰厚,因而也格外娇丽婀娜。游人至此,采几只“绿蝶”夹进书里、本子里,就是再好不过的纪念品,愈是远走千里万里,愈是过去十年、几十年之后,愈是会成为珍贵无比的相思之物。罗知县围着老白果树边瞻仰端详着,边发着感慨赞叹。
转过几圈罗知县忽然心生一念,想起要量量老白果树到底多粗。几百几千年,人们说起老白果树,用的总是形容词,诸如高可入云、摩星勾月啦,魁伟无比、叹为观止啦,很少有人说得清老白果树究竟多高多粗。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作为老白果树的儿孙和新任知县,他可不愿意继续糊涂下去。高,量起来麻烦;粗,可是再简便不过的了。他让王凤盯准一个位置站好,自己张开双臂,围着老白果树打起了转儿。一搂、两搂、三搂、四搂……一直量了九搂,还没量完,见王凤忽然一个劲儿朝这边打着手势使着眼色,以为是不足一搂了,便张开手掌一拃一拃地拃起来;一连拃了八拃,还要继续拃下去,这才发现树下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位躲雨的小新媳妇儿。那小新媳妇儿一身红,身上淋了不少雨,不住地只是抖落着、扑打着,丝毫没有注意到罗知县量树的事儿。罗知县有心请人家让开一点,话到舌尖几次打了旋儿,也只得作罢了事。
好在那并没有影响丈量的结果。
“九搂、八拃、外加一个小新媳妇子儿。”罗知县不无幽默地报着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