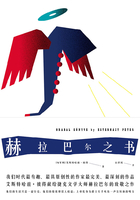“这你就不懂了。企业建厂房机关盖大楼,就连修个桥、开个大门,当不了也得选个好地气、好方位、好时间,要不吉利不吉利可就难说了。”
“那看了就一定吉利了?”
“你们小青年哪懂这些。烟台一家商场从建起来就没赚一分钱,大师去调了调大门的位置,第二年就赚了二百万。大连一个区委书记怎么着就是提不起来,章大师在他办公楼上安了一个八卦罗盘钟,现在副市长都当上两年了。”
智新咧了咧嘴,卓守则却惊奇不已,说:“这一说就更得见大师一面了。”他拿出几包海米送到吴老师面前说:“请你跟大师好好说说行吧!”吴老师说:“我们这儿不兴这的。你要是真心就捐点款吧。我们这三合功园都是捐款建起来的,大师最看重的也是这。”
卓守则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得求到章大师门下,就把身上的一万块钱拿出来说:“这是第一次,是答谢大师的,以后我们肯定还得捐。就是见大师的事儿……”吴老师说:“要不这样,晚上大师回来我汇报汇报,明天你们早点来……”
在圣子山下一家小宾馆里住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卓守则和智新果然见到了章大师。章大师之为大师与过去确是大不相同了。一身长襟布扣的学者服,一双亚麻编织的布底鞋,一头齐齐整整的银发,再加上一张透着枣红的面庞,确乎有了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他听卓守则讲过智新的情况说:“好,早就说卓家还有兴旺的时候,这不看见了嘛!大智若愚、大器晚成这是古来就有的;姜子牙八十岁出山,智新要真到那份儿上才好呢!”
从圣子山回来,卓守则对智新的“以后”越发信心百倍。他带着智新连续拜访了东沧和海州不少头面人物,把当年章大师怎么预言的、后来病怎么好的、这一次章大师又是怎么说的,不厌其烦地向人家做着介绍。智新对章大师且信且疑,对父亲挨门介绍更是不以为然,走过几天就再也不肯了。这样卓守则只得告一段落,接下把卓家的历史一遍遍地给智新讲起来;讲的全是卓家如何如何对年家恩大如天,年家如何如何对卓家忘恩负义。开始智新只是默默地听,听得紧张也听得义愤。可听了几天就听出疑惑来了,说:“爸,你干吗老讲这些呀?不会是让我回来替你和我爷爷报仇的吧?”
卓守则被问了一个怔愣,说:“这个孩子!你是卓家的老大,卓家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你爸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你不知道行吗?这不单单是个报仇不报仇的事儿懂了吧?”
智新似乎懂了,把脑袋点了几下,又似乎越发懵懂了,眼睛里一连闪过几缕茫然的光波。卓守则看出单靠自己不行,那天摆起一桌酒席,把四叔、卓守礼和卓家几位有头有脸的人找进了门。席间说了不少祝贺智新的话,也说了不少卓家的苦难和屈辱。因为是大家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智新的好奇心被说得动了,不少原本进不到脑子里的话和事儿,有意无意打下了印记。因为座上还请了一位正在为卓守则写书的作家,话题也就说到最近就准备出版的书上,说到了卓立群被枪杀那一段要不要保留上。作家是省里一位创作员,姓魏,据说是影响大得不得了和跟上边的大人物铁得不得了的。他的意思是保留,说那才是全书的“戏眼”,少了那一段后边好多事儿就很难说得清;再说一个自小靠做小本生意发了家的民族资本家,能跟共产党国民党、****国军扯得上什么瓜葛!平白无故被枪杀了这么多年,连几句公道话都不兴说吗!这一说四叔就抹起了眼睛,说:“惨哪!那个惨哪!只穿了一个花裤衩,还让血染得黑糊辘涂的。”卓守则面前就出现了父亲像狗一样蜷曲着身子和落了一层苍蝇的情景,眼睛里就湿了。
卓守礼问:“那么当时说海州分区差一点被消灭是因为二叔送了情报,到底有没有根据,凭的是什么?”
四叔说:“屁!还不是因为你大伯在那一边是上校参谋长,想找个垫桌子腿的出出气!”
卓守礼目视卓守则问:“上次你去香港时大伯是怎么说的?到底有没有送信这个事儿?没有,这个案不翻过来是不行的!”
卓守则说:“就算没有送信的事儿还有大地主大资本家那一条呢,你想翻就翻了?再说大伯当时病得那么重,我问得出口吗?”
卓守礼说:“那照这么说,这个冤案就得没完没了地背下去了?”
卓守则说:“那不就在咱吗?现在又不是过去,你想背背,不想背扔了谁还怎么着你了?”
魏作家说:“这才是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背那?要不当初我给卓总说这本书一定要写,这不是你一个人和一家人的事儿,是牵扯到不少人不少家的事儿!”
卓守礼说:“这么说你对那段历史,体会还挺深的?”
魏作家说:“反正今天没外人,我就说个实底吧。我爷爷苦了一辈子置了九十多亩地,雇了几个人帮忙还是忙时来闲时候走,到了一个大地主扫地出门,把我们这些儿孙辈也压了二十几年。共产党那真是罪责难逃!”他见卓守则显出几分不自在,连忙声明说:“我是只在这儿说,到外边嘴可是严得很,谁他也别想抓住我半点把柄。”
卓守礼说:“那你觉着老爷子这一段是留好还是不留好呢?”
魏作家说:“要我说当然是留。不要说送信的事儿拿不出根据,就是拿得出根据那也是各为其主,比起逃到台湾的那些人屁都算不上一个!那些人成了座上宾和这委员那委员,老爷子倒还……当然了,卓总要是让删我就删。不过这个材料我是绝对不丢的,起码得写出部小说来。现在全世界都讲保护人权人性,你侵犯人权摧残人性,我喊几声冤枉都不行了?这我可做不到!”
卓守礼说:“行,这才叫有种!五七年的错误承认了,六〇年、****年和****的错误承认了,再往前为什么就不承认了呢?”
卓守则说:“你们也不用说那么多,这个事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试探试探再说,要是留不住,我可是寄希望于魏作家的小说了。”
魏作家胸脯一拍说:“那是!说不定还捧回个大奖来呢!文艺界是越是戳得狠戳得痛越是有人给你叫好!不信你们就等着瞧!”
话题到此结束,酒宴到此结束,智新仿佛明白了许多也仿佛糊涂了许多,没等众人出门他就有点结巴地对卓守礼说:“叔,我怎么觉着你你你们讲的那些,挺没有味味味儿的呢!”
一般地讲肯定是不行了,卓守则寻思着得出去,让智新有点实际体会和感受。想法一露立刻得到响应:回美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智新可不想闷在家里老是听那些没滋没味的老皇历。
两个人的想法合到一起,要去的地方随之确定下来:那一是深圳,二是新疆。
去深圳,卓守则要看的是当年逃亡时的那片荔枝园和草厦子,要看的是那个埋死尸和逃港被抓住的深圳河。荔枝园和草厦子是一进深圳就知道白想了的:扑面而来的除了高楼大厦、花园大道还是高楼大厦、花园大道,连一片原来意义上的果园也难得见到了。人住下,打了一辆的,在高楼大厦和花园大道中转了两个小时,也只是大概找了一个方位。深圳河还在,除了河堤经过整修,河边的平房变成小楼、小路变成大路,并没有太大改变。沿着河堤走进河滩,卓守则讲起当年被人拉来掩埋死尸的情形,讲起冒着子弹和强光灯外逃的情形,不一会儿就把智新眼睛里讲出了火花。
“爸,那要是当时你被打死了,就白死了吗?”
“不白死了怎么着?说不定你脚底下就踩着几个死人,哪一个还能活过来不成!”
智新急忙低头搜寻,确证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脸上才算是平稳了。
“那……那要是你那会儿死了,就没有我了吧?”
“怎么没有?要是那会儿我死了,说不定这会儿你正在给那几棵小草上营养呢!”
那说得智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惨!可真是太惨了!”他露出了从未有过的严峻和悲伤。
沿着河道下行,来到当年被捕的那片滨海的河滩时,卓守则在一座小沙堆前坐下了。往事已经变得淡而无味,悲哀却有如高天之云、大海之浪,冲击着、缠绕着,使他仿佛变成了一尊悲天悯人的佛雕。智新理解爸爸的心情,却只坐了几分钟便走向旁边的一片草地;在草地上徜徉了一会儿又去到水边,洗起了手和脸。手洗净了脸洗净了,一路的风尘、一身的风尘、一肚子的风尘洗净了,才回到小沙堆前对卓守则说:“爸,咱们也该走了吧!”
他满脑子都是未来,不愿意爸爸过多地沉湎于往事。卓守则果真被惊醒了,不无怅惘地站了起来。
从河滩出来,来到当年那个穷得出了名后来又富得出了名的渔民村时,卓守则与一位散步的老人聊起了天儿。他问老人记不记得当年这里逃港的人多得数不过来、死的人埋不过来的情景。老人嘴角一笑,说:你也知道那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儿的?卓守则说我就是当年在这里埋过死尸,也差一点把自己埋在这儿的人。老人嘴角又是一笑,说这个村当年没埋过死尸和没差一点让人给埋了的找不出几个,现在你再试试,有走的才是怪了!卓守则为着让智新能听明白,问那是为的什么呢?老人说******有话呀,你那个政策有问题呀!卓守则说******有话?我可是一点都没听说。老人说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复出,一次到广东视察,听说深圳河边逃港的人越来越多,边防部队打死了那么多人也阻止不住。******说还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呀。那时的很多人,包括给******汇报的人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逃港属于叛国投敌,对于叛国投敌除了抓捕只有开枪,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政策会有什么问题呢?直到改革开放,逃港的人回来了,向外赶也没人再走了,人们这才明白了******的本意和非同寻常之处。
卓守则是第一次听人讲起这段往事,第一次知道******当年说过这样了不起的话。细细地体味,他甚至于把******的口气、表情也想象出来了。
“谢谢你老伯!特别地谢谢你老伯!”卓守则拉着智新站到老人身边,以深圳河为背景,郑重其事地留下了一张合影。
从深圳河回来,智新果然受到了触动。他问:“爸,你当初逃港时没想会有今天吧?”卓守则说:“那会儿连第二天脑袋还在不在也说不准,还今天!”智新说:“你当时特别恨那些坏人是吧?”卓守则说:“不仅当时恨现在也恨。你没听人说不懂得恨就不懂得爱吗!”智新问:“那你是不是觉着我大爷爷他们不去台湾中国就好了?”卓守则说:“你大爷爷他们?这跟你大爷爷他们有什么关系?你大爷爷他们当年要是真好、真有能耐,还至于让人家赶到台湾岛去吗?”
智新有些迷茫了,说:“这么说你也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了?”
卓守则被问得有些懵了,说:“你爸恨的是那些坏人,怎么会恨改革开放呢?没有改革开放你爸能不能活到今天,咱们卓家断没断根儿也难说得很!坏人是一回事儿,改革开放是一回事儿,这可不能搞混了啊!”
智新这才笑了,说:“那就行!我们在国外的同学可都是拥护改革开放的!”
卓守则哭笑不得也喜出望外地拍着智新的肩膀说:“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
有了深圳河的一番感受,智新对华云当年帮助父亲逃命和阻止父亲逃港的行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劲儿地催着要去新疆,要见华云姑姑。旧地重游,同样勾起了卓守则对华云的思念,对库尔德林大草原的思念。当晚两人便买了经由乌鲁木齐去伊犁的机票。第二天傍晚时分,卓守则和智新便出现到华云面前了。
华云来到库尔德林大草原已将近四年。将近四年里,凯华从一个黑黑的小肉团儿,变成了一个在草原上四处奔跑的小哈萨克——草原上的哈萨克牧民,皮肤黑黑的鼻梁高高的,与凯华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四岁的小哈萨克,每天都追在华云身后喊着“妈妈妈妈——老师老师——”追在老科学家身后喊着“爷爷爷爷——老科老科——”随着凯华长大长高,华云不仅学会了照料孩子和养蜂,还学会了说哈萨克话跳哈萨克舞,学会了吃馕、喝奶茶、弹冬不拉。一所牧民小学,更是把孩子们稚嫩悠扬的歌唱,传遍了浩茫古老的草原:
加克西玛——你好
翟仑木——草原
阿它——马
伊犁阿它——伊犁马
可日——羊
夕日——牛
他马克什——吃饭
热合买提——谢谢
合试里冬试——再见……
凯华也是妈妈的学生。长了本事的凯华经常又用汉语或哈语,考着妈妈和爷爷。
“爷爷爷爷,泉水怎么说呀?”
妈妈或者爷爷也总要变着法儿考一考凯华,让凯华在课堂之外把学到的词句再复习几遍,或者再学一句新的。每到此时,暖暖的黑蜂房里,绿绿的草地上,这个特殊而又幸福的小家庭里,总会溢满欢笑。那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动人的欢笑了,华云经常都要情不自禁地落下热泪,老科学家经常都要情不自禁地落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