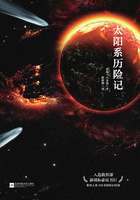生意仍旧很清淡,每日只能赚回一点维持平常日脚的小利。
沈梦洁又调整了货架,把一些有妆色的货物放到显目的地方。
她定定地坐在店堂里,每天的早晨总是纷乱嘈杂的,弄得她头昏眼晕、神思恍惚,只有到开了店,坐定下来,才稍微可以松口气。可是一入定,脑筋清爽了,她就会想起连续几个夜里听见的那个奇特的声音。她看见大孃孃百般无聊地立在那里东张西望,煞不牢召呼她:“哎,大孃孃,你过来,我问你一桩事体。”
大孃孃兴头十足,颠颠地跑过来:“啥事体!”
沈梦洁一时倒不好直言相问了,只好说:“你们夜里困觉,有没有听见什么声响,这地方,夜里有什么物事么?”
大孃孃的面孔马上紧张起来:“夜里啥物事?你夜里听见啥声响啦?”
沈梦洁顿了一顿说:“我也说不出是啥声响,反正蛮可怕的,又象哭又象笑,又象唱歌又象背书……”
“在啥地方?”大孃孃眼乌珠[5]弹出,问得汗毛凛凛。
沈梦洁身上不由得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啥地方,我也听不清,反正蛮近的,好像就在身边。”
“喔哟哟,沈老板,你真的假的……”大孃孃现出紧张、兴奋、神秘的情态,她压低声音问:“你听说过邱小梅吧,她就是在这间屋里吊……”
下面的话不讲了,让沈梦洁自己去想象,自己去吓自己。
沈梦洁勉强镇静下来,但面孔有点发白。对过“吴中宝”店里黑皮听见她们的对话,吹了几声口哨,就过来搭讪:“沈老板,你听她瞎说,大孃孃一张咀巴,你要上当的……”
郭小二也在一边笑:“大孃孃你不作兴的,人家沈老板新来乍到,你不可以吓人家的□……”
沈梦洁心里放松了一点,但还是疑心疑惑:“不过那种稀奇古怪的声音我真的听见过,呜哩呜哩,吓煞人……”
黑皮和郭小二一同哈哈大笑:“啊哈哈,啊哈哈,沈老板吓煞人,呜哩呜哩,小和尚念经呀……”
沈梦洁一想对了,恐怕就是那种声响,不由也哈哈大笑。
大孃孃还不甘心,说:“你们不要瞎缠,和尚念经归和尚念经,和尚念经和鬼哭是不一样的……”
沈梦洁再细细回想起来,那声音很凄厉,很悲凉,和尚念经怎么会有这种悲切之情呢。
“我告诉你们,天井里唐师母一直生毛病,爬不起来,人家全讲是……上身了,八月半那一日,唐师母……”大孃孃正在绘声绘色地往下讲。郭小二眼睛尖,叫了起来:“哟,小和尚来了,问问他们……”
沈梦洁连忙朝那边看。
两个穿着的确良袈裟的小和尚各人挑了一担水桶,从寒山寺边门出来,到寒山寺弄老虎灶去泡开水。沈梦洁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年轻的和尚,不由多看了他们几眼。
郭小二贼皮赖脸地说:“沈老板,小和尚不可以多看的,和尚怕女人看的……”
沈梦洁笑骂了一声:“小猢狲”又问郭小二,“小和尚挑水吃,和尚庙里不开伙?”
“咦,现在样样讲究经济效益,和尚也要讲经济效益,自己烧水不如到老虎灶泡水合算么。”
沈梦洁觉得很好笑,郭小二却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和尚又不是佛,又没有成仙,和尚也是人呀,也要吃也要穿……有的小和尚还买猪头肉吃呢。”
沈梦洁说:“和尚庙里没有规矩的?我听人家说做和尚苦煞的,一日天只许睡三、四个钟头,吃么,只有点薄粥咸菜汤……”
大孃孃说:“你讲的是老法里的和尚,现今的和尚也惬意的,老法里的和尚是苦的,喏,钱老老喏,老早也做过和尚的,做得面孔蜡蜡黄。”
郭小二戳穿了大孃孃的牛皮:“你怎么晓得,钱老老做和尚的辰光,你在哪里?”
大孃孃面不改色:“咦,是钱老老自己告诉别人的,他自己讲出来的事体,还有假的?”
隔了不多久,两个小和尚挑了两担热水走过来了。
郭小二连忙去拦住他们,用普通话说:“哎哎,小和尚,歇歇,歇歇。”
小和尚放下水桶,两个人也不施礼,只是随随便便地问:“何事?”
郭小二对沈梦洁眨眨眼睛,说:“没有别样,问你们一桩事体,你们想不想女人?”
“罪过罪过。”又是异口同声。
沈梦洁熬不牢笑了,她发现两个小和尚也拼命憋住笑。
郭小二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们为啥口是心非,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不想女人的,你们是不是男人?”
小和尚终于笑起来,其中年纪稍大一点的一个说:“我们可以发功排杂念的……”一边说一边和另一个和尚甩令子[6]笑,活络得很。
沈梦洁插上去问:“你们原来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来做和尚?”
小和尚低垂了眼睛,不看沈梦洁的面孔,说:“我们是佛学院毕业分配来的。”
“是灵岩山上的佛学院吧?”沈梦洁说,“还有大专学历呢,你们上佛学院,读点什么书?”
小和尚神气起来:“女菩萨,不瞒你讲,我们读的书多呢,功课有《金刚经》、《般若经》等经书,还有两门外语,还有天文地理等等,至于我们自己看的书,什么都看,金庸琼瑶,还有佛洛依德……”
沈梦洁简直不可思议,和尚看佛洛依德,会成为什么样的和尚。
郭小二拍拍小和尚的肩:“啥,小和尚——”
小和尚正色地纠正郭小二:“我们都是有法名的,我叫悟性,他叫悟原——”
“啊哈哈,啊哈哈,悟性:悟原,还有悟空,悟净,悟能呢,啊哈哈,小和尚……”
叫悟原的小和尚说:“你不要小看我师兄,他马上就要升为执客了,执客你懂吧——”
“执客,”郭小二寻开心:“执客算哪一级干部,处级?科级?”
悟原一本正经点点头:“科级。”
“那还得加工资吧。”
悟原又点点头:“自然有的。”
悟性招呼师弟:“走吧,水要凉了,老家伙又要啰嗦了。”
悟原挑起水桶,临走,压低声音问郭小二:“你有没有邓丽君的磁带,帮我弄弄看,我隔日来拿。”
沈梦洁看着两个小和尚走回寒山寺,她绝对不相信,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能够净六根,达彼岸。
小和尚走了以后,钱老老又踱过来,问:“小和尚同你们讲什么的?”
郭小二说:“小和尚讲,老和尚要来请你进寒山寺主持佛事,他们说你从前做和尚做得贼精,现在庙里一塌糊涂,要请教你老先生呢,喂,你从前是不是做过和尚?”
钱老老不点头也不摇头,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是盯了沈梦洁看。沈梦洁被钱老老的眼睛感动了,差一点说:“钱老老,你想认我做女儿吗?”
沈梦洁父母死得早,一个人过了许多年,还从来没有年长一辈的人这样温和地看过她,因为她个性强,穿着打扮也是独出一只角,上了年纪的人看不惯她的腔调,钱老老却偏偏对她百看不厌。
钱老老盯着沈梦洁的面孔,自言自语地说:“寒山寺大雄宝殿里的寒山、拾得铜像,寒山的肚脐眼是一枚铜钱,说是铸寒山佛的辰光,枫桥有一个贫女从小佩带上拿出这枚铜钱,之后投入熔炉——这枚铜钱不曾烧化,原模原样变成了寒山和尚的肚脐。”
沈梦洁心里一动。
钱老老又说:“后来他们到佛像身上刮铜,把那枚铜钱也挖下来了。”他指指寒山寺的山门:“当家和尚气得吐血——”
郭小二挖苦钱老老:“那个贫女叫什么?是不是住在这条街上?”
钱老老闭着眼睛摇摇头:“不晓得,不晓得。”
“作兴是钱老老的好婆[7]还是太婆[8]……”
“罪过罪过,”钱老老说:“后来那女子得道,看破了红尘,做了尼姑。”
沈梦洁没有同他们一起笑,她不相信这样的传说,但是听过之后,她心里却有了一种辨不清的滋味,她总觉得自己一世人生也看不穿这爿世界的,就是到了另一爿世界上,也仍然会象现在一样的。周川曾经说她有做女王的野心,她从没有反驳过。她和周川正好是互补的一对,她是处处不让人,处处不认输的,而周川却是个老好人,处处让人,处处甘拜下风的,有时候沈梦洁觉得真不合算,她这一边在外面争强好胜,周川却在他那一边把一切名利抛在脑后。为了这个,她抱怨过周川,可周川笑笑说:“这叫互补维持平衡,要不然,这爿世界就会倾斜的。”
沈梦洁和周川相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周川在一座很普通的中学当语文教师。有一日和沈梦洁同科室的一位中年女技术员的儿子来找母亲,说学校要开家长会议,让母亲马上去,那位女技术员正有加班任务走不脱,沈梦洁于是自告奋勇去了。周川见了沈梦洁很惊讶,问她是那个学生的什么,她瞪了他一眼,“说是:阿姨,有什么话你说是了。”周川却顶真地说:“我们要求母亲或父亲来,别的亲属不能代替。”沈梦洁哼了一声,说:“你这个人煞有介事的,这样卖力气,领导又不会给你加工资加奖金的。”周川更加认真地说:“我做班主任每月是比别人多拿六块钱奖金的。”说得沈梦洁笑弯了腰。
为啥要同这样一个人结婚,沈梦洁并不是一时冲动,她自己总想出人头地,高人一等,要是嫁一个同样好胜的男人,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她同周川性格上可以互补,事业上却需要周川为她作一些牺牲。可惜,结果却适得其反,三年前,周川那所中学分到一个援藏名额,大家都不肯去,推来推去,最后周川说:“终归要有一个人去的,就让我去吧。”
沈梦洁大叫大闹也没有阻止得了,周川可怜巴巴地说:“别人都不肯去的,讲好我去的,怎么可以后悔呢。”周川走的辰光,沈梦洁正面临各种困难,她报名考职大,单位不同意;儿子刚满周岁,正是烦人的时候。周川却说:“这点事好办,小人交给好婆带,考大学就不要考了,现在单位待你不错,上了大学不一定能有更好的位子。”说完就走了。这一走要去八年,每年顶多能回来一次,沈梦洁这辰光才明白她嫁的是一个多么偏执而无情的人,她守着空房哭了一夜,第二天把儿子放到婆婆那里,转身就去报考职大了。
沈梦洁正在胡思乱想,大孃孃走过来,很神秘地对她说:“喂,沈老板,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沈梦洁抬头一看,铃木宏慢慢地朝这边走过来,好像很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她没有对大孃孃说什么,她对这个神经兮兮的日本人不感兴趣,反正他不是来买东西的,同她不搭界。
郭小二也看了一眼铃木宏,突然说:“这个人不是日本人,前两天我碰见他和奶油五香豆在讲话,一口苏州话,比我这口江北苏州话地道多了。”
沈梦洁奇怪地“哦”了一声,又抬头看看铃木宏,铃木宏已经走近了,对她友好地一笑,完全不是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夹杂着仇恨和疑窦的表情了。
沈梦洁也对他报以同等的一笑,心里却骂了一声:“十三点。”
铃木宏用日语问沈梦洁:“请问,邱家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吧?”
沈梦洁突然想弄送一下这个不晓得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脚色,她突然一笑,用苏州话问铃木宏:“你是邱家啥人?”
铃木宏面孔上有点尴尬,古怪地笑笑,朝寒山寺弄一号院子走进去。
过不一会儿,天井里传出邱贵老婆尖利的哭叫声:“邱荣死掉了,去寻死路了,你到阎龙五那里去寻他吧……”
铃木宏走出来,面色仓皇还有点气愤,沈梦洁他们几个人暗地里发笑。
铃木宏好像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地走开,他站在“寒山屋”门口,随手拿了柜台上的一座老寿星瓷像,问了一下价钱,也没有还价,就付了外汇券。
沈梦洁晓得这个阴森古怪的人心事重重,她不由多了一句咀:“你寻邱菜,他现在不大回来的。”
铃木宏盯着她看了一眼,终于用吴语和她对话了:“你晓得他现在住在啥地方?”
沈梦洁说:“只听说在盘门那边开了一爿店,具体地方不清爽,我也要寻他呢。”
铃木宏探询地看着沈梦洁。
沈梦洁说:“你看,我这个人大约不是做生意的胚子,店开了这一阵,生意做不起来,今朝要不是你施舍点外汇,要去喝西北风了。”她看见铃木宏面孔红了,开心地笑起来,继续说:“我寻邱菜,是想请教请教他的生意经。”
铃木宏乘机提起他关心的话题,“这爿‘寒山屋’是你向邱荣租的吧,邱荣的侄女邱小梅你认得吧?”
沈梦洁奇怪他怎么了解得这么清爽,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晓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铃木宏反问:“你看呢?”
沈梦洁眼眉毛一挑,一本正经地说:“我会看相的,你是做侦探的,半个中国人半个日本人,对不对!”
铃木宏警惕地看看沈梦洁,并不明白她是真是假。
“你自己肚皮里有数脉,不做侦探,为啥这样虚头晃脑,鬼鬼搭搭的腔调。”
铃木宏掩饰地笑笑,他想不到自己在沈梦洁的眼睛里是这样一个形象,也不晓得沈梦洁为啥要回避邱小梅的事体,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那个邱小梅,你认得吧!”
沈梦洁抓疑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我不认得,我是来步她的后尘的。”
“那个邱小梅,她到底为什么……”铃木宏期待地看着沈梦洁。
沈梦洁仍然摇头:“我不晓得,从来没有啥人来向我介绍过邱小梅,我对这种事体也不感兴趣。”她发现铃木宏非常失望,就指指大孃孃、郭小二他们说:“喏,立在那里的几个人,他们是这里的老人家了,你可以去问问他们。”
铃木宏看看那几个人,叹了口气,摇摇头,十分不情愿地走了。
沈梦洁不明白,他既然可以向她打听,为什么就不能去问大孃孃呢。
大孃孃见铃木宏走了,赶忙凑过来,挤肩弄眼地说:
“哟,沈老板,你们讲得热络得来,他同你讲点啥?”
沈梦洁原本想实话相告,可不晓得什么念头一转,把话咽了下去。
对过“吴中宝”店的黑皮话中夹音地说:“日本人挑你一笔生意,给的外汇吧,你花功不错么,日本人存心挑你的……”
大孃孃盯牢沈梦洁的面孔看了一歇,莫名其妙地笑起来,说:“面盘子着实算标致的,哎,那个假日本,会不会看中你了!”
沈梦洁心中很反感,但随乡入俗,嬉皮笑脸地说:“可惜我没有这份福气,喏,对过店里骚妹妹,一张面孔雪白粉嫩,人家欢喜的。”
黑皮听见沈梦洁把话又甩还给他了,晓得这个女人不是好惹的。黑皮虽然年轻,但架子却不嫩,说话办事都讲究分寸,表面文章是做得蛮好的,所以,他就没有再接咀同沈梦洁打舌战。
大孃孃立得腿脚发酸,回到停车场的遮风棚坐下来,六路公共汽车到站了,下车的客人大多数往寒山寺涌过去,只有一个老太婆抱了一个四五岁的男小人朝停车场这边走来。
老太婆穿了一件蓝竹布大襟衣裳,一双布鞋,头上包一块方头巾,腰里束一块围身头,实足一个乡下老太婆,那个男小人倒长得蛮清爽,穿得也蛮洋气。
乡下老太婆走近大孃孃坐的地方,翕动几下干瘪瘪的咀问:“老阿嫂,问个询。”
大孃孃不屑地白了她一眼,心想叫我老阿嫂,我总比你这个老太婆要嫩一点的。
“老阿嫂,”乡下老太婆不晓得是不识相,偏偏还多喊几声:“老阿嫂,问个询,有爿店叫,叫寒山寺,哦,不对,叫寒山啥的,新来一个老板是女的,在啥地方?”
大孃孃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不是直接回答她,却反问道:“你寻她做啥?”
乡下老太婆蛮拎得清,听大孃孃的口气,晓得沈梦洁离这里不远了,一张尖咀也不饶人了,反唇相讥:“我寻她做啥,反正是有事体,没有事体大老远跑来寻死啊,真正告诉你,喏,这个小人,是沈老板的儿子。”
“啊?啊啊!?你讲什么,你讲讲清爽,你讲这个小人是沈老板的儿子,沈老板哪里来的儿子,真是滑稽,你个老太婆,这个小人哪里来的?”
“咦,你这个人问出闲话来别有一功的,哪里来的,当然是她养出来的,总归不会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大孃孃兴趣浓厚,也不在乎乡下老太婆的口气,又问了一遍:“这个小人,真的是沈老板的?”
沈梦洁的阿婆是个很粗俗、尖利的乡下人,恐怕从出世到今朝,从来没有人教过她怎样讲话才有礼貌,她的儿子周川一点也不象是她养出来的,娘儿两个脾气正好相反。她对大孃孃横了一眼,说:“不是她的,是你的?”
大孃孃一口气噎住,她还没有碰见过这么不讲理,讲话这么冲的人呢,顿了一歇,实在熬不牢,又问:“你是帮她领小人的吧?这个小人是不是她的私生子?”
沈梦洁的阿婆火天火地:“啥人私生子?啥人私生子?你这样瞎讲,要吃耳光的,告诉你,这个小人是我的孙子,沈梦洁是我媳妇!”
大孃孃不相信沈老板会有这样一个老阿婆,但是这种事体又不好造谣的,谅她老太婆也不敢当面说谎。大孃孃换了一副面孔,对沈梦洁的老阿婆说:“噢,噢,噢,你是沈老板的阿婆啊,哟哟,好福气,抱孙子了,你不要缠错[9],我是讲沈老板看上去蛮嫩相,不象生过小人的……来,来,我领你去……”
只消手指一指的地方,大孃孃还热情地领过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先拉直喉咙喊起来:“沈老板,你快点出来看看,啥人来了!”
沈梦洁闻声从店里出来,看见是阿婆抱了儿子来,一时十分惊讶。
一直不作声的儿子,看见姆妈,急得叫起来:“姆妈,姆妈,抱抱!”
沈梦洁连忙过来抱儿子,亲儿子。
左邻右舍都有滋有味地看。
大孃孃继续大声叫喊:“喔哟哟,沈老板,儿子这么大了,真看你不出□,你这个儿子,象你的,你看一双眼睛,乌溜溜地转,滴滴滴地看,活象你;一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们大家讲,象不象,啊?”
不等沈梦洁发问,她阿婆叽哩哇啦地抱怨起来:“这个小鬼头,作煞了,非要来看姆妈不来不成的,我有啥办法,弄不过他的,他是我的阿爸爷,我吃不消他的,一碰哭,两碰气,一点点的人,脾气倒蛮大,不象我们川川的……”
“象我的。”沈梦洁半真半假地打断阿婆的啰嗦,“那件绒线外套为啥不穿,要受凉的,你看风多大,你看,拖鼻涕了……”
老太婆眼睛白翻白翻:“不是不帮他穿,你的小爷硬劲不肯穿,这个小人少见的,别人家的小人欢喜穿新衣裳,这个小鬼头看见新衣裳就喊‘甩脱伊、甩脱伊’,也不晓得啥人教出来的。”
看闹猛[10]的人全笑了,在旁边议论现今的小人难弄。
老太婆更有劲头了:“你们两个人一对宝贝,一个高飞,一个远走,屋里不要了,小人也不要了,真是少有的。小人丢给我,我弄不动了,现在外面帮人家领小人,一个月寻个五、六十块笃定的,我帮你们白看小人,还要贴吃贴用,真是蚀本生意,小鬼头一碰还叫姆妈,好像我亏待他了,你讲怎么办?”
沈梦洁本来对周川窝了一肚皮的火,老太婆还来寻事,她也火冒了:“怎么办,去问你的宝贝儿子呀,你到西藏去叫他回来呀,痒茄茄,支援西藏呢,不晓得什么人教养出来的活雷锋,老实告诉你,他不到西藏去,我也不会甩掉小人来开店,你自己心里有数,他不要屋里,我瞎起劲做啥,大家横竖横,拆牛棚,一家门翘光拉倒……”
老太婆这一下有点懵了,她的心情是蛮复杂的,对沈梦洁是又看不惯,又碰不得,她晓得自己儿子几斤几两,讨这样一个女人不容易,现在又开了店,说不准哪一日就成了财主,千万不能放手,不然儿子转来空屋一间,儿子要难过的。老太婆连忙笑起来:“说说白相的,说说白相的,啥人要讲拆牛棚,蛮好的人家,川川去了已经三年了,再熬几年就出头了。”
沈梦洁冷笑一声:“再熬几年我也熬成老太婆了。”
“你看你说得多难听,你早呢,一朵鲜花刚刚开呢。”
大家又笑了,郭小二油腔滑调地唱:“才放的花蕾,你怎么也流泪,如果你也是……”
老太婆也笑,说:“就是么,就是么,你叫这位小阿哥讲讲,你是不是好年轻的,象不象三十岁的人……”
郭小二故作惊讶,大叫小唤:“哟哟哟,沈老板进而立之年啦,照我看起来,当她刚刚高中毕业呢。”
“好了好了,别寻开心了。”沈梦洁不耐烦地说,又回头问阿婆,“你打算怎么办,小人不领了,还给我,还是要我贴你五十块六十块?”
老太婆转转小眼睛:“瞎说瞎说,他讲要来看看姆妈,我是领他来白相的,又不是来讲别样的,什么钞票不钞票,他是我的孙子呀……”
这几句话才象个做好婆讲的,沈梦洁心里想。当初不晓得周川有这样一个泥土气的老娘,她真的有点懊憹同周川结婚了。
大人烦了半天,冷落了儿子,儿子不开心,勾牢沈梦洁的头颈说:“姆妈,等一歇我跟好好婆回去。”
沈梦洁奇怪,问他:“你喜欢好婆?”
儿子点点头说:“好婆天天买好吃的物事给我吃的,还带我到大公园去乘小火车,还到动物园,还到说不出名字的地方去,姆妈没有带我去过的地方……”
沈梦洁心里一热,眼睛有点发酸,想对阿婆说几句感激的话,但看见老太太和大孃孃他们叽叽咕咕讲话,样子又土又俗,她不由叹了几口气。
阿婆进灶屋间去帮沈梦洁烧饭,沈梦洁心里一动,心想要是让阿婆和儿子都住过来,倒也蛮好,虽然拥挤一点,但可以天天同儿子在一起,阿婆除了看小人,还能帮帮她的忙,烧烧饭,省得象现在这样老是疏打饼干方便面混日脚。
吃饭辰光,沈梦洁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阿婆,可是阿婆不同意,说:“住到这边来,那边屋里不住人不灵的,不住人有阴气的。”
沈梦洁说:“不要紧的,隔点日脚去晒一晒透透风。”
阿婆仍旧不肯,停了一歇,才说:“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倘是川川刹生头里回来,屋里没有人气,冷冰冰的,他要吓坏的,当是出了啥事体了,我不高兴住过来,还是不住过来的好,这一点点地方;怎么住……”
沈梦洁没有办法,只好送走了阿婆和儿子,无可奈何地看着汽车开走了。
她回过来的辰光,看见上一次那个高个子翻译领着几个外国人手指着黑皮的“吴中宝”店招,朝那边过去了。她眼巴巴地看着黑皮在很短的辰光里又做了一笔大生意,卖出三只双面锈、一件真丝绣花睡袍,还有些红木,玉石小摆设,她不由叹了一口气。那个翻译走出“吴中宝”店堂一副得意之情。她晓得他肯定会从黑皮那里得到相当的好处,她不由对黑皮说:“老板,你花露水蛮足的么,寻到这种好帮手,招财进宝□。”
黑皮说:“沈老板你寻开心,我有什么好帮手,骚妹妹那点花露水你是有数脉的,不及你一根汗毛的。”
沈梦洁有意说给那个翻译听:“啊呀,我告诉你,那天工商局有人来寻我,问我晓得不晓得外事单位翻译吃回扣的事体,叫我知情揭发,我讲我新来乍到,怎么会知情呢,你讲是不是。”
那个翻译听沈梦洁这样敲边鼓,无动于衷,对黑皮说:“中国人里顶多的就是眼皮薄,眼皮一薄,什么事体都做得出的,告密啦,做暗探啦,这种人,到处都有。”
黑皮和他一吹一喝:“就是么,前一腔,‘古吴轩’店的姚老板看我多赚了一点,背地里就去告我,结果呢,碍不着我一根汗毛,我后来同他讲,告人,要有证据的,人证物证,不要以为凭自己瞎想想就可以去告人、咬人……”
沈梦洁想不答,狠狠地瞪了那个翻译一眼,那个人却对她笑笑,笑得十分真诚。
沈梦洁越想越气,黑皮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小青年,做生意为啥这样发落,她自己枉有一张大专文凭,枉长了一张聪明面孔,做起生意来被黑皮甩几甩也是轻而易举的,真是门对门气煞人,倘是对门的不是黑皮,沈梦洁作兴不至于这样气不平。在这条寒山寺弄开店的,也不是个个象黑皮那样精灵的,象3号“重光”店老板李江,那个老头子,就是死蟹一只了,沈梦洁虽然不大了解这个人,但有辰光走过去看看,老头子总是缩在店堂里,坐一张矮凳,只露出一对小眼睛看看柜台,一日到夜低了头,不晓得在看书还是在做啥,他的那爿店店面也十分凌乱,货架上乱七八糟堆了一点低档蹙脚货,灰积了一层,从来不去揩揩,生意自然比沈梦洁还冷落。
沈梦洁无聊得很,走到李江店门口去看看,一看,不由笑起来。李江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有一堆花白头发在柜台后而,他听见笑,抬头朝外而看看她,好像不认得,又低头看书,沈梦洁喊了他一声:“李老师,你在做啥呀?”
李江又抬头看她一眼,不说话,扬扬手里的那本书。
“哟,看书,喔哟,李老师认真得来,看什么书呀,市场学,还是生意经?还是……”
李江把书面朝沈梦洁展开,沈梦洁一看,《妇科医生精要》,她吃了一惊,以为李江不怀好意,是个流氓,可再看看他那副腔调,又觉得好笑,实在不象个心怀鬼胎的人。
“喂,”她固执地又去打扰他:“喂,李老师,你生意这样清淡,怎么不想想办法?”
李江淡淡一笑,好像说有什么办法。
“你看黑皮店里,发得不得了,啥道理,你晓得吧?”
李江不置可否,但看上去肚皮里是一清一爽的。
沈梦洁又追问:“到底啥道理?他是不是有什么名堂?私皮夹帐,违法乱纪!”
李江仍然不置可否,不吐一个字。
“什么名堂!”
李江又低了头。
沈梦洁急了:“咦,李老师,你是哑子啊,怎么不讲话的,什么名堂。”
李江又笑笑,好像根本不在乎“什么名堂”。
“你既然晓得黑皮那一套生意经,不啥不学他的样,不走他的路子,多赚点钞票,喂,你讲呀……”
李江终于开口了:“我只要日脚过得去,不想多赚钞票。”
沈梦洁听不出这话是真是假,虽然李江孤身一人,没有负担,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追求,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不欢喜钞票的人。她觉得李江这个人很特别,不再去寻他的开心了。
沈梦洁回到自己店里,刚坐定,眼睛突然一亮,她看见邱荣正从江村桥上走过来。她心里一热,突然有了一种见了久别的亲人的感觉,好像有好多话要对他讲。她不晓得,倘是现在桥上的不是邱荣,而是周川,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恐怕不一定。
罪过□,沈梦洁想,这是不是把金钱看得胜于爱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