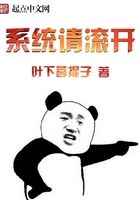一个黄昏,战歌送呼延书南到达了一个小镇,离云州不到半天路程。进了云州,再穿城而过,再走十天,就到了呼延书南王庭所在。
云州,燕云十六州之一,目前是呼延书南的二叔呼延赞在此驻守。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了乞奴的武力范围。
只是,不知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呼延书南带一行人住进了呼延书南的秘密别院,高太后已命大批随从假扮商人等于此地,先前那几百人的商队也在其中。
这几天一直在下雨,虽不大,却细细密密,路上泥泞不堪,每个人穿上簑衣,却挡不住细雨的浸入,衣服又湿又冷紧贴皮肤,象裏着枷锁一般,很不舒服。
今天,战歌总算泡了个澡,换上了女装。从现在起,她暂且充当呼延书南的贴身侍。
仆妇将战歌引至饭厅,凌尔白在门口请战歌进去。
呼延书南早在饭厅候着战歌。
战歌一身乞奴女子的装扮,紧身窄袖,大红夹衣,黑色灯笼裤,一件白色带毛边的小袄把战歌的腰身勾勒得凸凹有形。
才洗过澡,战歌双颊微红,吹弹可破的皮肤衬着灵气逼人的双眸,转眄流彩,光润玉颜。
呼延书南吹了声口哨。
“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他半真半假道:“姑娘可愿随了书南?”
战歌乜了他一眼:“我若随了你,你就不怕夜半惊魂?”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书南固所愿耳。”呼延书南一双含情笑眼柔情似水。
“妖孽!”战歌在心里骂道。
“做鬼么,容易得很。出门左拐,有个池塘。”战歌恨道。
呼延书南作捧心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姑娘好狠的心!”
一个“心”字还未落下,呼延书南忽然一扬手,一掌击向屋顶,站在一旁的战歌呼吸滞了滞。
好强的内力!
“呯!”一条黑影坠了下来,差点砸在战歌头上,呼延书南再拍一掌,那黑影斜飞出去重重摔在墙上,再软软委顿在地。
这是战歌第二次见呼延书南出手。
第一次是初遇时他反手一剑直插刺客胸口。
两次出手都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战歌心内微惊。
凌尔白听到响动,破门而入,见一人倒在地上,忙跃上屋顶查看。
战歌道:“怎地已近云州,刺客还敢偷袭?”
呼延书南嘲讽一笑:“就是因为已近云州,才胆子更大。”
“你二叔……”
“对,我二叔。拜他所赐,书南才更是处处受关照。”
战歌叹道:“无情最是帝王家。当初你二哥也是拜你所赐,才命丧北地。”
呼延书南无赖道:“我那好二哥可不是我关照的。他不是命丧安北将军之手吗?”
战歌气结。
呼延书南呵呵一笑,道:“说起这个,安北将军恐怕得委屈改个名字,换个身份。”
战歌略一沉思,道:“就唤我照君吧。”
这是战歌醉心中国国学的母亲为她取的字。
“愿逐月华流照君。好,正合我意!”呼延书南深情款款地望着战歌。
看来他已熟读汉华大皇子华昊的诗词集了。
战歌避开他的眼神,道:“明天即进云州,高公子可作好准备了?”
“有照君在,书南放心得很。”呼延书南涎皮赖脸地说。
战歌很想照他那张俊脸搧一巴掌。如果不是为了一探他王帐的虚实,真想带着飞甲军就此回北地。
……
第二天中午,一行人到达了云州。
城门上「雲州」两个大字泛着岁月的苍凉,似乎在无可奈何地诉说着被迫易主的无奈。
凌尔白上前交路引,又唤城税司来计算税金。他们的身份是来此地做生意的商人。
虽说战乱频发,但杂族人仍需大量汉华南地的丝绸茶叶等物,所以士族门阀仍有特殊渠道与杂族人有商业往来。
这些商队背后,多有杂族贵族的支持,或者说干脆就是某些杂族贵族敛财的重要渠道。比如当初李太后和李丞相就是以此为条件,放了完颜阿骨烈的。
而云州的呼延赞便从中抽取重税,故而商队可顺利入城。
等候期间,呼延书南与战歌坐在车里。这是在别院换的一驾马车,是高太后为呼延书南准备的。
车子外面毫不起眼,普普通通的毡布围帏,车里却是白狐皮铺地,白玉为案,香楠为柜,处处都是价值连城的物件装饰,却不显张扬。
看来高太后也非常人。
呼延书南在泡茶,他姿态从容,嘴角含笑,满脸春色。
纤长的手指优雅灵活,动作娴熟,车厢里满是清香的茶味。
战歌悠闲地喝着茶,面上欣赏着呼延书南的无双气度,心里却想着宁王,不知战况如何,他是否安好。
呼延书南抬眼瞥了一眼战歌,轻笑一声。
战歌回过神来,瞪着他。
呼延书南无可奈何地说:“似乎应该是我来品茶,照君泡茶才对吧?”
战歌干脆利落地答:“我不会。”
“作为贴身女侍,书南不介意亲手教导。”他加重了“贴身”两个字,带着他特殊的有如泉水流淙的声音,邪魅地说。
战歌嗤鼻。
“也罢,就由书南为照君泡一辈子的茶如何?”
“哦?高公子愿放弃汗位,做我茶僮?”
“兼作夫君倒也可以考虑。”
战歌眯了眯眼。近日呼延书南越发放肆,战歌思忖他的目的。
“书南真心倾慕照君,为何不考虑考虑书南?”
“我正在考虑,我与宁王是否真是在与虎谋皮?我看高公子已有闲情逸致,要不我今日告辞如何?”战歌一哂。
呼延书南意味深长一笑:“书南的王帐可是正准备迎接宁王安北将军大驾光临。”
战歌却觉心内不安,呼延书南到底想干什么?
一时事毕,凌尔白引大队人马进城,去客栈投宿。
路上,战歌从窗帘往外看,云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市阜,比建水自是差远了,但在北地也算比较繁华了。
街上随处可见着乞奴服装的人趾高气扬,汉华人面黄肌瘦,神情麻木,在乞奴人的淫威下唯唯诺诺,毫无骨头。乞奴人一走,转身又去欺凌更弱的汉华妇幼。
战歌气闷的放下窗帘。
呼延书南斜靠在铺着纯白狐狸毛的坐榻上,见战歌一脸沮丧,他玩味谑道:“人人可欺我,我可欺人人。你们汉华人不都是这样?”
见战歌一张俏脸寒气逼人,涎着脸凑近战歌道:“你欺我可好?书南愿意一辈子被照华欺……”
“好啊,”战歌往后靠了靠,似笑非笑,“我欺你,让你从此远走草原,永不踏入汉华一步。”
“照华陪书南远走草原,永不踏入汉华一步?昭华不会想北地千里沃野,万里江山?”呼延书南大惊小怪。
战歌很想将那张人神共愤的脸揍成猪头:“大白天的做梦呢!我和你桥归桥路归路,别扯上我。”
“那可不行。如此,昭华怎生欺我?”
战歌实在不想和这徒有其表的二货啰嗦,扭头又看向窗外。
一个满脸黑泥,瘦弱纤细的半大孩子,穿着看不出颜色的袍子,正被一群仆妇抠打,几个衣着华丽的乞奴女子神情据傲地倚马看着,中间那女子身材高挑,小麦色的皮肤,眉目深遂,手握马鞭,满脸不耐烦。
呼延书南从战歌耳边伸手过来,“唰”一下拉下窗帘。
战歌一脸错愕地回头看他,嘴扫过呼延书南的下巴。
呼延书南心猛地一缩,战歌尴尬地呵呵。
“那个,呃,怎么啦?”
“那是冒顿的亲表妹加堂妹,她母亲与我父王的大阏氏是亲姐妹,也是呼延赞的王妃。”
嗬,好显赫的家世。
战歌在脑中转了几转,才想明白关系。
“那,也是你的亲堂妹嘛!”
“也算,不过我父王和呼延赞不同母。”
“呃?”战歌不太乱得清这关系,她从来没有亲戚。
书南难得见战歌一脸迷糊,想伸手捏捏战歌的脸,终是忍住了,抬起的手碰了碰自己的下巴。
战歌眼珠子骨溜溜转了转,“别是你惹的风流债吧?”
呼延书南一脸厌恶:“蛮女!”
也是,呼延书南的母妃是汉华名媛,与一般的乞奴女子自是天差地别,教得呼延书南也是儒雅贵气。
战歌若有所思地看着呼延书南。
呼延书南疑惑地理理衣服,有些不自在。
“其实,你母后是汉华人,你理应对汉华亲近些,为何……”
“为何认贼作父?”呼延书南嘲讽一笑:“我父王疼爱我母妃,对我也是万般溺爱,他雄才大略,是草原之鹰。书南自小在草原长大,除了这张脸和汉华人无异,书南早已是草原之子。”
战歌诚恳的说道:“高公子误会了。我并非说你认贼作父,谁都没有选择父母的可能。而是说你身上即有汉华血统,为何对汗华人也如此残暴?”
“残暴?”呼延书南眼神迷茫。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不是天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