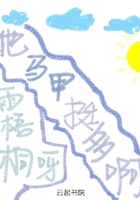“那种感觉是很不好受的,你站在那,周围都是人,你喊啊叫啊,可他们都像聋了,瞎了。你去打他们,他们就像棉花,你打不痛他们,他们也不在乎你。你想离开,他们又把你包围地团团转。就像在太空。”
鹿游因为绝食昏倒在课堂上了,她的老师吓坏了,以为家里有人虐待她,想帮她报警,也许那算是个逃脱的好机会。可鹿游没听懂,也说不清,王东明说她在减肥。那金发碧眼的外教看着瘦削的鹿游,怀疑这说辞。但等周放出现,他镇定自若又满怀歉意的绅士模样又完全说服了她。
“她也不是在减肥,她是太担心我了。我生病了,她吃不下饭。今天早上她没吃早饭,低血糖,昏倒了。”
鹿游就在一边看着,她听不太懂,不然她一定愤怒地把周放的嘴撕裂。
经过周放的解释,外教看鹿游的眼神就变了,她像在看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并怜惜道:“神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那外教还给她一根拐棍糖,樱桃味的,特别难吃。
因为昏倒了,鹿游被送进医院做了例行检查,打了一瓶米白色的营养液。周放全程陪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像在拔河。只有王东明在滔滔不绝。
“你真不应该这样,老周把你们托付给我照顾,按理说我也应该和你们住在一起,只是景仁不让,才作罢。要不是他跟我说,我还不知道你在闹绝食!这是好玩的吗?!”王东明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一起了。
王东明是国外的分公司的经理,一干事物都是他在打理。他大约四五十了,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接机那天鹿游见过,那小家伙在鹿游身上又跳又叫,吵死个人。
鹿游躺在床上,不甘心地发问:“我妈去哪了?”
“在国内,办着签证呐。”王东明回答。
“她根本就不来了,三个月过去了!”
“你还在这,她会不来吗?”
“那为什么不让我给她打电话?!我回国也不许。我不会说英语,也没有钱,现在除了上学,哪也不让去,为什么?!为什么?!”鹿游大叫,要把她的针管拔下来,“你们这是囚禁,我要自杀!自杀!!”
鹿游吵闹着,把护士引了来,可她不会说英语,张嘴闭嘴只会说是杀啊死啊,护士以为她犯了精神病。
最后周放终于开口,“你想知道你妈去哪了?”
鹿游瞪着他。
“我告诉你,然后你就会好好吃饭吗?”
“会!”
“睡觉呢?”
“会!你告诉我,我再不会闹了,你告诉我,我妈去哪了,为什么不来了?为什么我联系不了她?!”
“好。我帮你去问问,你乖乖的,好吗?”
即便鹿游知道那可能是假的,她还是答应了,她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定下了协议,日子就好过许多。但鹿游总惦记着她妈的事,差点害了厌食症。无数个寒冷无人的清晨,鹿游都扒着马桶狂吐不止。
杨保姆是唯一一个同情她的人。
上一个目睹鹿游怒砸会客厅的保姆已经辞职,这是一个新的。她姓杨,女儿把她办过来,她在这,吃喝不愁,就是闲得头皮发麻,于是给人当保姆,她来应聘的时候就是鹿游招待的。说起来也算不上应聘,是两方都对对方进行一番考察,人是王东明给联系的,杨保姆来的时候他却又迟迟不现身。
鹿游和杨保姆在餐厅呆坐,都有些尴尬。
“你不去上学吗?”杨保姆问。
“啊,哦,我,我现在请假了。”
“怎么了?”
“我生病了,经常吐。他们不让我上学了。”
“他们是谁?”
“他们,他们就是,王东明,你认识吗?”鹿游回答。
“当然认识了。我听说你和你哥哥一起住,是吗?”
鹿游点点头。
“那你们都爱吃什么?高级的我不会,我只会做些家常菜,你爱吃辣吗?我做菜可能有点辣。”
鹿游怔了一下,“我什么都行,我不爱吃白萝卜。”
“你哥哥呢?”
“我不知道。”
杨保姆露出困惑的神情,她又说:“我听说他也有病。”
“啊,对。”
“是什么病?有忌口吗?”
“啊…我,我不知道。”
“哦…那…”
本来杨保姆已打了退堂鼓,因从进屋她就觉到一种不友善的冷气,再见这屋中的小主人,更是和这屋子融为一体。但不料,正当杨保姆想要起身告辞时,鹿游突然说起话。
“您喝水吗?我该给您倒杯水的。”鹿游已站起身,“不好意思,我忘了。”
她想快点起来,却被椅子困住,起身的时候差点摔跤。
瞧着鹿游细瘦的身板在厨房里游荡,杨保姆突然有些心疼,她问:“你多大了?”
“十五。”
“上的什么学?”
“该上高中。以前我在山里,没有爸爸。后来有了爸爸,他还很有钱,就送我出国,到了这。我现在在学外语呢,一点都学不会,他们叽叽呱呱,我什么也听不懂。”鹿游断断续续地回答,若是往常,她大概不会这样,现在太久没有人愿意好好听她讲话了,因此她显得有些激动和语序紊乱。
她将一杯水放到杨保姆面前,“真不好意思,您再等一等吧,王叔叔平时很准时的。”
正是这段话,让杨保姆决定留下来,她得照顾她,杨保姆是这么想的。
鹿游和杨保姆学了些做糕点的手艺,她不怎么上学,每天在家看书,反正书房里的书是应有尽有。等杨保姆来了,她就和杨保姆并肩坐着,一边盯着烤箱,一边坐在太阳底下聊天,现在的鹿游,已经胖了不少,气色也好了许多。
杨保姆说她是东北来的,女儿很早就送出来,嫁给了一个华裔,是她的高中同学,两个人住在隔壁市,偶尔来看看她。
“但她那个老公已经不说中文了,也是叽叽咕咕的一嘴鸟语,我听着就心烦。他也不会写中文,只会听会说。用我闺女的话说,他是个香蕉人,外黄内白,明明是个中国人模样,操的都是老外的心。他老早跟着他的爸妈出国,还信基督,阿弥陀佛,每个星期要去做礼拜。”杨保姆边说,边露出难以理解的神色,“咱们习惯不了。”
鹿游笑:“姨姨,我想吃麻辣火锅。”
“不能吃,那嘴里两个大泡。”
“那我想吃麻辣兔头。”
“不行。”
“麻辣鱼。”
杨保姆气笑:“你看我像不像麻辣鱼?!”
虽然杨保姆这么说,中午还是开车带她去吃麻辣鱼,要了一份清口麻辣鱼。她说起之前在白人区吃过的左宗棠鸡,咸咸甜甜的。
杨保姆问:“那里那么远,怎么搬到这边来了?”
“之前住的那边是公寓,让我砸坏了。公寓的人生气,把我们撵出来了,反正我在哪读语言课都一样,才又搬到这来了。这里中国人多,可以打车去超市逛逛,比之前强。周放说他要看病,现在大概住在医院边上,才不怎么回来。”
杨保姆知道她不喜欢提起那个哥哥,于是识趣地别开话题。
“你砸成什么样了?”杨保姆握着鹿游的手腕笑,“瞧着小胳膊小腿,还不一下给掰折了。”
“我可是大力士。”鹿游笑,“因为我很生气,我生气得力大无穷,像吃了菠菜罐头。”
“什么罐头?”
“就是大力水手吃的,菠菜罐头,吃完了就有很大力。我抄起高尔夫球杆,原地转,像个大陀螺。噼里啪啦的,都砸了,这是我的大招,谁惹我生气,我就拿着球杆旋转。”
杨保姆笑,觉得这是鹿游在说胡话。
她觉得鹿游是经常说胡话的,她还见过鹿游在夜里对着院子里的树说话。那时她开车开到一半想起包落到鹿游家,想着第二天再拿,但鬼使神差又开回去了。一进屋看见院子里灯光明亮,好奇地过去看看。
她看到鹿游穿着睡衣坐在院里的铁椅上,仰着头,嘴巴一张一合,正对着树说话。她完全没发觉杨保姆来了,杨保姆隔了几米,听她絮絮叨叨的念:
“我想回家,想回果子坡,想去见见宋嘉,姚月,张菲菲。以前我们一起扒着大巴到县城去,一逛就是一整天。我们最爱逛银祥园,那里是个服装批发中心,有几百个小铺,卖什么的都有。我们一个个的看。我有一条很想买的白裙子,可我不敢买,买了穿不上。首先干活是穿不上的,上学,那又要走很久的路,白裙子怕脏。何况我也买不起。我记得那条裙子,才一百三十块钱,合,合二十刀,好便宜。”
“后来有人来接我,说我有爸爸了,还很有钱,起初我还不信。原来他真的很有钱,我去逛街,那商场大极了。比县城里的商场都大,金碧辉煌,走廊都有十几米宽。每个店进去就有服务员,端茶倒水,点头哈腰,也有长得很好看的,说话柔声柔气。也有狗眼看人低的,我泼了一杯水在她身上。”
鹿游边说,边叽叽咕咕地笑起来。
那次杨保姆把她骂了个狗血临头。一个因为她半夜不睡觉在外面装神弄鬼把自己吓的不轻,二是她穿着单衣坐冷板凳隔天一准受冻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