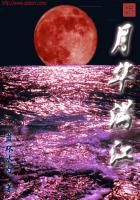这个声音,是我一辈子的梦魇,我恨之入骨却又藏匿至深。
不敢回想的过往。
那一夜,我的清白被毁。
只因那一夜,娘三天三夜高烧不退,最终离开人间。
“大胆奴才。”
“恩恩?快跪下,恩恩?”
“刁奴,竟敢直视皇上,还不快跪下?”
我听不清周围的人在说什么,缓缓地直起身子,目光的焦点定在了那个明黄的人脸上,深邃如夜空的眸子隐藏了记忆中的锐利,却依然叫人不敢直视。
这是一张能叫女人轻易动心的脸。
可对我而言,是妖孽,是魔鬼。
记忆如潮水而至,点点滴滴,越发清晰。也带起了我隐藏在心底深处,刻意淡忘的恨。
只是万万没想到,那个毁了我清白,间接害死我娘亲的人竟是当今的皇上,年仅二十七岁的肃帝。
一个我恨不起的男人。
我的震惊与不信可想而知,但这个声音与相貌,千真万确,是那个毁我清白的男人。
我握紧拳头,指甲几乎掐进肉里。
他高高在上地坐着,只是冷冷地扫了我几眼便自顾自地喝着宫女送上的茶水,仿佛并不认识我。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将她拉下去?”明妃气得不轻,香肩也隐隐颤抖着。
“皇上请恕罪,恩恩进宫不久,不懂宫里规矩,请皇上从轻发落。”素姑姑叩头为我求情,声音里满是紧张。
两名太监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拖着我就往外走。
我强行扭转脖颈,如果目光是刃,只怕他已死在刃下无数次了。
泪夺眶而出,那夜,我无法为自己失去的清白讨回一个公道,就算找到了那人,如何向一个上青楼寻欢的男子讨公道?
我并非软弱之人,但这个男人,竟会是天下至尊,所料不及,所有的苦恨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可是,至尊又如何?就算他权倾天下,我也同样能恨他。
“慢着。”他突然开口,起身走了过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神情冷漠,“你恨朕?还是,这是你为了引起朕的注意所使用的手段?如果是,你成功了,演得很逼真。”
手段?演得很逼真?他以为我在演戏?以为我这么做是想引起他的注意?我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他,生平第一次,有想揍人的冲动。
他竟不认得我,一个曾被他强夺了清白的女人。
“皇上是要收了她吗?”明妃明明在他身后冷怒地瞪着我,说出的话却娇柔无比,“若真如此,臣妾可要恭喜皇上了。”
“她是引起了朕的注意,可朕是不会将像她这样的人留在身边的。”他朝架着我的两名公公挥挥手,“带走。”
“皇上,一切都是奴婢的错,是奴婢教导无方,您要降罪就降在奴婢身上吧。”素颜姑姑冲了过来,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皇上,求您饶了她吧。”
“素颜,你自己还是个戴罪之身,凭什么为了一个为博得皇上注意而玩弄心计的洗衣女求情?”明妃偷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见他并无所动,喝道,“来人,将素颜拉出去。”
“皇上,恩恩不是那样的女子。”在公公即将抓过素颜的手时,她突然道,“十一年前,皇上曾许诺奴婢,只要奴婢他日有所求,定会应允奴婢一个要求。尽管那时皇上年少,但君无戏言,望皇上能够践诺。”
素姑姑?我心底一阵感动,我与她并不熟稔,虽入洗衣局也近半年,但这半年来所说的话寥寥无几,为何素姑姑要待我如此之好?
“你将朕赐给你的机会就这么用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洗衣女身上?”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嘴角挑起一个讥讽地笑,似在嘲笑我眼底流露的感动。
“是。”
“那好吧,朕就当此事从未发生过。”
“奴婢谢皇上恩典,虽说皇上当此事从未发生过,但奴婢怕其他人惹起无端是非来。”
眼角余光看到明妃一脸铁青,在皇帝面前却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柔弱的模样,柔声道:“素颜可真会多想,既然皇上已说当此事从未发生过,其他人又怎敢违背皇上的意思?”
“既然娘娘这么说了,奴婢这心也就放下了。奴婢代苏恩谢皇上和娘娘的恩点。”素颜磕头谢恩,“奴婢告退。”
雪亮得刺眼。
我闭了会儿眼才适应满地明晃晃的白雪。
素姑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静静地在前头走着。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底沉重万分,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半年的时间,那一夜的屈辱我以为已经藏匿在心底慢慢淡化,可没有想到在听到这个声音时一切都乱了,藏匿的记忆再次痛苦地展现在面前,那一刻除了恨别无其他。
明明知道他是皇帝。
明明知道惹了皇帝是要没命的。
“别再想了。”走在面前的素姑姑淡淡开口,“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都将它忘得一干二净,这里是皇宫,你只是在这里拿俸禄做差事而已。”
“姑姑,谢谢你。”我再次湿了眼眶,皇帝的允诺,那是天大的机会,素姑姑却用在了卑微如我的身上。
“每一个人进奴洗宫,我都会静静观察她们,这么多年来,你是唯一一个做事认真,不懒不拖,一年如一日本本分分做事的人,”素姑姑转身,笑望着我,“想抓你短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人又怎会耍什么心机呢?”
“姑姑,我……”
素姑姑摇摇头,“我对你在宫外发生的事并不感兴趣,我刚才说过了,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事,都将它忘得一干二净,这里是皇宫,你只是在这里拿俸禄做差事。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吗?那一夜所受的痛苦和屈辱,娘亲的离世,一切的仇恨都将消失。
做得到吗?把这一切都忘记,不是深藏心底,是真正的忘记。
这里是皇宫,他是皇帝。
做不到又能如何?
素姑姑望着我紧捏成拳的双手,叹了口气。
我黯然地望着地面,咬紧下唇。
做不到,就算那个人是皇帝,我也做不到不恨。
“请姑姑将恩恩从管分处调回洗衣局洗衣吧。”只要不出洗衣局,我就不必见到他,不见到他自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
这辈子,我与他最好不会再见面。
素姑姑点点头,“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就跟我说一声。”
年后的十天,每夜都能见到天空烟花五彩缤纷,一碧千里。那是宫里的主子们在寻欢。
而我则是每夜在小竹林中孤身一人遥望炫彩夜空度过。
仅仅十天,我就瘦了一大圈。
元宵节那天,我终于调整好了心情。
娘临死前要我快乐地活下去,我既然无法放下清白被毁的恨,那么也不该在怨恨中过日子。
既然答应了娘就该做到。
“看到你笑我就放心了。”素颜姑姑带着几名洗衣女从我身边走过,见我朝她微笑,她松了口气。
我用腰间的围裙擦去手上的水珠,朝素姑姑施了一礼,“这些日子让姑姑操心了。”
素姑姑点点头,“没事了就好。我去趟皇后宫里,一会儿就回来,屋里有几件娘娘的衣裳,你为人细心,就交给你了。”
“是。”
目送着素姑姑离开洗衣局,我进了正堂,刚进堂内,就见一小洗衣女慌张地将什么东西藏入了衣裳内。
“你在做什么?”我心底疑惑,要知道正堂内放着的都是各宫娘娘们的衣裳,虽然只是小小的衣裳,也不容有任何闪失,要是破了个洞或是开了线,轻则木棍侍候,重则处死。
“没,没。”小洗衣女双手乱挥,脸刷地一下变白。
我朝摆放衣裳的地方看了看,看不出什么异常,可见洗衣女慌张的样子,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我先走了。”
“慢着。”我喊住欲离开的洗衣女,双手将她刚才碰过的衣裳翻了个面,果然,那件丝绸衣料的华服上断了几根丝线,只要再动一下,则触一丝动全身,这衣裳怕就要报废了。
“姐姐,我不是有心的,求求你不要告诉素姑姑,呜呜呜……”小洗衣女跪在地上大哭,极为害怕。
“这衣裳是哪个宫的?”
“是,是柳妃宫。姐姐,求求你不要告诉素姑姑,我,我怕被罚,呜呜呜……”
我扶她起来,心情也变得沉重,“我若替你隐瞒,那受罚的就是素姑姑,你忍心吗?”
“那,那怎么办呢?”
我细想了下,也只能如此了,半年未碰绣活,不知道生疏了没有。
“你有针线吗?”
她摇摇头,“我没有,不过绣衣坊有。”
绣衣坊与此地隔了一个长长的甬道,来去也得一炷香的时间,素姑姑去了皇后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又见小洗衣女既害怕又期待地看着我,我只好安慰地朝她笑笑,“没事的,你在这里等我,无论如何,这件衣裳也不能叫人拿去柳妃宫,知道吗?”
小洗衣女点头。
黄昏,整个皇宫笼罩在晚霞的光环中,美不胜收。
今天是元宵节,宫里每一处都挂起了大红灯笼,一片喜气洋洋。
我无暇欣赏黄昏的美好,心底也无半分喜气,只想着一旦拿到针线该如何将那衣裳恢复原样。
甬道极长,每隔十几米就是一道圆门,圆门内不是院子就是殿堂,往内望去,也是隔了诸多的风景才能看到殿堂的顶端。
宫女太监纷纷从身边走过,彼此也不打招呼,默默地走在这一条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甬道内。
偶有几名神气的宫女太监走过,其他的人纷纷向他们微笑示好,他们却回以冷眼,这些人不是得宠娘娘身边的宫人就是数得上妃位娘娘身边的红人。
偌大的皇宫,人情冷暖,比起宫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抬头望向天空,甬道上的天空一如这窄窄的甬道,也只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的蓝条。
我要在这蓝条下过上十年。
突然间,胸口感到很闷。
“回避——”尖细的声音喊破了静寂。
一顶轿子抬了过来,是某位娘娘路过。
我与所有的宫人一样,在一旁施礼,直到轿子过去才起身。
绣衣坊近在眼前,只要过了那个圆门就是。
我加快了步伐,就在快到圆门时,远远地瞧见一顶黄色的轿子抬了过来,路边的宫人纷纷下跪。
若是娘娘路过,只需施礼。
跪,只对皇帝。
双手下意识地攥紧,那个男人?不想向他下跪。
轿子越来越近,我听到了公公的喊声由远而近,“跪——”
咬牙一闭眼,我转身进了身旁的圆门,加快脚步,到最后几乎是用跑才将那“跪——”的喊声远远地抛在脑后。
已决定不再去想那过去,决定了要快乐地生活下去,可这会儿还是有些莫明的伤感。
停下脚步时已气喘吁吁,我跑得很快,很急,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将那伤感稍微淡化些。
平息气喘,我直起身子时,却与一道冰冷的目光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