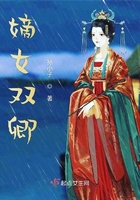血迹一洗就掉了,石头表面粘的沙子、污迹也一起洗掉了。用毛巾包起那块石头,擦干,再打开毛巾,洗掉了沙子和血迹的石头,并没有像宝石般闪亮,也没有像什么蛋似的诞生一只奇异生物,也就是平淡的石头而已。高桥返回客厅,把石头放在桌面上。刚才染了血的样子,蠢蠢欲动,令人产生不祥之感,不挺好吗?平平淡淡一块石头没意思。阿惠在刚才那张纸上写东西,对高桥说声“谢啦”。阿惠写的是“捡石头日记”之类的东西,她写下捡到时的情况,和石头一起存放起来。高桥也曾说,那就只写日记也行吧,可人家说“那不一样”,置之不理。
“这石头带血更好吧?”
“为什么?”
“我不是在写日记类的东西吗?那么,‘泡澡时被刮胡刀弄伤’,也真算一则奇闻,而这块石头置身那个刺激场面,就让它带着血,记下‘沾上了阿渡洗澡受伤的血’,这一来,就是两个人的回忆——两人专有的记忆了吧?我觉得,把它作为两人含蓄的爱情结晶留下来,挺好的吧……”
高桥又浮现了会心的微笑,但阿惠没笑,只是灵巧地骨碌骨碌转动指间的钢笔,她视线移动的次序,依着纸张、电视机,到空中,再到高桥的膝盖,然后是电视机、石头。她嘴里“嗯”一声,在想着事情。
“说起来是不好听。可是,也确实吧……确实是吧。沾了血也是今天发生的嘛。留下带血的石头,也会有的吧。”阿惠像是自言自语。
“对吧,可惜了。”
在高桥说完以前,阿惠拿起石头从沙发站起来,在地板上坐着的高桥旁边蹲下,拉起他右边裤脚。“你干什么?”高桥稍微抗拒了一下,但阿惠一句“还有血吧”让他愣住了,便由得她了。阿惠撕开高桥的创可贴,把石头按在那个地方。随着痛楚,干了的伤口又开始渗血了。阿惠让石头蹭上血,笑着说“谢谢”,返回沙发上,拿起钢笔又在纸上写起来。
“明天面试吧?早点睡为好。我明天是夜班,你先睡好了。”
高桥看了一会儿又开始冒出来的血和阿惠,发现时针已经过了一点,就重新贴好创可贴,上床去了。
高桥逆着水流的方向,走在沿江路上。有大学生坐在江边长凳上练习吹小号,隔着耳机听得见漏气的号音。因为昨天的伤口与裤子摩擦会疼,他右脚不使劲,慢慢蹬自行车。他想,那号音跟听的曲子没关系,不知为何感觉挺好的。因为蹬了三十分钟了,出了点汗,他松开领带,让风吹进来。满眼是不知名的杂草,散步的长毛狗,度过了新生欢迎会及黄金周、稍微安顿下来的几组大学生情侣,和河水的颜色,作为一个整体,令人有初夏的感觉。
落选了吧,高桥心想。原想今天该用“我”的,岂料初试就有五位面试官,因此太紧张了吧;或者因为一开头其中一人就发言批评飞特族[2],于是就畏缩了吧,最终说成了“鄙人”。话一出口,这个总觉别扭的“鄙人”,渐渐就“鄙人呢……鄙人呢……鄙人呢……”起来,干扰了自己,这样一来,感觉也好,对话也好,都乱七八糟了,连前一天练习过的也忘了,最终一位面试评审说“你也不小了,该当真考虑一下找工作的事”,这其实是“我们公司不会录用你”——完全不予考虑的意思。高桥再扯松一点领带,忍痛蹬得快一点。
回到家,阿惠已经出门,桌上有一张字条:“忘了今天中午也有兼职。晚上也要打工,所以不要煮我的晚饭啦。有空的话,找一下猫。”高桥到寝室换成针织裤子和T恤,脱下的西服在房间一角的衣服架上挂好。衣服架旁边的钢架子上摆着一溜石头。以前这里摆的是高桥的CD和书,自从阿惠收集石头之后,就成了石头陈列架。阿惠每次捡回石头,高桥的书和CD便顺次被移到下一层。现在,五层的架子已有四层被石头占据,高桥那四层里的东西,不得不堆到最下一层;放不下的东西,就无所谓地堆放在架子旁的地板上。高桥从排最后的、昨天沾了血的石头下,抽出便笺纸。
X月Y日
今天,在美味蛋糕店“果果”前的树下拾得此石,是上班前和客户去的。店里的柚子夹心蛋卷放了草莓和蓝莓,堪称绝品。当晚沾了阿渡的血。
读完了,他把便笺纸放回石头底下。便笺纸上,记下了高桥所不知晓的阿惠的日常生活。只是从便笺纸放的位置来看,明显是不妨为人所知的内容,不会是全部。为何特地将便笺纸放在看得见之处呢?高桥凝视着几排石头。可能这些家伙比我更加了解阿惠。他对此有点儿嫉妒。高桥没心思再看石头了,穿上衬衣出门,见对门的山本大婶在清扫大门口。
“哟,是高桥,出门呀?”
高桥和阿惠搬来这个排列着相似平房的城市,唯一有交往的近邻,就是山本大婶。几乎所有邻居都觉得没有正式工作的高桥二人形迹可疑,只有点头之交,惟有山本大婶从一开头就很爽快地搭话。起初高桥烦她说话直通通,但每次见面她都搭话,不知不觉中高桥二人有时也主动跟她说话了。似乎山本大婶的儿子也跟高桥年龄差不多,在东京大学毕业后,没去找固定的工作,晃晃悠悠说要当电影导演,因此她也没视高桥为异类。
“对了,刚才见你穿正装回来,找到工作了?”
“还没有呢。”
“快找好工作,让阿惠开心呀。阿惠晚上很晚回,比你干得多吧?”
山本大婶没有动扫帚的意思,似乎要跟高桥聊聊的样子。
“那可不行哩。该振作啦。对了,之前电视上有说,嘴里衔一双筷子,每天练习五分钟做笑脸,就笑得自然了。我之前就感觉到啦,你有点儿不够和蔼可亲。练练笑容。第一印象很重要——面试官在电视上说的啦。——你从今天起就练练。”
高桥没法说自己看了同一个节目,已经立马付诸实践了。
“是吗。那我试试看。啊,我得走啦。”
“你去哪里呀?”
“去找找猫。”
“你还在找呀?好悠闲——找工作比找猫优先啦。”
“可阿惠说找找看。大婶看见过吗?”
“那只猫,之前还不时见它一闪而过,最近完全见不到了。去别处了吧?”
“是跑掉了,所以找它呢。那我出发啦。”
再扯下去,这山本大婶恐怕又倒腾出什么话题了。高桥急忙跨腿上车,说声“再见”,左脚一蹬地面。
心里还想着完全无效的衔筷子练笑容法,就到了图书馆前面。这里是北区的中心位置。高桥为了找猫,从网上打印了地图,以住处为圆心画了一个半径一公里的圆圈,把它东西南北四等分,找猫的日子,每天跑完一格。之所以定半径为一公里,是高桥的自作主张:那么懒的动物走不了多远。这两个月来共找过十二天,也就是说,四格都已找过三次了,今天是第四次在北区搜索。迄今的收获近乎零。只一次在南区见一只相像的猫走在民居的围墙上,但想靠近看,骑车过去时,警惕的猫逃进了自行车不通行的小巷,他想追,停好自行车时,那猫已经不见踪影。高桥考虑到上下自行车的缺点,自此总是步行找猫,以便随时可以追捕。
他把自行车停在图书馆的自行车停车处,开始走动起来。他决定今天先往北走。市镇像一个围棋棋盘,道路笔直,住宅、停车场、杂居楼、住宅、停车场……两边街景如此这般一成不变地重复,高桥就在此中寻找小猫。说是在找,可高桥对猫的习性一无所知,对这种生物会在什么地方走动也不甚了了,充其量就是在那一带转转而已。那猫原先也不是自己养的。它是一只野猫,约两个月前从窗口溜进来,不走了,阿惠很高兴,买猫食给它,但它过了一周左右,又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去不回头。就那么一只猫而已。对于高桥,这事无所谓,但阿惠无论如何都想找回它,高桥便勉勉强强出来找。
寻找猫中间,高桥想起有一部电影叫《小猫失踪》,他实在想不起导演是谁,很不甘心,从兜里掏出手机,要问问喜欢电影的设乐。
“怎么了?”传来设乐没睡醒的声音。
“你在睡觉?”
“没有。起来了。”
“这是工作日的大白天啊,你真是!”
“别烦人。哎,啥事?”
“没啥事,那个《小猫失踪》的导演是谁?”
“这是工作日的大白天啊,没别的要问吗?”
“工作日的大白天,没啥问你的。”
“有啊。那个嘛——之前的电视节目,说嘴里衔着筷子练习笑容,会有一张成熟的脸,人家公司爱录用呢。你试试看?”
“我说你,要那样就能找到工作,你早就在工作了。”
“也是。说着就想起来了——那导演。是塞德里克·克拉皮斯[3]吧?”
“噢噢。你看过那电影吗?”
“看过啊。”
“怎么样?有趣吗?”
“我也是大学时看的,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一个找猫的人寂寞地寻找自我的电影。噢,因为你正在找猫吗?”
“没错。”
“呵呵,你也在寻找自我?呵呵,怪不得怪不得。快找快找!把自己好好弄清楚,可能会有好事哩。”
传来设乐的嗤笑声。
“呵呵,我来找啦。找找猫和我自己。说不定跟大便一起拉在那边了。”受设乐的笑声传染,高桥也哼哼着笑。
“好,总之弄清楚了,是克拉皮斯嘛。Thank you.”
“嗯。哎,猫无所谓啦,明知靠不住,你也试试那衔筷子吧。”
“好吧,上当一回试试。”
“还有,这么长时间,跟阿惠亲热过了吗?”
“没——有啦。就这样吧。”
电线杆周围,摆着撕去商标、装了水的塑料瓶。这大概是有人摆着防猫的吧,高桥踢倒了其中一个瓶子。跑到家里来的猫,大模大样就睡在矿泉水旁边。这些人也受骗了吧。又踢了一个瓶子,它发出吱吱吱的声音,横着滚到一边去了。拿购物袋的大婶和西装革履的大叔对高桥侧目而视,走了过去。高桥一下子惭愧起来,拐进一条岔道,而这条笔直的路也展现着同样的景色。
“怎么样?”
阿惠一边对镜卸妆,一边说。
“没有啊。”高桥好不容易才入睡,又被回家的阿惠弄醒了,他一边抬臂遮挡晃眼的光线,一边答道,“影子都没有。”
“不是那个,我说的是面试。”
“可能更糟吧。”
“是吗。”正在不遗余力仔细卸净细微处的残妆的阿惠表情怪异,她从镜子另一头说道。
“对了。原本明天休息,改成上夜班了。今天那家伙来了。他说明天也来,我只好上班了。”
“‘那家伙’是谁?”
眼睛习惯了光线,高桥散落的意识渐渐收拢起来了,他稍微欠起身,背靠着床背。
“乌迷呀。”
阿惠向高桥转过卸好了妆的脸,有点不耐烦地说。
“那家伙烦得很。有段时间没来了,最近情况又好了吧,天天跑来。就一个上班族,好像很有钱。他老约我,我就讨厌他,不理他。妈妈桑也说别理他。真是个烦人的家伙。唉,明天不想去。那我去洗个澡啦。”
阿惠卸了妆,说了想说的话,爽快了,她面露笑容走出寝室。也许是阿惠的衣服、头发熏的吧,房间里有了居酒屋的烟酒混合味儿。高桥被那味儿刺激,从阿惠放在小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因空气不流动,嘴里吐出的烟没飘散,似乎在脑袋上方变成漫画对白框。在这个对白框里头,高桥想起了叫“乌迷”的男子。这名字或来源于“海”,或来源于该男子流脓[4],他自称“我脑瓜子里积了脓”,整天流着黄鼻涕,喜欢亮给女孩子看,恶心人家,于是被店里的人喊作“脓包”。“乌迷”是阿惠店里的熟客,好像是出名没品的人。他对每个女孩子都动手动脚,实在烦人,都有几个女孩子因为他而辞职不干了。而他现在盯上了阿惠。房间一角的空气清新机感知到烟雾,突然启动起来,对白框似的烟渐渐消失了。高桥把抽了半截的香烟在烟灰缸摁灭了,听着空气清新机的声音睡着了。
阿惠摇醒了高桥。已经过下午一点了,但连日深夜在工厂兼职打工,生活完全日夜颠倒,加上今天也是夜班通宵,睡着是在三个小时之前。高桥还想再睡一下,但难得跟阿惠休息日对上,于是就起床了。因为阿惠说想去看电影,高桥嘴里嚼着面包,上网查电影院的排片。得悉在美国获奖的大热影片放映时间正合适,二人便决定去看它。做出门的准备,是阿惠回寝室,高桥去浴室,洗个淋浴好清醒一下。高桥好困,连站着都累,便坐在凳子上淋热水。膝盖的伤口被白白的、软塌塌不像话的皮肤覆盖着。一触碰,白色的膜破了,露出下面黄黄的脓块。看了一下,感觉很不好,他就用热水冲掉它,洗把脸出了浴室。他在对镜打扮的阿惠旁更了衣,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过了一会儿,随着一声“我好啦”,阿惠身穿有帽的上衣配牛仔裤来到客厅。高桥觉得她样子可爱,就说了“好可爱”。阿惠对此只是冷淡地“嗯嗯”而已。去电影院的同时也找猫,二人步行出门了。路上看见几只猫,但都跟那只猫不一样。
工作日的中午,电影院很空,但这部片子大热,还是坐了一半人。高桥和阿惠快开映才进场,领位员说中心区后面看起来舒服,但二人都不喜欢狭小拘束,在边上的空位子就座。场内随即暗下来,一直吵吵嚷嚷的声音安静了。高桥一看昏暗中的银幕,可能是睡眠不足吧,一下子发困起来,他一口气喝干买来的咖啡,但到阿惠“喂喂”地摇醒他时,银幕上播放着演职员表,好几名观众已经迈向出口。
“怎样了?”
因为用了一个怪姿势睡,高桥肩颈酸疼,他一边扭动脖子,一边问阿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