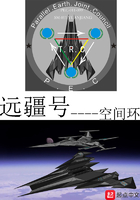时间进入年尾,隆冬下的北风愈显强势,通常这个时节,河朔地区都十分干燥,处在河北腹地的漳河一带自然也不例外,自十月以来,这里已经有四十多天未见雨雪,连空气都似乎凝固了。
相州境内的漳河北岸,平坦开阔。马燧等人在临洺休整月余后,于前不久率领大军赶到此地安营扎寨,此时田悦早已纠集起残军三万余人在洹水筑垒坚守,并以前来助战的淄青军与成德军为侧翼分别驻扎于洹水城的东西两面,与之遥相呼应。
马燧见贼兵势大,乃奏请天子增派援军,德宗遂命临近的河阳节度使李芃率兵前去助阵,李芃全速行军,只两日便赶到漳河,四路大军近十万人沿漳河联营扎寨,场面蔚为壮观。
马燧等人先为李芃接风洗尘,之后便升帐聚将,共商进军事宜,众将到齐后,熟知河北地理的李抱真先言道:“我军驻于漳河北岸,而田悦驻于东南五十里外的洹水县城,我军若要攻破洹水,必先渡过漳河,但漳河东西绵延数百里,水深不下一丈,几十里内只有一长桥可通过,然田悦已派大将王光进在此镇守,大军若要安然渡河怕是不易啊。”
李抱真声音一落,帐内响起议论声,河阳军一将争先道:“一个王光进有何惧哉?末将愿请命夺下长桥。”
“不可,”李抱真摇头道,“长桥宽不过七尺,大军难以施展,况且王光进早已修筑好工事,若是强攻只会徒增伤亡。”
众人纷纷点头,片刻后又一将道:“既然长桥过不得,那何不乘船渡河?”
李抱真听了直摇头,道:“我军有十万人,若乘船渡河,至少也须几百只船,可一时间到何处去找如此多船只?”
众人纷纷说是,此法遂被摒弃,片刻后神策军一将道:“末将倒是有个法子,只是不知可不可行。”
马燧目光朝向那将,见是都虞候李演,遂道:“李虞候有何策只管说来。”
李演道:“此正值腊月,天寒地冻,估计再过些日子,漳河便会结冰,到时大军可否踏冰过河?”
此话一出,众将议论纷纷不一,有人说可行,有人说不可行,这时李晟道:“你所言倒是一策,只是漳河何时结冰谁也无法预料,总不能它一日不结冰,我等便等一日?”
“李都候所言极是,”听了李晟之言,马燧点头道,“兵贵神速,我军不宜在此迁延太久,必须尽快渡河。”
此法遂被否决,之后诸将又提出不少建议,但都被四位主帅一一否定,马燧只得下令暂不渡河,待有了良策后再做决断。
寒风凛冽,草木皆枯,但漳河却是川流不息,丝毫没有要结冰的意思。李愬牵着战马走在河岸边,时不时俯身捡起地上的碎石子,朝水里掷去。与他并行的薛镇有些不奇怪,忍不住问道:“不是说来寻渡河之策么,你朝水中掷石子做什么?”
李愬拍了拍手上的灰土,淡淡地道:“没什么,只是试试河水深浅。”
薛镇歪着头,朝河中央看了一眼,回过头来道:“那你试得如何?可有发现?”
李愬轻叹口气,道:“这条河任何一段都深过七尺,人若不会水是过不去的,就算是会水这么冷的天也游不过去。”
“嚯,弄了半天就得到这个结果?”薛镇长叹一声,从马背上取下了画戟,道,“照我说还不如直接攻下长桥,若与我三千精锐,我定能冲杀过去。”
李愬禁不住嘘了一声,哂笑道:“若是此法可行,何须等到现在?长桥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欲强攻过去难比登天。”
“过河不行,夺桥也不行,难道十万大军就被这小小一条漳河给难住了?”薛镇一脸的郁闷,随手将画戟伸向了水中,信口道,“若是能把河水阻断就好了。”
李愬忍不住一笑,突然间他灵光一闪,似是想到了什么,一把从薛镇手里夺过画戟,同样以戟尖置入水中,眼睛直直地盯着河水。
薛镇感到莫名其妙,看着他道:“你……你这是怎么了?”
李愬愣了半晌,突然收回画戟,一脸欣喜地道:“也许真能将河水阻断,表哥,我已经想到了过河之策,咱们现在就回营。”
“啊?你想到了?”薛镇正迷茫之中,却见李愬已经跃上马背,他遂收起画戟,翻身上马,随李愬向营寨方向奔去。
李愬回到军营,立刻去拜见李晟,却得知李晟和众将皆在河东军大帐议事,于是他又动身去拜见马燧。听闻李愬有过河之策,李晟先是吃了一惊,未等他反应过来,马燧吩咐道:“请其进来。”
李愬同薛镇入了大帐,对几位主帅和众将一一行礼,礼毕后马燧问道:“听闻贤侄有渡河之法,不知是何良策?”
李愬拱着手,朗声道:“末将之策是阻断河流,涉水渡河。”此言一出,帐内顿时哗然,众人皆面露诧色,薛镇更是“啊”的叫出了声。
马燧转眼看了看李晟,回过头对李愬道:“你且细说之。”
李愬不慌不忙,道:“我军营中有数百辆战车,今可将战车以铁索相连,横断河水,再以装满沙土的麻袋置于其上将水流堵塞。”
众人听到此处已是目瞪口呆,李愬又接着说道:“末将方探查过河道,见其中一段呈葫芦口状,下流道窄正适合筑坝,上流道宽正可储水。如此一来,下流河水很快就会变浅,到时大军便可涉水过河。”
众将听罢皆感惊异,议论之声骤起,马燧略加思索,问左右的李晟、李抱真和李芃道:“诸公看此法如何?”
李晟心中已然赞同,却不便明言,这时李芃开口道:“我看此法可行,不妨一试。”紧接着李抱真也点头道:“不错,试试无妨。”
马燧见二人无异议,遂起身道:“好,那就依李愬之言,以战车和沙袋阻断河水。事不宜迟,诸公立即行动。”众将应诺,遂依策行事。
第二天,漳河上出现一道长坝,将流水拦腰阻断,那是用数百辆战车和无数填满沙土的麻袋相连而成。过了一夜之后,下流的水位果然下降不少,几名水性好的士兵下水试探,最深也不过腰间,人马皆可通行,于是马燧立刻下令全军分批过河。
十几万人陆陆续续涉水过河,前后只用了两个时辰。渡过漳河之后官军一路向东南挺进,将洹水以西的叛军尽数歼灭,兵锋势不可挡。田悦据城以守不敢出战,众将对应敌之策争论不休,唯有许士则一言不发,暗自思索,田悦便向其询问计策。
许士则道:“主公无需忧心,依属下看官军渡过漳河于我军未必就是坏事。”
田悦与众将不解,遂问其缘由,许士则接着道:“官军人马虽然过了河,可是粮草却不能渡,只靠马匹驮运来的粮草,难以久持。所以属下以为只要坚守不出,官军为求速战必然强攻,到时只需令城外的淄青军与成德军自官军背后出击,必能大获全胜。”
田悦闻言恍然大悟,喜道:“士则果然足智多谋,吾有士则何愁不能击退马燧?传令下去,各军坚守城垒,不许出战。”
“主公且慢,”田悦话音刚落,王侑进言道:“坚守不出虽是良策,但东边寨成德军只有三千人,马燧若攻恐怕难以久守,不如将其调入城中,如此一来,我们便与淄青军形成了辅车之势,马燧要想破城势必难于登天。”
田悦深以为然,便依王侑之言将兵少的成德军调入城中,与魏博军合为一处,两军遂与城外的淄青军形成了辅车之势。
官军渡河数日,军中粮草渐渐不支,众将正一筹莫展时,马燧突然下令各军只带十日口粮进驻到洹水西岸的仓口驻扎,与魏博军隔河对峙。
众将闻令多有不解,李抱真、李芃问马燧道:“我军粮草不足,贸然深入敌区是否太过冒险?”马燧摇了摇头,对二人道:“正因粮少,才更应速战速决,田悦闭关不战,便是欲使我军粮草耗尽。只有进军到洹水,对其形成威胁,田悦才可能出战,届时我军再全力出击,定能破之。”
李抱真、李芃闻言不再异议,马燧遂率军进驻洹水,各军扎好营寨,马燧、李晟等亲率百余骑到河岸查看敌情。洹水河道比漳河窄了许多,水流也不及漳河湍急,而洹水县城就在洹水以东不足三里处。马燧前后一番查看后,心中有了计较,遂传令在正对城门的位置造上三座浮桥,以备渡河攻城。
次日,李自良、李奉国奉命率五千军渡河至城下挑战,田悦却紧闭城门不出,李自良令麾下诸将轮流上前叫阵,偏将阿跌光进先往城上骂道:“田悦,尔世受皇恩,却犯上作乱,失人臣之道,还知羞耻二字乎,如今天兵到来,尔还不开城投降。”
城上并无动静,阿跌光颜也驱马上前,跟着道:“贼悦,闭门怯战算什么好汉,难道是惧了我等不成,真应该叫尔鼠辈田悦。”
诸将闻言纷纷大笑,齐声高叫:“鼠辈田悦……”
田悦在城中,听到城外震耳的辱骂声,不禁大怒,竟要出城应战,众将急忙拦住,许士则劝道:“尚书稍安勿躁,马燧遣人在城下叫骂就是为了激怒你,你若出城正中马燧之计矣。”王侑、康愔等人也纷纷相劝,田悦这才止住怒火,避声到了后堂。
天色渐晚,李自良见敌军始终不出,便引军退回了营寨,众将见其无功而返不免有些失望,马燧却不以为意,次日又派遣昭义军前往城下继续叫阵。
昭义军五千人,由行军司马卢玄卿率领,过浮桥往洹水城下挑战,诸将使尽浑身解数,各种言语激将,洹水城却始终大门紧闭,卢玄卿只得收兵回营。
又次日,马燧再遣河阳军城下挑战,但结果依然如此。
第四日,神策军前来挑战,邢君牙率军抵达城下,诸将照例上前叫阵,半晌下来,却不见城中有丝毫动静,薛镇渐失耐心,愤愤道:“这个田悦,起兵反叛时气焰何等嚣张,如今却像个鼠辈,我嗓子都快骂哑了,他怎么就是不出来哩?”
邢君牙不慌不忙,正色道:“田悦知我军粮草不足,不能久战,故坚守不出,以待我军粮尽之后,乘虚而攻。”
“既如此,那我等为何还要来挑战?”薛镇嚷道,“倒不如强攻来得省事。”
“不可莽撞,”邢君牙白了他一眼,伸手指着前方讲道,“洹水城墙高逾三丈,易守难攻,况且西边还有淄青军与之呼应,一旦强攻必会腹背受敌。”
薛镇一脸怏怏,不服气地道:“可这样每日挑战不是徒劳无功么?”
邢君牙暗自思索,李愬突然笑了笑,道:“依我看并非徒劳,马公这么做一定有其用意,也许他已经有了破敌之策。”说完他又对邢君牙道:“刑将军,今日也差不多了,收兵回营罢。”
邢君牙点点头,遂勒令撤军,薛镇仰面叹息,却也只得随军回营。
一连四日,田悦都闭门不战,众将不免心中着急,昭义军几员将领合计之后,遂一同前去拜见李抱真,劝其退兵。诸将言道:“我军只带十日口粮,如今已过去四日,诸军却还是寸功未建,照此下去,我军危矣,不如暂时退兵,徐图再进。”
李抱真闻言面露难色,叹道:“尔等所说吾何尝不知,只是马仆射军令如此,又能奈何?”
“尚书此言差矣,”李抱真声音刚落,大将王云兆道,“尚书与马仆射同为节度使,并无隶属关系,只因马仆射年长望高,才由其统率诸军,今其率军冒进,实为兵家大忌,尚书若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李抱真闻言一怔,心中暗自计较,片刻后谓众将道:“诸公之言确实在理,那就诸公请随我去见马仆射,共请其退兵。”众将欣喜,遂同李抱真往马燧大帐而去。
诸人见到马燧,当即道明来意,马燧听完李抱真之言,淡然笑道:“太玄不必担心,吾自有分寸。”说完又对众将道:“请诸公各自回营,听候号令。”
诸将闻言心中愤愤,皆不肯退去,王云兆道:“马公不会是有意推托罢?若你实在没有破敌之策,不如早早撤军为好。”
马燧脸色登时一变,眼中放出一道寒光,王云兆不觉浑身一颤,闭口不敢再言。李抱真见状淡淡地道:“既然马仆射如此说,那我等就暂且回营罢。”说完遂拱手向马燧告辞,转身出了大帐,马燧目视众将离去,心中不免有怨。
洹水城中,魏博兵马使康愔见官军日日挑战,突然心生一计,向田悦献言道:“官军明日必复来挑战,我军可于洹水一岸设下伏兵,待官军至城下,伏兵齐出前后夹击,定能大获全胜。”田悦闻言大喜,遂依计吩咐下去。
次日,天还未亮,城里一片漆黑,偶尔听得几声鸡鸣犬吠,而城外的官军营寨却亮起无数火光,并传出阵阵鼓角声,这声音由西向东,渐渐远去。
田悦隐隐听到鼓鸣,只当是官军又来攻城,并未放在心上,待到天明时,突然有士兵来报说官军起寨拔营沿着洹水向东而去。田悦闻听惊诧不已,正琢磨马燧是何用意,许士则突然惊道:“不好,官军东进乃欲突袭魏州,绝我军退路矣!”
“什么?”田悦闻言大惊失色。康愔上前对其道:“魏州乃是根基所在,如今主力大军皆在洹水,魏州几千军恐难以久守。”
田悦心中大急,忙问道:“那依尔等之见,该当如何?”
康愔拱手道:“请尚书立刻下令追击,利用风势以火攻奇袭官军,必能取胜。”
田悦闻言深以为然,又问许士则、王侑等人是何意见,二人想了想,皆点头赞同。田悦遂亲率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四万余人倾巢而出,追官军而去。好在洹水上的几座浮桥并未被官军拆除,田悦率兵由此渡过洹水沿着河道向东追去。
众军追击了十余里,突见前方棘草丛生,旌旗闪动,田悦料是官军人马,立即下令乘风点火,鼓噪进军。此时正值正月,天干物燥,枯草遇火便燃,顺着西北风疯狂地朝东面扑去。不远处,官军已等候多时,马燧见西边火起,镇定自若,传令道:“动手。”话音一落,数百将士列队向西,手持朴刀除草斩棘,很快便造出一片开阔地带。
火势向东蔓延而来,所经之地尽成焦土,但大火到了距官军百步之处的开阔地突然衰竭,很快便失去了火光,此时官军早已严阵以待,河阳军、神策军在左,昭义军在右,河东军居中,马燧一声令下,诸将遂带队冲锋,直奔敌军杀去。
田悦见官军扑来猛地大惊,立刻号令全军列阵应战,双方数万人遂绞杀在一处,邢君牙、李自良、阿跌兄弟、李愬、薛镇等将皆冲锋在前。杀至正午双方僵持未下,昭义军与河阳军渐有退却之意,马燧见势谓左右道:“众将士浴血奋战,我等岂能坐视,诸君愿随我出战否?”众人皆道:“愿随。”马燧遂亲自持刀杀向敌军阵中,几步间连斩数将,勇不可当,李晟、李抱真、李芃见马燧身先士卒,亦持刃赴战,官军士气顿时高涨,无不奋力死战,很快便占据上风,田悦军难以抵挡,向西败逃而去。
田悦退至洹水,正欲渡河,却见水面上的三座浮桥已被焚毁,原来马燧事先留守百余人伏于浮桥附近,只等田悦过桥之后,便焚桥断其退路。田悦见不能过河,顿时大惊,方知中了马燧之计,嘴上骂骂不已。很快李自良、邢君牙等将率部追来,魏博军失了退路军心大乱,纷纷跳河逃窜,被射杀者、溺死者不计其数。
叛军兵败如山倒,田悦正惊措间,突听四周响起“活捉田悦”的阵阵高喊声,田悦心惊胆战,欲跳河北遁入城,许士则急忙拦下,劝道:“主公,经此一战我军伤亡殆尽,现在北去只有死路一条,还是返回魏州重整旗鼓罢。”田悦踌躇片刻,随后听从其言,令大将孙晋卿、安墨啜等人断后,自率残军千余人向东冲杀出去。
诸将见田悦败逃,争先追击,李愬反身向东,追不几步正遇安墨啜,挺枪便战,安墨啜识得李愬,未经交手心中已怯,刀法随之紊乱,只数合即被刺于马下。李愬继续向前追击,不多远又遇孙晋卿,正欲迎上,却见阿跌光颜已与之战到一处,此时薛镇也自西边赶来,一见阿跌便道:“我去助他。”李愬拦下他道:“他一人足矣!”声音刚落,只见阿跌光颜手起刀落,孙晋卿随之翻身落马。三人会于一处正要再追,突听身后传来鸣金声,李愬、阿跌遂收兵回返,薛镇却仍欲前追,李愬勒马冲其喊道:“服从军令。”薛镇深叹口气,随二人向西而去。
天色已晚,战斗渐渐停止,马燧整军回营,令人收拾战场,此战官军斩杀、俘虏叛军三万余人,斩敌将数十员,只逃了田悦、康愔等人。李抱真、李芃料其逃亡魏州欲连夜追击,马燧却道:“今日历此大战,各军将士皆已疲惫不堪,待休整些时日后,再进军魏州不迟。”说完他又对李抱真道:“此外,魏州城高池深,非一日可下,烦请贤弟自临洺运攻城器械来。”
李抱真闻言心有不悦,沉吟了片刻后,点头“嗯”了一声,随后便顿兵不动,派人往临洺调来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