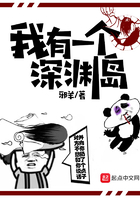慎心斋内,凝重的气氛比闷热的天气更让人烦躁不安,雁儿来报信,霂颻只是听了大概。并没有细问,就打发雁儿先回去了。
“太妃娘娘,你真的不过去瞧瞧?”瑞喜焦急的询问,他看得出霂颻也在担心。
“你怎么又忘了,刚才我讲的计划很清楚,如果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太过关心,以后她就会被怀疑。”霂颻深重的叹了口气,阖上双眸,有些时候狠心是必要的。“何况这种事情她日后还会遇上很多,如果不知道怎样面对、如何处理,那早晚都是一死。与其是那样,晚死不如早死,还能少受些罪。”
福海没有吭声,之前他害怕霂颻会把玹玗当棋子使用,可今天听过她的计划,才知道她已经为了玹玗,把自己摆上了棋盘。事情既然发展到这一步,他只能选择听从,霂颻怎么说,他便怎么做,只求精准无误的将计划实行下去。
“你们若是担心,等入夜后就过去看看,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睡了你们才偷摸出去的。”望向院墙外太医院的方向,霂颻心情凝重地说道:“以玹玗那孩子的心思,这次未必真的那么严重,有可能是她的应对之法。”
瑞喜、福海相视一望,都无奈的挤出了一丝笑意,只能等到入夜后再去探望玹玗。
而在另一边,毓媞得知裕妃下狠手之后,一直不动声色,只是又一次让人把这事儿传开,务必要阖宫上下都知道,故事怎么编她不管,但要围绕着裕妃杀人泄愤这个点去传。
耿氏这几年渐渐显露了野心,以为自己坐上了妃位,儿子又册封了亲王,就机会觊觎更大的福气,却又不知道掂量自己的份量。
戏罢众人散去后,毓媞便命人将裕妃请到景仁宫小坐。
“裕妃妹妹,有些事情既然过了就应该忘掉,总揪着不放还挑事点火,也不怕烧着自己。”毓媞也不点明事情,只是隐隐的出言警告。
“熹妃姐姐说什么,妹妹我听不懂。”裕妃心中七上八下紧张的打鼓,她手下的小太监一直没回来交差,涴秀去而复返后又总横眉竖目的瞪着她,只怕是事情失败,可在毓媞面前还得强撑着。
“妹妹要知道,如今后宫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蕊珠的事情还没让你看出宫中的情势吗?”虽然出言相劝,毓媞却是乐意见到裕妃闹事,虽然弘昼继承大统的机会不高,但总是个威胁。“你心疼蕊珠,等过段时间想个法子招她回来就行了,别把事情闹得沸反盈天,收不了场还反把自己搭进去。”
“蕊珠是我的表侄女,招她入宫本来也不是当奴才的,却因为一个辛者库罪籍被罚去先帝妃陵,我只是想替她出口气。”裕妃行事之前早让人打听过玹玗的身世,见她是在慎心斋当差,如此命贱应该是没人怜惜。“我知道,涴秀格格和那个贱婢亲近,姐姐也不管一管,小心沾染了一身晦气。”
毓媞冷声一笑,还真是个愚不可教的蠢女人,难怪不得雍正帝宠爱,如今上了年纪,岁数是在增加容颜渐残,可内涵依旧浅薄,宫里熬了这么多年,也没半点长进。
“娘娘宫里又出大事了。”银杏刚回景仁宫就听说裕妃也在,便故意到毓媞跟前说道:“奴才们都在传,今天有个小太监在西华潭边行凶,正好被一个侍卫撞见,据说事情已经传到皇上跟前了。”
“砰”地一声茶杯落,裕妃心中一颤,以为只是件小事,怎么会闹到雍正帝跟前,忙向毓媞问道:“今天西华潭边侍卫不是都撤了吗?”
“是撤去了一部分,调派到西安门至团城一带驻守,但宫闱禁地怎么把侍卫全撤掉。”只因为今天允许宫婢去西华潭边祭祀花神,才撤去西苑门一带的侍卫,让附近内务府会计司的太监们留心盯着点。“出西华门左边是升平署、灰池、油漆作,右边是会计司,杂人杂事最多的地方,岂能不放侍卫看守?”
裕妃一脸焦虑地望着银杏,问道:“可知道皇上怎么看待此事?”
“皇上国事繁忙,哪里会管这些事。”银杏瞄了毓媞一眼后,才继续说道:“不过皇上把这件事交给齐妃娘娘处理,要她一定严惩。”
“怎么又是她?”裕妃挑拨的对毓媞说道:“这后宫执掌凤印的是姐姐你啊,可皇上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事情交给她处理,这不是明摆着夺姐姐的权吗?”
“我也只是代执凤印,皇上觉得齐妃姐姐比我更会管理后宫,且她位分排名确实在我之上,自然就把权利都交给她了。”毓媞露出一个浅笑,满不在乎的说道:“所以我才会劝你消停些,齐妃可是个黑脸包公,弘时死后她也没少受委屈,眼下得了权势,还不拼命的发泄心中不快,储秀宫以前是她的,如今你住着,她不挑你的错,还能挑谁的?”
如果按照雍正帝当年分派宫院的想法,永寿宫空置,翊坤宫锁闭,居住在储秀宫的裕妃似乎就是地位最高者,可实际上却比毓媞都还不如。耿氏年轻那会儿徒有容貌并无学识,在藩邸时只是乌拉那拉氏房中的格格,说白了只算得上是个通房丫头。刚入宫时,还能凭借着容貌混到个嫔位,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唯一邀宠的资本渐渐逝去,儿子弘昼又不长进,她在雍正帝心里早已没了地位。
“当年可是她自请迁宫的。”裕妃挑拨不成,反被毓媞将了一军,又想起当年弘时刚死,她却故意在咸福宫摆戏,人前人后也没少挤兑曼君,心里就更觉寒颤。
“齐妃那边又是怎么说的?”裕妃的抱怨,毓媞全当没听到。
“说是要追根究底的详查此事。”银杏故意把语调放沉了些,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裕妃一眼,才说道:“那小太监是要杀宜太妃身边的宫婢,就是在内务府受过裕妃娘娘处罚的玹玗,奴才斗胆揣度,齐妃娘娘如此大动肝火许是另有用意。”
这话如针般插进了裕妃的心里,便急急告辞先回储秀宫,她必须想法子赶在曼君前头把那个小太监料理掉。
“玹玗怎么样了?”殿内已无旁人,毓媞才向银杏问道:“涴秀说她呛水严重,你回来之前她可有醒过?”
“没有呢。”想着玹玗的情况,银杏的心情更沉重了几分,“发着烧一直昏睡着,杨太医说是引发肺染,恐有性命之忧。”
毓媞皱起眉头,呛水不是小事,当年仁寿太后生养的六皇子胤祚就是死于落水引发的肺染,不知道玹玗那孩子有没有福气逃过此劫。
“今夜景仁宫的门就别落锁了。”毓媞叹了口气,才柔声说道:“你把这话带给涴秀,免得她又生出爬墙头的把戏。”
银杏浅笑着点了点头,现在涴秀是被困在景仁宫,可一旦入夜毓媞就寝了,那是一定会想尽法子溜出去的。
入夜后,滚滚乌云低压,一道闪电撕裂了天幕,暴雨倾盆于天地间。
御药房和太医院之间的排屋。
雨水砸落在石阶上,泛起朵朵碎花,闷热的暑气因雨势而减退。
玹玗虽非完全昏厥不知事,但呛水引起发烧却不是假的,耳际的轰隆雷声让她从昏沉中醒来,只觉得全身发软,四肢酸痛无力。
瑞喜和福海从天黑后就一直守在这,见她睁开眼了,那提着的心才算是放下一半。
“你可吓死我们了。”三人关系好,且他们又是太监,平时也没什么忌讳。这会儿瑞喜跳到床上,缓缓扶着她坐起身,用自己的身体做她的靠垫。“太妃娘娘要避嫌,才不敢来看你,我们两也是入夜后才偷偷过来的。”
“你先喝点温热的粥,然后在吃药。”福海眼中泛着泪光,端着清粥亲自喂她。
玹玗刚吃了一小口,就觉得胸口发闷,肺部也有疼痛传来,胃里泛起的痉挛引来干呕。
“那还是先喝点水。”看她如此难受,瑞喜忙指着一旁帮的蜂蜜水说道:“那是杨太医吩咐下的,要是你没有胃口,就用野蜂蜜兑点水喝。”
“嗯,那粥一会儿再吃。”玹玗勉强挤出一丝浅笑,反而安慰他们道:“我没什么大碍,这是故意做出来的苦肉计,博取银杏姑姑的同情。”
“别说话了,自己好好歇着。”福海又端了药来,眉头紧皱地说道:“我刚才尝了一口,这药可苦了,你又是喝了****再喝苦药,只能忍着点。”
玹玗细声笑道:“我不怕苦,没事。”
“宫里的日子长着呢,你以后行动可得注意点,今天我们哥俩打听过,那个裕妃最是小心眼,一定是她挟怨报复,才命人下毒手的。”听着玹玗说全身酸疼,福海便坐到床边帮她捏腿。“我们过来的时候遇到御药房的李公公,他说银杏姑姑一定会帮你出气,会想法子给裕妃颜色看。”
“我恍惚中也有听到他们的对话。”玹玗深知后宫中多的是奴大欺主,银杏要对付裕妃也不是难事。“银杏姑姑跟在熹妃身边多年,她自有法子警醒裕妃,以后裕妃应该也就不会对我下手了。”
深知她是在宽慰他们,瑞喜也不多言,只想着她发烧必定头疼,就轻轻的为她揉着太阳穴,又细声说道:“你要是累就闭上眼睛养着,我俩伺候着你。”
“这一病才知道,有哥哥宠着真好,以后得多病些,才有这样的福气。”玹玗知道瑞喜的身世后,偶尔也会喊他一声哥哥,也就是因为他们俩攀上了亲,有时说话更近些,才会张罗着给福海也认个妹妹,这样大家都能有亲人相伴了。
“乌鸦嘴!”瑞喜忙啐道:“坏的不灵好的灵,就是不生病我们也会宠着你,这种话可不许再说了。”
窗外雨声嘈杂,雷声不断,玹玗虽觉得身子乏,却并不困倦,于是和他们低声说笑。
此时,落雨中夹杂着急促的脚步声,只见涴秀带着雁儿推门进来,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一半。
“这么大的雨,你们跑来干嘛?”福海既然认了雁儿做妹妹,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忧心。“别她还没好,又病倒两个。”
“玹玗妹妹,你可好些了?”涴秀走上前,挨着床边坐下,见玹玗醒了才不似之前那般担心,且她也知道了认亲之事,便取笑地说道:“你们都是有哥哥宠着的,偏我没人疼爱。”
瑞喜和福海只是笑着不答话。
“两位王爷不是专程送了礼物给格格吗?”虽然雁儿看不明白礼物的含义,但是涴秀却喜欢极了,“只是那礼物有点莫名其妙。”
“是什么东西?”雁儿那一脸的纠结,引来了玹玗的好奇心,弘历、弘昼都是心思细巧的人,千里迢迢送来的礼物,一定必有深意。
“一大箱子泥土,还长着草呢。”雁儿答了,又说道:“肯定是和亲王戏弄咱们格格呢。”
“不是!”瑞喜、福海、玹玗异口同声的否定,众人都不由得相视一笑,才缓缓为雁儿解答了疑惑。
春树绕宫墙,宫莺啭曙光。忽惊啼暂断,移处弄还长。
隐叶栖承露,攀花出未央。游人未应返,为此始思乡。
深宫之内,一箱故土,遥寄多少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