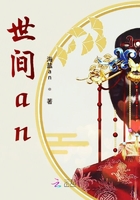虚云被杨羽气疯了上去就给杨羽一个耳帖子,杨羽知道自己理亏拔腿就跑。
杨羽跑进屋里,等着虚云招呼,虚云骂道:“你还知道要脸啊?”杨羽抱着头躬着腰准备挨打。一顿拳脚后,虚云说:“混蛋,你怎么想的,能干出这么操蛋的事?”
杨羽抱着头回答:“你不是想让周亚宁帮你吗?我本来想说服他跟咱们走,人家想在药铺当账房过安稳小日子。”
“那你就陷害人家爹,逼买人家房,你是人吗?”虚云继续骂着。
杨羽辩解道:“不这样周亚宁能跟咱们走吗,再说他家的房是狗子买去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虚云一听是狗子买的周亚宁家的房更是气,上去又是一顿暴打:“小杨羽我看这回看你如何收场。”
虚云问杨羽,狗子花多少钱买的周宅?杨羽说:“三千两银子。”虚云骂道:“周家宅院五世经营的宅子,最少也值三万两,三千两,这是趁火打劫。”
杨羽说:“成大事不拘小节。”虚云气急败坏的骂道:“你放屁!”
杨羽说:“我只是想让周亚宁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这样我要求他做什么,他都会答应的。”
虚云骂道:“你可真无耻!”
周父在牢房里被打的皮开肉绽,趴在稻草呻吟:“我真没有通匪,我冤枉啊…”
周亚宁和母亲暂住在他舅舅家,如今,周母心中熬糟,一点办法都没有,整日里以泪洗面,几日里面黄肌瘦。
舅母总是冷言热讽得说:“平时人家日子过的好,不经常走动,出事了才知道亲疏里外。”舅听到后总是骂她:“有事没事搁了嗓子,败家娘们。”舅母阴阳怪气的说:“人家天天拜佛的人,可如今又如何?”
周亚宁听出舅母在说母亲,可是,人在屋檐下,能怎样哪?舅舅说:“周亚宁明天你再去求求东家,你们家三辈子给他们家当账房,总归有点情意啊!”
周亚宁说:“早就求过了,东家说如果知道这事,我父亲也参与其中,是不会告官的,如今证据确凿,多人亲眼看到父亲和土匪沟通,土匪没抓到,药物银两也没追回,现在就是想撤讼都不行了。”
周亚宁妈妈喃喃自语的说:“平日里我吃斋念佛,他父亲更是与人为善,不曾得罪人,怎会遭如此祸事”。
虚云打骂过杨羽后说:“你赶紧去置办些好酒菜。”虚云转头去找狗子。
看管周父的两个狱卒边喝酒边骂骂咧咧的说:“这年月,人都不识相,都到这份上了还当守财奴。”另一个狱卒说哥:“咱只能认倒霉,人家是打算盘子的,东家都养不熟,咱算啥?”年长的说:“算啥?等老子给他上上手段,他自然知道咱算个啥。”
周父听到要给他上手段,央求的说:“我真是冤枉的,请二位大人高抬贵手。”
年纪小的狱卒哂笑着说:“这红嘴白牙,说冤枉就冤枉,呵呵,王法是你家的啊!想在我们手里舒服,得有舒服的理由。”
年长的狱卒使了个眼色说咱得让他明白明白规矩。年轻的狱卒坏笑着出去了,一会带着一个囚犯进来,年长的狱卒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新带来的囚犯回答:“没了,全死光了。”年长的说:“你要是想亲人了我们倒是能进点人事。”新囚犯害怕的喊:“你们要干什么?”年长的说的句:“更衣。”年轻的笑着说:“没事,给你解带。”衣带解开后,年轻狱卒脸色一变,手上用力,只听啊…!的一声惨厉的叫声,劳服带着血痂被活生生的扯了下来,犯人伤口的血咕咕的流出来。犯人骂道:“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年长的抓着犯人的头一顿撞墙,犯人被锁着手脚知道反抗无用不在出声。
把他送回去后,年长的狱卒说:“倒点酒给我净净手。”
周父吓得面如土色,年长的狱卒安慰着周父说:“别怕,他不懂规矩,你不会也不懂吧!”年轻的狱卒接着说:“这叫“生剥”,不懂规矩的伤口化脓后可不好办了,恐怕真金白银也只能当纸钱用了。”年长的狱卒端着酒碗说:“这酒可是好东西,既能消毒,又能剥痂不流血。”
狗子骂道:“缺德矬子你不怕生孩子没**啊!”年长的狱卒就是狗子嘴里的矬子。矬子满脸堆笑:“这不是马哥吗?早上喜鹊就在房上叫,这不晚上就见到贵人了!”年轻的赶紧让座倒酒。狗子请虚云兄弟坐,虚云拱了一下手没说话每动地方,斜眼瞪了一下杨羽。杨羽见周父的惨样心中翻滚。
矬子问狗子:“这二位是?”狗子说:“你没资格知道。”矬子强忍着尴尬笑着说:“刘哥有什么指教,小弟能做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狗子拿出五十两银子说:“买酒喝。”矬子推辞,狗子一瞪眼说:“嫌少?”年轻的狱卒赶紧收下:“刘哥太抬举我们哥俩了。”狗子说:“知道抬举就好!”杨羽往牢房里走,看清了周父:“周叔叔受苦了。”情绪不稳的周父见到杨羽于是呼救:“救我,救我出去…”接着有说:“你们快走这里是炼狱快走。”杨羽此时,口干舌燥,百爪挠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狗子说:“这盒酒菜是给里面的,那盒是给你们哥俩的。”“好生看管,他少一根毫毛,我扒你们的皮。”狱卒唯唯诺诺的说:“是,是,好好。”狗子说:“有想吃的你们言语,我给你们送。”狱卒:“客气了,您放心,不会差事的。”
虚云们走后,年轻的问年长的:“那两位是什么来头?马哥亲自来交代咱们?”年长的狱卒说:“想好好活着,少知道点事安全。”
杨羽一夜未眠,他该如何应付这陌生的世界哪?狗子在外面这样嚣张,在柴家就像条狗为什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