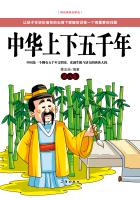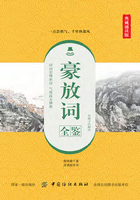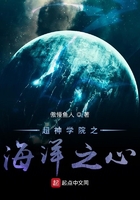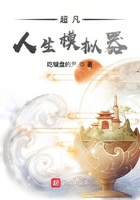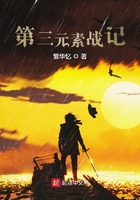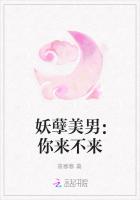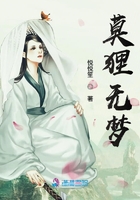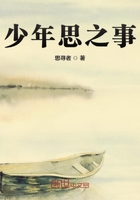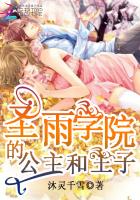刘海琴
甲骨卜辞所见“寻”字资料与典籍所载“释奠”之关系的揭示,是与“大学”在卜辞中的最早发现与研究紧密相连的。
今试借由对“释奠”具体内容之辨析,反观“寻”卜辞,再探两者之关系,以期获得对该类卜辞、该项活动之进一步认识。
一、“释奠”之具体动作及其与甲骨文“寻”之对应
各家注释多将“释奠”“舍奠”“设奠”三者互释,如凡经文中之“舍奠”,郑玄注多云“释奠”,如《周礼·春官·甸祝》“舍奠于祖庙”,郑玄注即谓“舍读为释,释奠者,告将时田,若时征伐”,而孙诒让又证之以上引《礼记·大传》之“设奠”,称“彼即征伐舍奠之事”。无论“释奠”抑“舍奠”“设奠”,其“释”“舍”“设”因音近而通之“义”,只能是“陈置”“设置”。“释”之“陈置”“设置”义隐含于“释奠”中,论者虽常以“陈设酒食”言“释奠”,然并不贸然以“陈设”解“释”,至常用工具书《汉语大词典》虽收录有“释輟”“释奠”“释菜”乃至“释币”等词语,却未将“设置”“陈列”列为“释”之义项,其所列义项中又不见有与此义相等者。而宋元时期学者熊朋来已明言之:“释之为言置也,故《礼记》作'释',《周礼》作'舍'释奠'者,置其所陈设之礼物也;'释菜'者,置其所挚苹繫之菜也。”
至于“奠”,其字像置酒樽于开上,《说文》即以“置祭也”为解。可见,“奠”有“置”义,是将“币帛”“酒爵”“挚”等物品放置在某处的意思。
而“释奠”中“奠”已见于卜辞,可用于祭祀,则“释奠”与“寻”之关系,重在“释”与“寻”之关系。举行“寻”这一活动的地点最受重视,有四个选择:丨、祖丁旦、庭旦、“大学”,“I”不识,暂不论,祖丁之祭坛“祖丁旦”、庭之祭坛“庭旦”均为祭祀场所,则“大学”亦应为可以与这些地点相当的祭祀场所,在该处举行的“寻”应该与在“门”“南门”等处所举行者一致。如此,将“于大学寻”看作是卜辞所见在“学”举行之“寻”,并将之与“释奠”之文献记载相对照,是可行的。
二、俘虏、祭祀及地名类“寻”卜辞与“释奠”文献记载之对读
卜辞记载与文献记载之战争告捷环节实现了相当程度的重合,卜辞之“寻”与典籍之“释奠”应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容,既然“释奠”意为依次陈列、分别设置,“寻”也应有相近的意思。照此思路推测,“寻”相当于“释奠”,则“寻羌”“寻执”“寻某伯”,就应该反映了献俘过程中分门别类陈列俘虏的情况,陈列的目的是为了报告战功,类似于田猎“献获”仪式“表貉”中之“属禽”:《周礼·春官·甸祝》:“师甸致禽于虞中,乃属禽。”更值玩味的是,《逸周书》与《小盂鼎》所载两事其发生地点均在“南门”,而“南门”正是卜辞中“寻”这一活动的主要发生地,“寻羌”“寻执”“寻某伯”均曾在此。
三、以“释囂'反观'寻舟”卜辞
今既辨“寻”与“释奠”相关,比之典籍中“释奠”有关内容,“寻舟”这一动名组合相当于典籍之“释菜”“释币”,或“释輟”“释获”。前者即“设菜”“设币”,“菜”与“币”乃“释”之直接作用对象,后者乃“为輟而设某某”“为计算所获而设某某”,“輟”与“获”乃“释”之目的。相较而言,为舟而陈设某某,比“陈设舟船”更符合他类“寻”卜辞所揭示之陈设祭品义,则“寻舟”与“释輟”更相接近。
四、由“释奠”再读几组疑难卜辞
前述已为“寻”类卜辞之大概,所余者多为辞例过简、省略严重乃至残辞,可不论,此外尚有几例或文辞不通、或义有未明,以致争议反复,试以“陈列”“依次设置”义再读之,冀有所得:
第一,寻占:丙申王寻占光卜曰不吉有祟兹乎来。
因行文与他辞迥异,各家释读不尽相同:《甲骨文合集释文》断为:“丙申,王寻占。光卜曰:不吉,有祟,兹乎来。”
第二:王马寻:甲午卜,王马寻,其御于父甲亚吉。
该辞中“寻”前出现了“王马”,迥异于之前所见人名,“寻”后出现了“4”,论者或言马悍
烈,或言马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乃至死亡,总之均为马的某一种状态,而非之前所见之俘虏、地点、舟船等名称。
第三:往寻:辛未卜,宾贞:王往寻,不……亡灾?
第四,寻丁
一是“寻”出现了一种新的组合方式,迥异于以往;一是对“丁”的判断尚有疏漏,“丁”仍然不
出俘虏名、事物名、地名中的某一类。就结构分析,“,丁乍,子兴寻丁”中“子兴寻丁”应是在“,丁乍”基础上进行的活动,“子兴”为主体,其“寻丁”之前提条件乃“丁乍”,两个“丁”所指应该相同。
五、余论
综上,“释奠”是一种依次陈列祭品的活动,甲骨文“寻”字资料与“释奠”记载具有相当程度之可比性,一定意义上,甲骨文“寻”字资料反映了“释奠”在甲骨文时代的部分内容。囿于客观条件及受笔力所限,尚不能在甲骨文“寻”字与典籍“释奠”一词乃至“释”一字之间画等号,它们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具有爵、三种写法之字所对应者本不为“寻”,亦非“释”,而为另外的字,然其字义内涵及相关卜辞内容与“释奠”记载之关系,大致仍应如前文及上文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