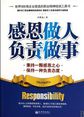主院,谢珞匆匆的脚步一跨入梁氏的房间,面向门外的梁妈叫道:“夫人,二少爷来了。”
闻声,搂在一起掉泪的妯娌二人抬头看向门外,见着真是谢瑾,三婶张氏急忙站起身迎向谢珞。
许是见着主心骨,张氏自觉有了依靠,一腔哀痛顿时抑制不住,‘哇’一声哭的嘶声裂肺:“瑾儿,你三叔他出事了,方才有人回来传讯说他被歹人袭击,深受重伤昏迷不醒,熬不熬的过去全看天意。”
尽管谢珞心中同样悲痛,脸上丝毫不显,语气镇定地问道:“三婶,南江过来的人呢?”
张氏哽咽着:“刚走不久,婶子不识得那人就让他走了。”
“瑾儿,你三婶要去找三叔,娘不让她去,妇道人家夜晚出远门太过危险。”梁氏声音也带着哭腔,听闻噩耗传来,她的心情也很悲痛。
梁氏虽是不喜谢无涯,只是叔嫂间的小纠纷岂会抹灭她的良心,再怎地也是至亲之人。
谢珞的面色平静,遇事不慌,有着不符年纪的沉稳,她若是慌了,两个妇道人家能怎么办?
族中庶支委实是靠不住,他们都是太爷爷的兄弟留下的血脉,血缘远了不说,族中一有糟心事儿,半个人影也见不着,若是有好事儿,前来分好处的族人准能将屋子挤的满满当当。
“嫂嫂,我求求你了,让我去吧。”张氏泣不成声。
梁氏见她又闹,双手迅速扣上张氏的手,伸出脚踢了踢呆楞的谢珞,不满道:“瑾儿,你杵着愣什么?快劝劝你三婶。”
谢珞愣神是在暗想独自偷着去,不去她会寝食难安,南江县不太平,不能带着谢瑾去。
回神,谢珞看着犹在抽泣的张氏,劝慰道:“三婶勿忧,三叔身边有人照顾。夜间出行不太平可千万不能去,今晚您就在这歇息,待明日天不亮我就来找您,陪着您一同去看三叔。”
张氏挣脱不开束缚,悲痛之下,泪水汹涌而出,她心系丈夫,如何能等到明日?
她后悔不该来此,瑞儿让懒婆子他们送来就好了,自己也能偷着去。
谢珞不想多待,她从梁氏房内顺了一样物件儿就走了。
她已决定要去南江县,匆忙的脚步到了外院的勤务苑,此处是谢府下人的居所,匆忙的身影进了院子,片刻后,小秋父子跟着她出了院子。
小秋父子都身怀武艺,只不过小秋的胆子太小,浪费了一身好武艺,对此,武艺高强的谢武常常叹息老子英雄儿怂蛋。
………………
幽静的黑夜里,闯入一阵持续奔走的马蹄声,打破了沉寂已久的夜空,站在南江县城城垛上的守城将领听着由远渐近的声音猜测距离,再揣度马匹的行走速度,两相结合得出大致的结论,随即严肃的开口道:“不足两百步,紧急戒严!”
无怪乎将领紧张,如今南江县正值多事,除却有屯兵在边界的彝南军队,今日城里还发生了刺杀事件。
马蹄声愈来愈响亮,渐渐的出现在守城兵士的视线,这是一辆样式寻常的马车,马车上挂着几个照明的灯笼,灯笼上都写着一个‘谢’字。
身侧副将扭头看向将领:“头儿,这是谢府的马车。”
钦州人都知晓谢氏,不单是因为谢氏是钦州扎根数十代的书香大族,更令钦州人谨记谢氏的缘由是谢相国在位期间替钦州谋了许多福祉,惠及了数十万钦州百姓。
将领一声不吭,正是谢氏的名头让他客客气气的任由马车渐渐靠近城门下,若是旁人的马车,他早已大吼质问,更是不能让马车靠近城门百步以内,否则将被乱箭射杀。
马车停在了距离城门十步远处,马车上下来一位年轻的公子,公子抬头仰视,温和的目光与将领的锋睿的目光相触。
触及锐利的目光,谢珞心中忐忑忐忑的,如今南江地域的局势紧张,能不能进城还未可知。
若是进不去,就得在城外等到天亮开城门,谢珞可不愿。
稍缓了缓心绪,谢珞微微一笑,举手向墙垛的将领作揖:“这位将军,在下乃钦县谢氏嫡系子孙谢瑾,今日有讯传来谢府,告知在下的三叔谢无涯,新任南江县县尉被歹人袭击,如今危在旦夕,族中让在下前来面见三叔一证虚实。”
将领粗旷的面容微微发红,暗道好一位俊俏小郎君,生的真个好看,笑得更迷人,瞧的老子都自惭形秽。
因惭愧而弱了半分气势,连带着说话也毫无平日里雄赳赳的威风霸气:
“本将相信你是谢公子,若是公子想要进城只能坐吊篮上城头,想必公子也知道大魏朝边塞城,自百年前就有规定天色入幕紧闭城门。”
将领话说的客气,但他自有主张,区区三人翻不起大浪,若是不放心,那就派些人跟着他们直到确认身份,若真是谢氏子弟,能结下善缘也不错。
谢珞心下一松,想不到竟能轻而易举的进城,有此可见以诚待人者,人亦诚而应。她又作揖:“自当如此,还未请教将军名讳。”
“谢公子客气了,本将名唤谢震。”
“原来竟是本家,多谢兄长。还请兄长放吊篮。”
“这可当不得,兄弟稍等片刻,愚兄马上放吊篮。”
站一旁的小秋不禁撇了撇嘴,“说是不敢当又叫上了兄弟,就你这粗鄙军汉也配当少爷的兄弟?”
“住口”谢武低声喝斥。
谢珞闻言,淡淡一笑。
大魏朝重文轻武,文人地位崇高,武人地位低下,曾有七品县令敢于呵斥三品武官,而武官竟也不敢言语半句,生受此大辱!
谢珞倒是不在意这些,言行举止谦虚客气一些,让人感受尊重有何不可。何必固守脸面。此番若是桀骜摆谱,哪能这般轻易进去?
不一会儿,主仆三人挨个坐吊篮上了城墙,本家谢兄与谢珞热络寒暄,许是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不由自主的道出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