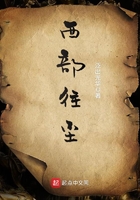一个时辰过去,里里外外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落座主桌的清河王元怿。
“高阳王一直说瞧不起石崇,欲与古人试比高,可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带着石季伦的影子。什么十里锦障,什么杀人劝酒,都是前人玩剩下的。”惊悸稍歇的阳祯,抱着拳头倚靠在门边,在心底暗暗嘟囔着。
“大王,请怜惜奴婢,喝一杯酒吧!”匍匐在地的舞姬哭诉道。她披戴绫罗细纱,满身兰麝的芳香,方才还在欢颜巧笑,此刻却是泪如雨下,叩首求着正襟危坐的白面宰相。区区一杯薄酒,维系着一条鲜活的性命,她和他之前的几个同伴,已经苦苦哀求眼前的铁人许久,可后者仍旧毫无反应。
而眼前的清河王,却依然正襟危坐,面沉如水,完全不为所动。此番被元雍这个宗室长辈邀请,他虽然碍不过面子前来,可却在富丽堂皇的王府里坐立不安。两百年前,石崇和王恺的斗富预示着西晋的颓亡,如今正值巅峰的北魏也遇上了这般情况,让他这个负责决断政务的太傅兼太尉,如何有心情欢畅饮酒呢?
“把这个没用的东西拖下去,杀了扔出府去!你,上去请清河王饮酒。”坐在上首的主人高阳王元雍,不急不缓指挥着。随即就有两个武士奉命上前,把犹自哭泣不已的舞姬拖拽了下去,处理掉又一个牺牲品。
随着远处的惨呼声,被点中的下一名不幸舞姬,不得不抹干脸上的泪水,捧起合浦珠镶嵌的赤玉酒盘,努力挤出惨然赴死的笑容,战战兢兢挪着步子向清河王座位踱去。她们只是毫无地位的豢鸟,生死进退从无自主。
“元怿,你要做样子差不多也就够了。平日里标榜着仁爱道德,可这时候狠心看着他人横死,还能心安理得坐着看吗?”在宗室的那一侧,领军将军元乂倒是看不下去了,替主人打抱不平起来。
“就是,就是!”不少哀怜无辜的宗室公卿们,都闻声附和道。
“我也真好奇,你们是如何做到心安理得的?”元怿带着怒气反唇相讥。
“唉,也罢。叹兹窈窕,生于卑微!你要是执意这么做的话,那我辈也无法阻拦,只是可惜罢了。”仗着万军在手、太后撑腰,元乂对元怿愤怒的眼神毫不在意,轻嗤一声扭过头去,肆无忌惮得继续取乐。
“卑微?尔等莫要忘了,我拓跋氏也是崛起于塞北苦寒之地,汉人强盛时我们也曾为奴为婢,只求在边疆苟活而已。是先祖们筚路蓝缕、开创基业,再加上天命庇佑、万众一心,我等才能安享今日的富贵。岂能因为现在的安逸,就忘却了先辈创业的百般艰辛?”元怿克制住心底的愤怒,环顾着神情淡漠的众人,苦口婆心得劝道。
“宣仁,我是显祖献文皇帝的儿子,这些事情不用你来教训!连当初我大魏从平城南下洛阳时,都是我亲自行镇军大将军之职留守代北,哪一件大事我不曾参与出力?在座的各位大臣,大多是都是你的长辈,平日里配合你那是应当,可是眼下是休沐假日,你还非得打断兴致吗?”话说到这个份上,身为主人家的元雍终于不能冷静坐看,忍不住重重哼了声,唤着这位侄儿的字呵斥道。
“也不知是谁人,丑事闻达于天下,秽行见笑于祖先。平日里顶着副光鲜的头脸,就敢以‘正义’的名义职责他人,拼命揽权、铲除异己。可我麾下的士卒也就是按律拦住了车马,就换得某些人暴跳如雷,什么公义道德都不顾了。”别人会怕,可元乂是根本不怵,他是货真价实的太后妹夫,又有何惧来哉。
“哈哈哈!”听见有人说出大家都不敢说的话,还在执筷端杯的公卿将相们,一个个憋笑憋得满脸通红,不少人都直接拍案笑出声来。尤其是老臣李崇,为了掩饰尴尬他横臂遮面,只露出双眯成缝的眼睛,躲在袍袖的后面不住颤动。
群臣的这副反应,让本来还尚显冷静的元怿,变得更加恼怒难抑、悲不自胜。他苦心孤诣做了那么多实事,难道安享富贵的满朝公卿,就无一人理解、声援自己吗?
“提我作甚?”门口处心虚的阳祯赶忙缩回头去,不敢让元怿瞧见自己。
“清河王时刻忧心国事,犹如一饭三吐哺的周公,这也是值得称颂的盛德。诸位莫要因此迁怨,他一定不是有意阻挠饮宴,只是有心直言罢了。”过了好一会,到底还是崔光发出了微弱的声音,音量不高却神态坚定。可是他能依良心做的也就是如此,当个居中调停的和事佬,而不会得罪满座同僚。
心中寒意刺骨的元怿,听到这话才感觉好受很多,他朝崔老侍中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低声叹了口气。可是即便百官不理解、宗室不赞成,他也会始终坚持着振兴魏国的信念,将自己的宗族引向更远的未来,而不是安逸于眼前的骄奢。他缓和了自身语气,忽视刚才的冒犯,试图与众人再度沟通。
“当初晋人正是如此奢靡,晋武帝后宫万人羊车,平原王司马干剖棺淫尸,王戎的钱财堆积到生锈也不曾动用,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法下咽。那还尚且是天下承平一统的年代,都招来了国家大祸,个个身死族灭。如今我朝只有半壁江山,北有蠕蠕寇边不止,南有梁帝时刻窥伺,怎么可以就安心享受了呢?诸位贵为藩王宗亲、公卿大臣,理应顾念天下社稷啊!”元怿边说着便站起身来,对厅堂内的皇族们啰嗦个不停,期盼着能唤醒各位勋贵。只要能多一分理解,他肃正纲纪的各项措施,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诸位大臣虽然笑过闹过,可大抵上还是明事理的人,闻言纵然是表面上不露声色,可心底也在低声赞许。特别是那些熟读经史的汉族大臣,其实都知道这样的“斗富”乃是歪风,只是没有办法去匡正罢了。至于宗室里里则心态各异了,有的想着应该励精图治、混一四海,有的则想着应该见好就收、安享半壁。
“诸侯王应当日听音乐,玩赏歌舞美女,享受富贵度过一生,这才是先祖立国所期望的嘛。况且治事各有相应官吏,只要负责安排好他们,天下贤人自会为我们大魏分忧,闲杂事不足为虑。若是不停插手帝王事物,居心何在?”元乂毫不在意得答复着,反而暗地里再讥讽了一句,毫不意外得继续唱着反调。
“是啊!说起政务,有清河王独掌不就足够了吗?孤只在乎每天看得到太阳升起,而担忧每天能否看到夕阳,如是而已。百年之后太过久远,谁又会真的在乎呢。”元雍回答得更为干脆,举起了水晶盅,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被侄子晚辈,当众横加教训、说东指西,他的心态自然很是不佳。
“你去求你的千秋万岁名,我们享我们的短暂百年身,有什么好值得争辩的?对待同宗的长辈尚且如此,又有什么面目执掌天下?且去,且去!”斗富的另一个主角,一直安坐如泰山的河间王元琛,也以长辈的口吻出声教训道。他是个简单直爽的人,最瞧不起的就是对方这种“假正经”,自己无乐也不让别人开心。
“唉!”眼见此番反应,元怿摇摇头懒得理会,扭头就想出门。
“嘿嘿嘿,高阳王体恤百姓的辛苦劳作,特地赐给金银、焚烧债券,以示宽厚之意。而不像某些人,忧心社稷民生只停留在嘴皮上,净做那虚情假意之事。”嘴皮子得胜的元乂,还是不肯放过遁去的元怿,乐颠颠得朝着其背影讥讽道。他向来和高阳王臭味相投,自然要替主人家争面子。
“清河王走好,可于榻上向太后问安!将来得个孩儿,究竟是称我为叔还是叔祖,可得细细考量啊!”元雍本就是个气量狭窄、睚眦必报的人,此番和老搭档元乂一唱一和,大大疏解了心中的不快。自己拉下老脸请来元怿这厮,反倒被后者趾高气昂得一通教训,还告辞也不告辞就拂袖而去,已经是极度触犯他的宗王尊严了。
听见背后一阵的奚落和讥笑,元怿的脚步忽然停顿在中途,紧紧得捏住了拳头。
“高阳王,你别以为我就治不了你!互相斗富也就罢了,国家有国家的赏罚,怎能私自施恩于民?你难道是要像齐国的田氏一样,借着机会收买民心吗?”元怿面无表情地回过头来,对着嚣张的叔父撕破了脸。
“你是什么意思?”元雍猛然色变,急得涨红了脸。
“大斗借出、小斗回收,齐民归之如流水。高阳王想做什么,我确实要向太后好好禀告,起码有个对策才行。今上幼弱,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暗存私谋,意图生掣肘之变呢?”也许是彻底的失望作祟,元怿难得得撕下了平日的“仁善”面具,阴测测得冷笑几声,颇有一朝权相的狠辣风范。
“你,安敢?”惊怒交加,元雍瞬间噎口,脑子里一片空白。
“无妨,我也会于明日面见太后,有什么好怕的!我就不信这大魏的天,就被一个人的袖口给遮住喽!清河小儿,既然待不住就少废话,给我滚出去!”群臣塞口之际,天不怕地不怕的元乂拍案而起,支着个腰横脸作对,替好友撑场面。也许是酒劲上涌,也可能是脾性使然,他轻蔑得瞧着眼前的白面竖子,脸上毫无惧色。
“嗤!自己尚且保不住,还去替别人做主!”元怿已经是出离愤怒,指着对方的鼻子哈哈大笑:“光说今年之内,扬州刺史李宠,想要调进洛阳,给你送了整整五车珍玩。洛阳令杨钧想要外放任职,你收下了他的银器无数。更别说在府邸之内,私下聚众昼夜朋淫,乃至于姑姊也没放过!过往的一桩桩一件件,真以为我不知道吗?太后若是得知,你岂能坐得稳这个位置?”
“你敢派人跟踪我!”短暂的惊诧之后,元乂气得汗毛倒竖。
“哼!”元怿冷冷地给了个眼色,浑不搭理。
“好了好了,都是流着同样血宗室的子弟,有什么深仇大恨至于此?来,看在我的面子上,清河王请饮下这杯酒,大家就当做这段话从没发生过,和和气气度日。怎样,给堂叔个面子?”话说道这份上,其他人已经是很再难调和了。河间王元琛倚着自己的威望,端起酒杯来迎上前去,充分表演了什么叫前倨后恭。
“你都管阉竖叫义父了,我怎敢还叫你阿叔?”元怿一把推开,笑得更是凌厉。
“你说谁阉竖呢?我是孝文帝的旧臣,尔等长辈相称又有何错?”本朝的大宦官,中常侍、长乐县开国公刘腾满脸怒气、拍案而起。但大部分人对此毫不知情,怔怔的看着两人的对峙,事情闹得更加无法收拾了。
连这也知道?元琛挤出一丝苦笑,半低着头回到了座位坐下,根本不敢与之对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确是因为无关可做,特意求在刘腾门下当了“养息”,也就是养子的意思。后来又陆续贿赂金宝万计,才赚得个都官尚书的职位,这是将来会明确记载于史书的丑事,可他本人当然没脸承认。
到了这种地步,满朝官员都变了脸色,打心眼里对这位执政清河王刮目相看。一直以来,元怿都是以宽厚大度的形象示人,平日里也不会和人有红脸争执,确实当得上谦逊和蔼的评价。可是任谁也没想到,此人在私下竟然布置了这么多的眼线,几乎侦知了朝堂上的任何风吹草动。表面上人畜无害的绵羊,竟会暗中藏着锋利的爪牙。
“清河,莫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和公卿大臣们争执若此。听我一句劝,不要过分追究他人之过,只要做好自身即可。无论是太后那边还是私下,这些事都休得再提,也算是你自己积德行善了!”万般无奈之下,地位尊荣的李崇颤颤巍巍站起身,豁出老脸替大伙赔笑求情。以他的资历和品德,在场也确实无人可及。
“呵,大魏良臣李尚书!你明明富倾天下、僮仆千人,却还恶衣粗食、食不加肉,乃至于每餐都用韭茹韭菹对付,朝堂上的确人人都夸你勤俭。”元怿就好像是锻热的镔铁,一时间竟降不下温度,遇上谁都忍不住敌意讥讽:“可是你知不知道,洛阳市井是如何评价你的?‘李令公一食十八种,因为二韭一十八’,这就是你邀名邀来的评价!”
“竖,竖子!”半头银发的李崇,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差点就直接薨于当场。
“诸位,汝等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都清清楚楚记着呢,可不要以为没有天道!老实点安享富贵也就罢了,要是以后再敢带头违逆新政,妨碍我大魏国的重振的话,就休怪我不顾情面了!”终于得到了预想中的满座惧意,大获全胜的元怿满意得点点头,昂着个头大踏步离开。徒留下面面相觑的公卿们,兀自怔怔然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