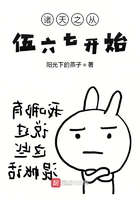冻昏之前,她记得是被几个士兵抬回了军营里。昏睡了大约四五个时辰,她在梦里被乱七八糟的思绪抓醒过来。
她睁开眼睛,滚下榻,在昏暗的光线中跌跌撞撞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但这是深更半夜,这帐子也不是她睡的那小帐,她根本没有辩清方向,朝前走几步,被柱子一撞,又跌坐在地上,呕出两口血来。
她觉得胸口钻心地疼,想来是前日被宣威将军踢的那脚的缘故。
帐子里的光线越来越强,仿佛是有人移来了烛火。她在这刺眼的烛光里险些睁不开眼睛,下意识拿手去挡。
“大半夜发什么疯?”执着烛火的人轻斥了一声。
冷阮缓缓张开眼睛去看,那人的脸在烛火下渐渐清晰,目光炯炯,明朗如星,正是傍晚那名少年。现下只着了玄色寝衣,蹲在地上看着她。
这帐子的轮廓慢慢清晰起来,果然不是她和赛赛睡的那小帐,内里比宣威将军帐子仿佛更加宽敞奢华。
她身子向后仰,拉开与他的距离,“你是谁?”
“也算是我救了你,你上来没一个谢字,倒先问我是谁?”他轻蔑一笑,“你说我是谁?”
冷阮细细打量了他两眼,方道:“邓大将军的长公子,邓羿。”
“哦,想不到你还知道?”邓羿目光中闪过丝惊异的神情。
平日听那些士兵喝酒时闲话,说什么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凭着家里的关系,上战场混个将军的名号和功绩,其实只怕连半个人都没有杀过。众人明面上都唤他“少将军”,私底下则唤他“邓家小公子”。当然,这些都是喝醉了酒放的噘词,只怕醒了说这话的人就不敢认了。而她也是偶然间听到。
冷阮忙撑着地跪在他面前,“少将军恕罪,我不过是个卑贱的俘虏,在宣威将军帐下听个使唤,心想并没有哪里得罪过少将军。还请少将军大人有大量,放我回去。”
邓羿不由笑了笑,站起身走到身后的榻上坐下,“你过来。”
冷阮犹豫了片刻,朝前膝行了几步,跪在离他一米远的地上。
“你怕什么?今晚你就睡在这里,明天我就让人送你回去。”
冷阮垂着头,不答话。
邓羿走上前来,拎着她后脖子的衣领将她拉起来,不由分说往榻上一扔,“你只管睡,明日一早就送你回去。否则,你出了这个门,外面守夜的士兵就有可能砍了你。”邓羿的双眸在烛火的阴影里发亮。
冷阮不敢不信,听话地趴在那榻上。
其实她已经有许多日没睡过这样干净宽敞又舒适的床榻,她卷曲着身子缩在被子里,对此刻发生这一切惶恐不安。加上胸口闷闷地痛着,又被那冰冷的河水一浸,头又昏又沉,终于在不安中睡着了。
她再度醒来,已经日上三竿。
外面的喧嚷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听得分明,她爬起床将这帐子打量了两眼,蹑手蹑脚走到后面的寝室,发现已无人在。整座帐子空无一人。
她回头瞧了瞧有光透进来的帐门,缓缓走向门口,慢慢拉起帐帘。
帐子门口来往的人都住了脚,统统站在不远处打量她,好像都忘了要去做什么,对眼前这个人感到格外新奇。
门口站着的两个士兵咳嗽了两声,其中一个道:“少将军一会儿就回来,你……还是先进去吧!”
冷阮对那些不同于往日的目光感到十分惊异和窘迫,她连忙关上帘子,退了回去。这会子,方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衣着。这布料上好的紫色绸衫略有些宽大,一根玄色的织锦绸带束在腰际,她正光着脚踩在地面上。
她脑中犹如听得重重一声鼓雷,霎时慌了。
终于,听得门口有士兵唤道:“少将军。”
她从榻上慌忙站起来,见帐帘掀开,邓羿领着两三个人走进来。
几人见了她,一起顿住脚看向她,仿佛都对她这衣着打扮很有些品见。
邓羿点了点头,道:“我的衣服虽大些,却比你昨日穿得好上太多,日后就这么穿吧。”
他身后三人,一个着甲衣军服,是他的随护。一个是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衣衫虽旧,却也干净,面容清秀可人,却神情凄楚,想来是和冯赛赛一样。一个则是五六十岁的男子,背着药箱,像是军医。
邓羿回头对那军医道:“她昨晚吐了血,你给她瞧瞧她身上有无别的伤。”说完,又对那女人道,“等会你帮她梳洗一下。”
冷阮忙摆手,“不,不用。”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谢少将军恩德,只是我身为奴隶,实在承受不起。”
邓羿微微眯起眼打量了她一眼,只同身后的人道:“赶紧吧,马上就要拔营了。”说完,自顾自进了寝室,也不再理会她。
“姑……你听少将军的话罢,少将军又不会吃了你。”那着军服的副将道。
那军医随后不由分说将她按在榻上,开口就问:“有没有哪里疼?”
“不疼。”她道。
“哪里都不疼?”
“哪里都不疼,我没伤也没病。”她斩钉截铁道。
军医搭在她手腕号了脉,脸色变了变,道:“若有隐疾请直言,否则出了事谁都担待不起。”
冷阮看向他肃穆沧桑的脸,“我前一日心窝处被踢了一脚,回去心口就疼。我自己觉着应该没有妨碍。”
军医皱了皱眉,向那副将道:“还请将军暂且回避,我要看一看伤口处。”
冷阮却紧张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我……”
邓羿从里面走出来,“先生进去看罢,我在外面等就是。”
军医垂眉一拜,让那女人扶了冷阮到里间,“你帮她把左肩的衣裳脱至胸口处。”
冷阮用手挡开那女人的手,“不用,我不看了。”
“老朽从医三十余载,做军医前也替女人看过病。”
冷阮听得这句话,脸色大变,脱口而出道:“你哪里看出我是个女子?”
军医眉头一凝,咳嗽了一声,“男子就更没什么妨碍了,脱衣服罢。”
那女人果然上手来解她的衣衫,冷阮忙挥开她的手,“我自己来。”
衣衫褪到胸口以上,军医轻描淡写地看了看,拿了块木尺按了按她有些发黑的伤口处,她轻轻一声低呼,军医便收了手,口中嘟囔道:“这宣威将军下脚倒挺狠,衣服穿起来罢。”
冷阮连忙穿好衣裳。
他从药箱内拿几瓶药出来,“这药丸每日口服两次,一次三粒。这药膏涂在伤口处,每日换一次。不消半月,便可痊愈。”
他说完,自己收拾了药箱走了出去。
那女人则不知从哪里取了把梳子来,要替她挽发。冷阮连忙挪开身子,“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你今日见了什么?”邓羿坐在榻上漫不经心地问。
那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答:“奴婢什么都没瞧见。”
邓羿又问:“知道乱说话的下场吗?”
“奴婢明白,奴婢不敢。”她伏在地上瑟瑟发抖。
“阿南,吩咐下去,不许任何人在召她服侍,就说她是我要的人。”
被唤作阿南的副将点了点头,“是。”
“奴婢多谢少将军。”那女人拜了三拜,方才退出了帐子。
邓羿回过头,看见早已梳洗完毕的冷阮站在寝室的门口看着他。那神情中,有些恍惚,有些敌意,亦有些惧怕。
邓羿别开眼,轻声一笑,话语中仿佛有些得意,“收拾收拾,午后出发。”
冷阮看着他走出帐子,那唤作阿南的副将方对她道:“从今日起,你就在将军身边作个随从。你放心,除了方才几个人,没人知道你是女子。不过你这样的相貌即便是男子也是十分惹眼,所以你最好不要再想着回宣威将军那里去,那里的人只怕会生吞活剥了你。”
“我必须回去,”她道,“我姐姐在那里。”
她尚且无暇去思虑邓羿的意图。
全军营都在忙着拔营出发,冯赛赛一面收拾她仅有不多的几件衣裳,一面忧心忡忡地念着一夜未归的冷阮。
“姐姐。”冷阮打开帐帘,好端端站在她跟前。
冯赛赛回头看向她,却唬了一跳,仿佛被她这一身打扮吓住,“你……你怎么回事?”
冷阮心里清楚得很,她虽然依旧是男儿打扮,但发髻齐整,脸面干净,她这一路走过来,那些士兵惊异的目光叫她如芒在背,焦灼不安。
“昨夜发生了一些事,我一觉醒来便在邓羿帐中。”
“邓羿?”
“就是大周邓大将军的长子。”
冯赛赛紧紧抓住冷阮的手腕,握得指节发白,“他知道你是女子?他有没有碰你?”
“他知道,但他,并没有碰我。我才十二岁,想来他还没有那么变态。”
“十二岁?再过一两年你就到可以出嫁的年纪,你以为他见了你的容貌,对你没有想法?”冯赛赛有些慌乱,“就算他暂且不碰你,那些虎视眈眈的士兵,他们见了你如此容貌,还会管你是男子女子?”
冷阮咬着下唇,没有言语。她知道,冯赛赛说的都对。
“你听我的话,今晚就逃,夜里你悄悄逃出去跳河走,你一个人,身量又小,他们不容易发现。”冯赛赛将她仅有一些首饰塞林她的怀里,“这个收捡好,别被人发现,回去路上不至于挨饿。”
冷阮觉得那几件首饰触手冰凉,心口不由闷着疼,“姐姐。”
冯赛赛拥住她,“我怕是这辈子都回不去了,你若回得去,替我立个衣冠冢,以后我死了,也好歹有个归处。”
冷阮亦反手拥住她,叹道:“我回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