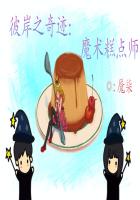为防有变,徐太医一直候在内室,每隔半个时辰便上前查看脉象,一直到辰正,床上的人才悠悠转醒。
徐太医忙走上前,询问道:“大人可感觉好些了?”
张廷无力地嗯了一声。
徐太医转头看向身后,只有一个张晋守在槅扇外,便对张廷说:“大人,下官发现了一件事情,本不该在此时叨扰大人的,可情况紧急,下官想请大人做主。”
张廷说:“说。”
徐太医说:“大人这些天的症状与陛下出奇的一致,下官初步诊断,应是中毒所致。只不过,大人的病情要比陛下轻一些,尚未危及性命。”
张廷疑惑地:“中毒?”
徐太医说:“大人可还记得,陛下曾在青云殿赏赐与您的招摇玉露,下官怀疑,大人与陛下所中的毒,便是从这上头来的。”
张廷不解:“招摇玉露?”
徐太医说:“是的,而且下官私下调查过,陛下病前常饮的招摇玉露,乃是都督佥事夏暝进献,且......且还是经过公主之手献给陛下的。”
张廷身子一僵,半响没缓过神。
徐太医接着说道:“下官也不能断定此事与公主有关。下官曾验过那茶中的毒,那是一种及其罕见,隐蔽的毒,不但服下后短期内寻常太医发现不了,连宫里的银针都试验不出。公主若想谋害陛下,其实不必用如此危险的手段。可......可根据奉茶处的记录,除了陛下与大人,公主也曾饮用过招摇玉露,但据下官观察,公主的身子并未出现不适之处。所以......”
张廷深吸了一口气,“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徐太医道:“大人曾说过,高盛是齐国公的人,下官担心他会将此事透露给齐国公,对公主不利,便没敢声张。”
张廷闭了闭眼,道:“这孩子打从娘胎里我便一直看着她,她是断不会害我的。”
徐太医叹了口气,道:“其实下毒一事,也未必是公主的意愿,也许她与夏大人之间有了什么交易,也说不准。毕竟,公主的母族与陛下之间,隔着那么多条人命,这些恩怨,不是单单靠陛下对公主的宠爱,便能了结的。”
张廷皱了皱眉,沉吟片刻,说:“娘娘在她三岁的时候,便将她交于我教导,娘娘平日里要求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她一言一行,皆遵从师傅的教导。如果她真的做了这样的事,那也是我的过错,是我没有教好她......”
徐太医不以为然:“下官倒不这样认为。有一些骨子里的东西,是生来就有的,没人能改变的了。娘娘也是明白这点,所以才将公主交于大人,希望能通过大人长年累月的熏陶,让......公主不至于同她父亲那样。”
张廷若有所思,“这孩子的性子,终还是随了她父亲。”
张晋走了进来,“大人,怀瑾公主到了。”
张廷与徐太医相视一眼,张廷指了指屋内的屏风,徐太医意会,站到了屏风后头。
清婉走了进来,顾彦跟在后头提着个食盒。
清婉在床边的杌子上坐下,关切地:“老师感觉如何了?学生听子承说,昨儿闹腾了一夜。”
张廷不动声色地凝视着她,说:“好多了。”
脸色白的像张纸一样,唇上也无一丝血色,怎么会好多了呢?清婉强压下心中的愧疚,生怕教他看出自己的异常,伸手接过顾彦递过来的药碗,说:“学生昨日向大夫求了个治咳疾的方子,一早让人熬了汤药送给老师。来,趁热喝了吧。”
清婉舀了一勺子,喂到他嘴边,神情竟有些恍惚。
张廷喝了一口,不由得皱紧了眉头,撇过头,“太苦了。”
清婉心里一急,无措与惊惶交织:“良药苦口,再苦也得喝,不然如何能好?学生给您带了蜜饯,您先把药喝了,好吗?”
张廷凝视着她的眼睛,他能感觉的到清婉在拼命的压制自己的情感,可她年纪还是太小了,那些细微的表情,又怎么可能逃的过他的眼睛,她可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有那么一瞬,张廷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即使她手中喂的是毒药,他也心甘情愿的喝了。
清婉见张廷不再反抗,耐着性子一勺一勺地喂他喝下。
待药碗见了底,清婉拿了一个蜜饯让他吃下,去去苦。
张廷的舌头依旧苦的发麻,蜜饯也不好使,清婉抽了绢帕擦手,浅笑着说:“老师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怕苦,像个孩子似的。”
张廷有几分不悦,道:“你不也是吗?”
清婉想起小时候生病,每回喝药都要闹腾娘亲很久,喝一小碗药,能吃掉一大碟蜜饯,后来去了扬州,没人纵容她闹腾了,她慢慢的也就不再怕苦了。
张廷见她不说话,又问道:“陛下如何了?”
清婉一愣,道:“陛下有太医照料,学生也帮不上什么忙。”
答非所问,是一个人心虚的表现。张廷的心里慢慢的有了答案。
清婉将手肘支在床沿,说:“过些日子,是母亲的祭日,学生和陛下说了,要去宝林寺为陛下和母亲祈福。”
张廷想了想,道:“宝林寺在雁香山,你去了怕是要第二日才能赶回宫城。”
清婉点点头,宝林寺有供香客暂居的禅房,“住一晚也无妨的。”
张廷忽然想到什么,神色微变,浅笑着说:“你既有这份孝心,不如待为师病好后,陪你一块去吧?”
清婉自然高兴了,笑着点点头,“嗯嗯,那老师可要快些好起来。”
清婉一直待到了正午。夏暝的药效果显著,清婉虽不懂医术,却能看的出张廷的脸色慢慢好了起来。和她说话的时候,也不像一开始那样气若游丝。
清婉很贪恋和他待在一起的感觉,哪怕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什么都不说,便让人觉得心神宁静,忘却了周遭的一切。
张承正要去问父亲午饭想吃些什么,经过窗户时,便瞧见清婉一脸花痴的坐在床边,父亲也不知和她讲了些什么,她以手支颐,痴痴地笑着,眼底的爱慕都快要溢出来了。
张承愣了愣,他想起清婉刚到府上和他询问父亲病情时候的那种焦急,一种既诡异,又尴尬的感觉攀上心头,他犹豫了半响,还是决定等清婉走了之后他再进去吧。
屏风后的徐太医一直待清婉走远了,才颤抖着双腿走了出来。
张廷笑了笑,说:“先坐会儿吧。”
徐太医走到圈椅旁坐下,双腿一被解放,他舒服的呼出一口气。今日他算是见到了,外人口中的女阎王,在自己的老师面前,就像个未及笄的娇俏姑娘。张廷这些年在她身上付出的心血,也并非无用。
徐太医稍稍缓了口气,便上前为张廷摸脉,摸了足足半刻钟,方收回手,不住感叹道:“真是奇也怪哉,倘若这药也是出自夏大人之手,那他可真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制毒人才。”
张廷心中的担忧未曾落下,说:“他不但是个制毒奇才,还轻易说服了公主与他朋比为奸,此人若留在朝中,必成后患。说不定,陈氏的死,也与他有关。”
徐太医说:“那陛下中毒之事,属下该如何处理?”
张廷说:“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你也瞒不了多久,那罐剩下的茶叶,我会找人偷偷替换掉。”
徐太医面露犹豫:“您真的要帮夏暝掩盖掉罪行?我们尚不知他的目的是什么,万一......”
张廷说:“公主不是会随意受人胁迫的人,她肯帮夏暝这么做,肯定有她的原因,我会找个机会和她问清楚的。换一步讲,如果此事真的暴露,夏暝是死罪,公主也难逃罪责,我现在帮的是她,不是夏暝。”
徐太医知道清婉对张廷的重要性,不再劝阻,拱手道:“下官明白。”
张廷又叫来了张晋,让他去查查夏暝的身世。张晋不知张廷为何又改了主意,忙应诺下了。
晚间用膳的时候,张廷已经能起身走动了,他用完饭沿着回廊慢慢走着,张承在一旁看着他,唯恐他又像前日那般忽然倒了。
“清婉早上过来和您说什么了?”
张廷不知他这话做何解,道:“没什么,就过来看看我。”
张承微露惊讶:“您昨夜还上吐下泻的,怎的她来了一趟,您便忽然好了?”
张廷不想让他知道这些事情,转移了话题:“对了,爹要不要让你二伯母找个时间去和侯夫人商量一下,把你们的婚期提前一些,陛下如今病重,指不定哪天就......要是真赶上了,你们的婚期就得推迟到一年后了。”
张承与武安侯府的二姑娘前不久刚定了婚。
“算了吧,翰林院最近忙的很,成婚事宜又繁琐,哪抽的出空来?”
张廷察觉到张承不大对劲,问道:“怎么,你不喜欢许姑娘?”
张承挠挠头,避开父亲的目光,说:“不是我不喜欢她。”
张廷严肃起来,说:“那是为什么?之前问你意见的时候,你也没说个不字,如今婚事都定下了,你做出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做什么?”
张承委屈地:“是她不喜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