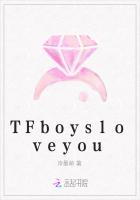不论埃菲尔铁塔在巴黎人心里的评价是什么,在这座塔上铭刻着72个人的名字,就和先贤祠中也安葬着72人一样,只是埃菲尔铁塔铭刻的72个人里一个文学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工程师、数学家、化学家。
文学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沐浴在荣耀的花环中了,比如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的道路,以及用维克多·雨果命名的热气球,相比之下理工科就没那么受世人关注。
普鲁士的快速崛起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文学显然无法铸造大炮,也没有办法让炮弹的射程更远。在经过19世纪短暂的黄金时代后文学创作者们又开始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实用”的理工科,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点缀,人们真正关注的还是那些物理、数学等领域的获奖人物。
是不是真的站得越高离天堂越近呢?
不论是从地上的望远镜还是太空的人造卫星都没有发现天堂的踪影,巴比伦修了一座巴别塔是为了能上天堂,所以站得再高有什么用呢?
1880年法国人修建埃菲尔铁塔不只是为了世博会,还为了向全世界证明法国的国力在经过普法战争后恢复了,从这个制高点往下俯瞰可以看到一座崭新的城市,看不到战争曾经在这里留下的疮痍。
然而维克多·雨果的日记里却记录了被围城时的情况:
1870年11月27日,法兰西学院已经恢复了工作,我接到了通知,今后每周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人们在做鼠肉馅饼,据说很好吃。
一颗洋葱要一苏,一颗土豆也要一苏,一只老鼠能卖到八苏。
他们已经不再让我授权朗诵自己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到处被朗诵。他们做得很对,我的作品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公众。
1870年12月25日,今天巴黎有一则新闻,一篮牡蛎刚到,售价为七百五十法郎。
在艾利斯和保罗·莫里斯夫人卖物品以帮助穷人的集市上,一直小火鸡售价为二百五是法郎。塞纳河结冰了。
1870年12月29日,枪炮声彻夜持续而激烈,普鲁士人继续进攻巴黎。
泰奥菲勒·戈蒂埃有一匹马被征用,要被吃掉,他写信求我救他的马,我请部长批准他的请求。
我救了那匹马。
有个不幸的消息,亚历山大·大仲马死了,德意志报纸已经确认的勒这个消息,1870年12月5日亚历山大·大仲马在位于迪耶普附近的普伊斯的儿子家中去世。
1870年12月31日,早上埃德蒙·德阿尔顿-希拜访了我,看来第落克将军想见我。
三天内普鲁士人发送了一万两千枚炮弹。昨天我吃了一些老鼠,然后不停得打嗝,我写了如下四行诗:
啊,老鼠先生小姐们,
我靠你们生存。
你的微笑让我死去,
你的肉让我活着。
我翻阅日记,发现12月5日那天有一辆豪华灵车从我面前经过那天刚好是亚历山大·大仲马去世的那天,灵车上盖着黑天鹅绒布,上面绣着银星,即使罗马人也会为这样的灵车感到自豪。
我们甚至连马肉都吃不上了,也许是狗肉,也许是老鼠肉,我开始胃疼,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1871年1月2日,杜米埃和路易·勃朗与我们共进午餐。
路易·科赫给姑姑送了一份新年礼物——几颗卷心菜和一对活鹌鹑。午餐时我喝了鹌鹑红酒汤,巴黎植物园的那头大象被杀了,当时大象掉了眼泪,似乎知道人们会吃掉它。
普鲁士人每天继续向我们发射六千枚炮弹。
1871年1月5日,轰炸越来越猛烈,伊西和旺夫正在遭受炮轰。
因为没有煤,无法将衣服烤干,所以不能洗衣服。我的洗衣妇让·玛丽叶特给我说:如果维克多·雨果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能为我向政府要一点煤的话,我就能洗他的衬衫。
1871年1月8日,卡米耶·佩尔坦给我们带来政府的好消息,法军夺回了鲁昂和第戎,朱塞佩·加里波第在努伊获胜,路易·弗雷德黑贝在巴波姆取胜,一切顺利。
过去我们吃棕面包,现在我们吃黑面包,人人吃的都一样,这很好。
昨天的消息是两只鸽子带来的。
一颗炮弹炸死了沃吉哈街一所学校里的五个孩子。
《惩罚集》的演出和朗诵不得不停止,剧院没有煤和煤气,因此无法照明,也无法取暖。
1871年1月30日,小让娜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她无法玩耍,佩里家尔小姐给让娜带来了一个新鲜鸡蛋。
1871年1月31日,小让娜还在生病,她患有轻微的胃黏膜炎,医生说炎症会持续几天。、我的侄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腌制的牡蛎。
1871年2月1日,小让娜好些了,她对我微笑了。
1871年2月2日,我一直胃疼,吃不惯马肉,昨天我对坐在我旁边吃饭的的埃内斯特·勒菲弗夫人说“那些动物肉让我难受,我对马爱恨交加。”
从1870年11月开始,巴黎市民为了解决饥馑问题,便开始杀死巴黎植物园里的动物们了。
诺亚方舟是个神话,即便不是狮子、老虎,人也是要吃肉的,方舟上的动物们不可能和平共处,至少也要把它们都关在笼子里才安全。
温室(green-house)就像是个大号的玻璃盒子,里面装着不少绿色植物。
克劳德-路易·纳维尔除了发现了空气动力学方程式外,他还发现紫外线无法穿透玻璃,但是能穿透石英,植物的光合作用并不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植物的歌勒光合色素主要吸收可见光中的蓝紫光和红光,因此才会呈现出绿色。
颜色的三原色是红黄蓝,这也是光的基本色,这个美术上常用的三色调和理论是化学家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提出的,同时他还在1863年与1879年担任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巴黎植物园里面。
在72个名单中有一个人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有很深的关联,他名叫乔治·居维叶,他不仅是巴黎大学自然史教授,还是法兰西学院物理学终生教授,他特别研究了巴黎地区的矿物地理和化石研究,是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者。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拿破仑排第一,居维叶排第二,第三是奥康奈尔,我将成为第四位。
居维叶提出了器官相关法则,认为动物的身体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身体各部分都有相应的联系,入牛羊等反刍动物有磨碎草牙齿的牙齿,就有相应的咀嚼肌和消化道,虎狼等肉食动物则有与捕捉猎物对应的运动、消化功能。
有一次他睡得正熟,几个爱恶作剧的学生打算捉弄一下居维叶,他们趁着居维叶酣睡时将窗户哐啷一声打开,被惊醒的居维叶看到一只满脸硬毛,张着血盆大口,并且头上长有犄角的怪物正发出吓人的嚎叫,两只蹄子伸到了窗户里,眼看着就要扑向居维叶。
这动物要是神学院的老师看到了非要大叫“魔鬼”,要是碰巧老教授心脏不好这一下恐怕要吓得心脏病发作,但居维叶只是撇了一眼就继续睡觉。
几个学生没有恶作剧成功,只好各自站出来,居维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学生们反而问居维叶为什么不害怕,居维叶笑着说“难道我没给你们讲过吗?凡是长着角和蹄子的动物都是草食动物,是不吃肉的,所以我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那几个倒霉学生这才恍然大悟。
1821年居维叶提出灾变轮,认为地球的历史上曾有多次巨大的灾变事件,原来的生物都会被毁灭,继而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根据灾变轮,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变化都会突然而迅速的且是灾难性的,比如海洋干涸成为陆地,陆地又隆起成为山脉,陆地也有可能变成海洋等等。
他推算出地球经历过四次灾变,却没有推算出自己会在1832年时死于霍乱,也就是路易-菲利普在巴士底狱广场树立七月柱的一年。
“为什么你会想到绿箱子?”龚塞伊看着不远处静静矗立在塞纳河边的植物园温室问西弗勒斯。
“你去哪边?温室还是化石博物馆?”西弗勒斯问龚塞伊。
“我觉得是植物园。”龚塞伊撇着嘴说“我记得那个通风口的柱子上有植物藤蔓的花纹。”
“那我去化石博物馆。”西弗勒斯说“有发现立刻联系。”
说完他就朝着那幢红色的房子走去,它的颜色粗看之下和维克多雨果的在孚日广场的房子外墙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