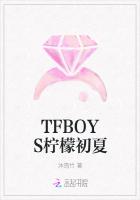阿沫说:“那天在那个村子里,看见那些牛被杀,你先走一步,说好了在前面等我们。我们向后赶来,却根本没有看见你,你当时到哪里去了?”田海满面羞惭,低着头不说话。阿沫看了他的脸色,不好再问。
出了殿来。老烧棍老远地大声说:“我的奴才,看仔细了?里面还有人没有?”阿沫大声地说:“没有了,就是这十数个。”
田海虽然手脚被铐住,耳朵却还灵光,听见那个邋遢老头喊阿沫是奴才,阿沫却又应得这样爽快,觉得好生奇怪。
老烧棍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悠悠地走了过来,看见了这些人身上依然还在铐着镣铐,不由得大怒道:“还不快解开?”
祝毅急忙命那些手下:“还不快解开?”那几个手下方才给他们打开镣铐。
那些人终于被解开了镣铐,个个大喜若狂,欢呼起来,手舞足蹈。独有田海虽然脸上身上都轻松了,却不是那么欢喜,揉揉双手,再揉揉脚踝。
祝毅将军带着那一干士兵,灰溜溜地进殿里去了。
老烧棍面对着这十数个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的人,朗声说:“今天,我打赢了飓风分殿,救了你们出来,你们高兴吗?”那些人纷纷拜倒在地,大声说:“高兴高兴,感谢老神仙救命大恩。”
老烧棍说:“我不是老神仙,我叫做老烧棍,老烧棍,老烧棍。”他一连把自己的名字大声地重复了三遍,似乎生怕这些人记不住似的,而且一声比一声高,大得震耳。
那些人又连连磕头,嘴里不停地说:“感谢老烧棍救命大恩,感谢老烧棍救命大恩、、、、、、”“老烧棍威武,战胜了神殿!”
起码一连说了几十遍,那个老烧棍脸上得意洋洋,一只手不停地去摸着下巴处的那缕胡须,两眼看天。
那些人还在不停地磕头磕得起劲,说话也说得起劲,田海却没有跪,随便鞠躬一个了事。
“感谢老烧棍救命大恩,老烧棍本事齐天,打败了神殿、、、、、、”这一句反复的话,一直杂乱地重复响着。阿沫都听得耳朵里快要起茧子了,见了老烧棍还在受听得舒畅,阿沫忍不住打断说:“老烧棍,我们该起身了吧?”
老烧棍这才说:“好吧,记得我的名字就好。你们回家去吧!”那些人听了,又再磕得几个响亮头,又再说得几句客气话,终于一骨碌翻爬起来,急急地溜了。
那个田海站在那里,不知道在踌躇什么,阿沫过去问他说:“他们几个呢?”田海说:“你都不知道,我还知道个什么?”阿沫笑笑,明白自己简直是在问不该问的话,简直是一个糊涂的问题,人家田海早早地就被弄去关押了起来,他怎么会知道呢?
老烧棍对田海说:“你既然已经脱离苦海,怎么还不走呢?”
阿沫急忙说:“他是和我一起的哥们。”老烧棍哈哈地一笑,捋了一下下巴处的胡须说:“好啊!看来我又白捡了一个奴才。”那个田海奇怪地看了老烧棍一样,又转头来看阿沫,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脸色是在觉得惊奇:你这个阿沫怎么成了这个老头的奴才了啊?
阿沫脸上浮现着羞愧的神色,却没有辩解什么,只是说:“我的这个哥们,他可是一个自由人啊!”老烧棍笑笑说:“和你们逗着玩的,走吧。我们找个地方睡觉去、吃饭去。”
阿沫忽然想起什么来,说:“应该是先吃饭、后睡觉吧?”老头说:“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有多大的关系呢?”阿沫说:“不是应该先看见闪电,后听到雷声吗?怎么在惊雷山上,却是先听见雷声、后看见闪电呢?”老烧棍说:“那不是在惊雷山吗?你以为是在一般的地方哦!”
听着两个的对话,田海说:“你们已经去了惊雷山吗?”阿沫点点头,接着把与田海分别后的情形说了一遍,田海惊奇地说:“那个小女孩竟然就是百变蛇妖哦?”老烧棍说:“百变蛇妖有许多变化,最是叫人防不胜防的,是个邪恶的厉害角色。”阿沫说:“她与其陷害我,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呢?”老烧棍说:“那几日她才蜕皮不久,是她功力最低的时候,她只好用这些卑鄙的手段了啊!”田海不解地说:“她和你无冤无仇,陷害你干嘛呢?”阿沫纳闷地说:“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呀。”老烧棍说:“她是有点忌惮你的银弓金弹,老远就能伤人,所以一心急着先要除去你才省心。”阿沫与田海一起愤愤然地说:“她个妖孽,下次定然不会放过她。”
老烧棍掰着指头算算,说:“现在晚了,她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你们两个加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阿沫说:“那怎么办?”
老烧棍说:“这样吧,我对付他应该没有问题,就作为你两个欠我一个大人情吧,我去帮你们除掉她。如何?”阿沫笑笑,心里寻思:她本来就和你有仇,还说什么帮我们除掉她,算作我们欠你人情,你可真会算计?
老烧棍看他笑而不答,说:“你不回答,那我就不管了啊!”
阿沫忍不住说:“你本来就和她有仇不是?还说是帮我们除掉她?”
老烧棍说:“既然如此,哪天我看见她,我就抱着手,看见她杀你们,如何?这总该划算了吧?”阿沫说:“不如我们联手一起对付她,如何?算作合作!”老烧棍大笑说:“以前嘛,我还没有绝对的把握胜她,现在呢,可不是我怕她,是她怕我喽。”说完了又仰头大笑。
阿沫说:“怪不得她当时要急于除掉你,就是怕你练成了驱雷之法以后难以对付?”老烧棍又笑,嘴里说:“看来你还不笨!”田海却说:“她要除掉你,可以明的不行暗的来呀!”老烧棍撇撇嘴说:“随便她来明的暗的,我都不怕她。”阿沫说:“还是小心一点好,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烧棍只是笑笑,满脸的毫不在乎。
几个边说边往前走去。看看天色昏黑了,老烧棍说:“今天一场大战,虽然赢了,但还是有点点累了,我们找一个住处,歇息一晚,歇息够了,明儿好去挑战第三神殿。”田海惊奇地说:“还要去挑战第三神殿?”老烧棍大笑,说:“厉害吧?”阿沫愁苦着脸说:“就因为太厉害了,所以才要去一家家挑战呀?人老心不老!人心不足蛇吞象!”
阿沫看看田海说:“你怎么会被那些神殿里的人抓去呢?”田海低下头,有些羞愧地,踌躇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回事呢!肯定是吃饱了撑的。”老烧棍大笑说:“你个小娃儿不要担心,都包在我的身上,一一给你讨回一个公道来,明天一去,我就问他们,你们如何得罪了我的小跟班,今天,赶紧向我的小跟班跪地求饶,不然,打得你们满地找牙!”田海听了,顿时喜不自胜,嘴里说:“太好了太好了!帮我出它一口恶气!”几个说着话,到了一家旅店门口,上面挂着一个旗号,叫做“天涯旅社。”老烧棍说:“好了,就晚上就住在这里。”正要往里迈步,看见阿沫去兜里摸什么,老烧棍说:“不要你破费,我这个当主人的,连这么一点小钱都要奴才破费,要是传扬出去,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三个人说着就走了进去。这时,门外面不远处有一个人,在那里鬼鬼祟祟地注意看他们这里。
三个人就要了三间房。
到了半夜时分,老烧棍忽然悄悄地起身,开了房门出来。
此时夜色正深,四下里一片朦胧。借着一点淡淡的夜色照亮。老烧棍轻手轻脚地走在大街上。走完了大街,他想想,拐进了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两面墙高,顺着进去,不知道到哪里去。老烧棍走得很慢,边走边侧耳听听。
忽然,不知道哪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之声。老烧棍顿时大喜,那神情,那动作,犹如一个在沙漠里苦行的人,囊里的水已经喝完半天了,正在嘴干舌燥渴得发慌,忽然之间就撞见了一片绿洲一样。老烧棍辨明了那婴儿啼哭的方向,就赶紧大踏步赶去。
隔得不远,几步之间,就赶到了,只见是一个妇女用围巾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那里。老烧棍大喜,闪身过去,从那个妇女的怀兜里劈手夺过那个婴儿,转身就走。奇怪的是,以往这些妇女都会大哭大闹地追赶,今夜之间,这个妇女丢了婴儿,却既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默默地看着。老烧棍的心里虽然浮起一丝奇怪,却也没有留心,只当是这个妇女吓得呆了。
老烧棍抱着婴儿到了一个拐角处,蹲下来,不知道在那里弄了什么,那个婴儿居然发出了嘻嘻的笑声,
那笑声既清脆又悦耳。
片刻过后,老烧棍抱着婴儿回来了,那个妇女还呆在那里。老烧棍把手里的婴儿递还给她。从兜里摸了一些钱,那妇女接过了钱,也不多谢,转身就走了。
老烧棍溜回了住处,几个都正在睡得香。老烧棍脱了衣裤,爬上床就睡。
第二天天刚刚亮,老烧棍起得最早,他吩咐旅店主人煮三大碗面。然后他去叫醒了阿沫,又去叫那个田海。
阿沫下了床正在穿衣服,听得老烧棍在外面说:“阿沫,阿沫!”阿沫急忙说:“怎么了?”老烧棍说:“我的那个第二奴才不见了!”“我的那个哥们吗?”阿沫听得一惊,急忙穿好出来。
阿沫说:“他不见了?”老烧棍用手捋着胡须说:“是啊。溜到哪里去了?”
阿沫觉得好生奇怪,急忙来到田海住的房间,里面的床铺上,铺盖胡乱蹬着,枕头也歪在一边。阿沫看了这个场景,说:“他会到哪里去了?”
老烧棍有些生气地说:“这个小屁孩儿,救了他,一声谢都没有就溜了。”阿沫说:“只怕他是被人劫走的。”
老烧棍听得一惊说:“是被人劫走的?”说着话,他都仔细看了再看。
阿沫指指那个被蹬翻的被子,说:“肯定是被绑走的。”
老烧棍有些火气上来,一拍大腿,说:“哪个龟儿子,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劫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