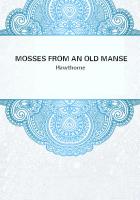楚歌寻声看去,便见迎面而来一位朴素的妇人。
很快,妇人到了两人的近前。
“妈……”楚歌有些不太自然地叫了声。
“我来看看你和义洲。”刘母温和地对她笑笑,眼角的余光却扫着于继晨:“你和朋友出去了?”
“嗯。”楚歌竭力不着痕迹地回。
眼前的妇人是刘义洲的母亲,她一直住在老家,还不知道她和刘义洲要离婚了。
楚歌看到刘母拎着旅行袋的手都冻红了,紧张地问:“妈,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给我和义洲打电话?”
“下午的火车到的,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怕耽误你们工作。”刘母憨厚地笑着说。
楚歌有些心疼刘母,赶紧去帮她拎旅行袋。
“妈,我帮你。”
于继晨抢先一步,接下刘母的旅行袋。
“阿姨,我帮您拎吧。楚歌今天不舒服。”
于继晨的话让气氛一瞬间变得尴尬,楚歌想解释,又觉得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刘母将视线落在于继晨的脸上,问道:“这位是?”
于继晨倒是神态自然,回道:“阿姨您好,我叫于继晨。楚歌的邻居。”
“谢谢你了,小伙子。”刘母笑得有些勉强,她将视线调向楚歌:“楚歌,快上楼吧。天冷儿,你怀着孩子不能在外边待太久。”
于继晨的眉心不着痕迹地轻皱一下,老太太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他微侧视线,看向楚歌。楚歌这会儿的脸色已经一片惨白,嘴唇都有些哆嗦了。
刘母眼角的余光始终打量着于继晨,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后,心下稍安。以为他那一下皱眉,是因为楚歌有孕而不能起色心才不爽。
楚歌面色沉重地看着刘母,还是点了点头。有些事情,还是刘义洲自己去与刘母交代比较好,哪怕将她说成过错方。既然她决定了要和他离婚,就没指望能得到他家里的人谅解。
当天夜里,刘义洲没有回家。刘母之前也见多了刘义洲出差或是加班不回家。她这次来也是想照顾楚歌,以及她未来的孙子。
楚歌临睡前又看了一些文件,才拿出医生给开的药,去厨房倒水吃药。她故意想避开刘母,免得尴尬。
楚歌倒了一杯水,刚想把药送进嘴里。
刘母的声音在昏暗的客厅里猝然响起,“楚歌,你干什么?”
楚歌的手一抖,药片滚落一地。
刘母快步走过来,痛心疾首地说:“你们这些孩子啊。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懂。怀孕怎么能吃药呢?还好我看到的快。你没吃吧?”
“没有。”楚歌的表情尴尬,“妈,其实我……”
“你怎么了?”刘母摸了摸楚歌的头,“还有点热。妈知道你不舒服,但是为了孩子,这也没办法。”
刘母拉着楚歌回屋,又端了一盆热水进门,浸湿毛巾给楚歌擦手脚。
楚歌尴尬无比,说:“妈,我自己来。您早点睡。”
“妈没事。你困了就早点睡。妈守着你。保证你们母子俩平安无事。”刘母憨厚地笑着,执意留下照顾楚歌。
楚歌面对这个阵仗,哪里睡得着啊。
刘母像是怕她无聊,开始从她生刘义洲那时候讲起,一路讲到刘义洲念大学,娶楚歌。
关于刘义洲年幼时候的往事,楚歌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像是今夜这般,从头到尾了解得透彻。若是换了从前,即便那些是她没参与过的过往,她也会跟着他一起幸福。可是,在这一刻听到,她的心里只觉得五味杂陈。
第二天一早,楚歌不顾刘母的劝阻,早早的出门,不想再与刘母以尴尬的方式相处下去。当着刘母的面,她连医院开的药也没办法带上。
让楚歌没想到的是她才一出单元楼,就看到了靠在车门上的于继晨。
他上身着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下身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即便满面的疲惫,但衣着却依旧规整。
晨光照在白雪上,反射出迷人的光芒镀在他的身上。让这个男人看着格外的温暖。
楚歌有些惊讶地问:“大早上的,你怎么站在这里?”
“送你上班。”于继晨语气自然地边说,边拉开车门。
楚歌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
于继晨关上车门,才快步走到驾驶座一侧,开车离开。
楼上的刘母看着楼下的一切,表情格外的沉重。
于继晨的车子开出好一段距离,楚歌都始终沉默着。视线明明落在车窗外,却无半点对景色的流连。
于继晨单手扶着方向盘,揉了揉眉心:“他的家人还知道你们要离婚?”
“嗯。”楚歌微侧头,看向他:“我跟刘义洲说,孩子是我自己流掉的,因为我恨他。”
于继晨的眸色深了深,心疼地说:“何必这样惩罚自己?”
“为什么你不觉得这是我对刘义洲的报复呢?”她的眼底晃动着泪花,唇畔挂着一抹感激的笑。
“你不会用自己的孩子作为报复。”于继晨肯定地回。
“……谢谢你。”楚歌哽咽了半天,才艰难地吐出三个字。
汽车在红灯的路口停下,于继晨转头看向楚歌,眼中的情绪复杂,有心疼也有抱歉。末了,他打开车载音响,在红灯结束时发动车子,什么都没有说。
送她到公司时,他递了一包药给她,和昨晚医院开的一模一样。楚歌想说“谢谢”,又觉得于继晨为她做的,不是“谢谢”两个字能表达的。
于继晨却仿佛懂她的心思,笑嘻嘻地说:“欠我三顿饭了。”
“好。”楚歌接过药,下了车。
楚歌进办公室时,陆娇娇正在帮她打扫。
看她把一包药放在桌子上,陆娇娇暧昧地笑着问:“是董事长拿给您的吧?”
楚歌愣了下,不解地看着陆娇娇。
“昨天我发现楚小姐的药忘记在办公室了。董事长说他给您送去,就把药拿走了。”陆娇娇解释道。
楚歌愣了下,平静地回:“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好的。”陆娇娇点点头,退出办公室。
陆娇娇才出去十分钟,就又冲进了楚歌的办公室。
“楚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启航出事了。一夜之间,在网上闹大时,启航的人才发现。各大网络,各大社交软件上,各种真的假的传闻,一个比一个劲爆。
这是楚歌进公司以来,第一次激动地冲到刘义洲的办公室前。
谷倩玲见她来势汹汹,连忙起身阻拦。
“楚小姐,刘董在里边开高层会议。你不能进去。”
“让开!”楚歌这会儿着急,不想与她多费口舌。
“楚小姐,不要为难我。”谷倩玲挺胸抬下巴,差点就没抬起双臂去拦楚歌的去路了。
“让开!”楚歌不客气地直接推开谷倩玲。
谷倩玲的身体趔趄,穿着高跟鞋的脚扭了一下,险些摔倒。
楚歌忘记了敲门,直接推开办公室的门。她进门时,刘义洲正在和高层开会。
“公司是不是真的挪用了一格基金的回款?”楚歌猜到他们正在研究的事情,一定也是她想问的。
不等刘义洲回答,乔远抢先回:“楚小姐,我马上会让公关部发布公告,严厉打击造谣的人。”
楚歌看向乔远,不客气地说:“我是在问刘义洲。”
“你们都先出去吧。”刘义洲等所有人都出去了,示意楚歌坐下。
见她坐下,刘义洲走到饮水机旁,拿出柜子里的杯子,动作利落地倒了杯水,放在楚歌的面前。
楚歌看着面前粉色的陶瓷杯一怔,一抬眼,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正放着同款的灰色。两个杯子都有些旧,也不是什么高档瓷器,还是创业那年,她在街边小店买的。那时候,她曾天真地对他说:“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还站在这,拿着这对杯子喝咖啡多好。”
只是,物是人非,杯子还在,人也还在。那时候的幸福感已经不复存在。她没有想到,他还留着这对杯子,她以为他早就丢掉了,再换上配他身份的高档货。
她努力地将自己从回忆中抽出,说:“不必客气了。”
“我是倒给你吃药的。”刘义洲把昨天没来得及交给她的药袋子拎到她的面前,“你这个时间生气,十有八九会忘记吃中午的药。”
楚歌看着桌子上的药袋子,心里酸涩,五味杂陈。
“你刚出小月子没多久,”刘义洲的声音有些哽咽,“天又冷,即便是感冒也不能大意。”
“刘义洲,我会保重我自己,活得好好的。”楚歌转头看向他,冷漠地说:“我们谈公事吧。”
“好。”刘义洲叹了口气,“公司确实挪用了一格募集的那笔回款。”
即便之前已经想到,楚歌还是不免失望。
“用在了百易的第二笔投资?”
“对。”刘义洲并不打算隐瞒她。
“在冯威跳楼后?”楚歌近乎肯定地问。
“对。”
即便已经猜到答案,听他亲口承认,楚歌还是失望的。
“你知道网上现在怎么说你吗?他们说你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注入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是为了转移资产。”楚歌说到最后,声音已经拔尖。于她而言,此刻的感受就好比是一个出轨的丈夫,现在还想祸害死他们的孩子。
“楚歌,我没有。”刘义洲解释的时候有些急切,他害怕看到她眼中的鄙视,又解释道:“只要百易的新型建材拿到专利,百易活过来,我们可以一并收回两笔投资。”
“刘义洲,难道你忘记了吗?风险投资就一定会伴随着风险,所以这个风险一定要是我们能承担,能面对的。”
“如果我不为百易第二次注资,百易死了,冯威在我们公司跳楼,保底增值的机制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连累我们公司倒下了。”刘义洲的声音沉稳,他毫无悔色的表情仿佛在说“我没错”。
“公司几个月前资金链就断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楚歌这才意识到她和刘义洲之间的问题,不只是谷倩玲。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无话不谈的亲密爱人变成了中间隔着许多的秘密。
刘义洲拿起一支烟,又烦躁地放下。
“现在公司没有倒下,还签下几个不错的项目。我相信启航会跟那年一样,活过来的。”
楚歌知道刘义洲口中的那一年,公司艰难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年轻气盛,没有经验才会惨败,该乖乖的放弃,回去好好工作。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一起挨过来了。
“刘义洲,启航是我们一起创立的,我比谁都不希望启航倒下。如果公司受百易的事情连累倒下了。我们清算破产,但是我们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可是,一格基金这笔钱是别人的血汗钱,我们如果还不回去,我们不只是做了亏心事,你还要坐牢的。”楚歌失望地看着刘义洲,她这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有情怀的刘义洲了。当年的他,一定会和她一样,情愿启航倒下,情愿自己失败,也不会愿意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现在的他就跟所有被金钱和欲望主宰的人一样,为了不让自己的金钱帝国倒下,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担心我?”刘义洲苦笑着问。
楚歌与他对视了几秒,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就算是现在发公告说没有挪用这笔钱,逾期不能支付,也隐瞒不了。”
“离支付日期还有半个多月,环业那边已经在退出了。不会有问题的。”刘义洲的语气并不是很肯定。
楚歌也惴惴不安,挪用款项这么敏感的事情,公司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却被言之凿凿地爆料出去。这说明肯定有人在整启航。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启航想度过这一关很难。
就如乔远所说,启航和一格基金很快发了公告,否认网上的指控,承诺到期一定会准时把款项打入一格基金,让他们发放给有限投资人,并扬言要追究散播谣言的人法律责任。
散播谣言的微博小号并没有因此被吓到,让网友等着看启航和一格一个月后被自己的公告打脸。
两周过去了,早已经签署股份回收合同的环业,以各种理由拖延着不肯把款项转给启航。距离最后限期越来越近,网上的舆论和各个维权群又活跃了起来。一格基金的负责人差点把启航的门槛踏破了,一次又一次地上门。除了舆论有规律的发酵很诡异,在到期那天,有人准时扯着条幅出现在了启航的门口。
这事如果不是有人扇动,不可能反应这么快。至少要在到期的一周后,才可能出现这么混论的情况。
楚歌看着那一张张情绪激动的面庞,拉条幅,上网声讨时,他们一个个看似强势,可这种种做法恰恰是最无力的表现。
启航召开了紧急高层会议,所有人都一筹莫展,公司的资金链断了,那是一大笔钱,不是哪个人想帮忙就能解决的。
刘义洲离开会议室时,整个人都处在努力压抑后的颓废状态中。所有人都恨不得躲着他走,免得踩雷连累了自己。所以在楚歌去刘义洲的办公室时,谷倩玲再也没有阻挠。她觉得楚歌是来看笑话的,会和刘义洲之间爆发世纪大战。可是,在楚歌离开刘义洲的办公室后,一格基金正式发布公告,三天内向有限合伙人发放款项。人们看到这个消息时是震惊的,认定是拖延的套路。可是,这一次剧情没有反转,一格基金如期发放了所有款项。
一场可能会危及公司的危机在风平浪静中化解,后来,有消息传出,是在楚歌的太太团帮助下,启航才能度过这次危机。楚歌的太太团除了以投资盈利做公益以外,还会因此收购一些专利,再以专利入股,与合适的合伙人办厂投入生产,因此赚到了不少钱。太太团极为相信楚歌的眼光。楚歌这次以百易的新型建材潜力作为推动点,组织了超二十位阔太太以有限合伙人的方式买下了启航二次入股百易的股份。启航顺利拿到钱,才能从一场危机中脱身。但楚歌知道,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完。百易的新型建材无论如何都必须研究成功。
至此,再也没有人敢轻视楚歌的太太团。据说太太团里不乏官商各界名人的太太。楚歌和刘义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仿佛也因此得到了缓解。公司里看热闹的不怕事大,在楚歌进公司的最初就开了赌盘。那时候,觉得小三谷倩玲会胜利的比例还比较大,如今局势逆转,这一局原配完胜。大家都等着谷倩玲出一招必杀,再让局势翻转。
楚歌一天比一天忙,在所有人都认定她是回公司抢男人,企图利用自己在事业上与刘义洲势均力敌,驱逐小三的时候,楚歌却天天都伏在案上,认真地梳理着她离开公司这一年多的业务。对传言,她置若罔闻。
陆娇娇是楚歌在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她亲自去招聘的新组员,果真与上一批人事部给过来的员工不同了。再加之如今太太团在公司中的地位不同,全组上下干劲十足。
这些天来,楚歌难得一次早下班,她站在马路旁,准备拦一辆出租车回家。
刘义洲的车缓缓停在她的面前,车窗降了下来。
“一起回家吧。我答应了妈今天回家吃饭。”
“不用了。我打车回去就好。”楚歌别过脸,并不想看刘义洲。
“上来吧。一会儿公司的人看到,明天又要有新版本的故事了。”
楚歌微迟疑,但还是没动,她并不在乎公司的流言。换句话来说,她要是在乎,也待不到今天。
“我们今天一起回去,我跟妈把话说清楚。”
楚歌看向刘义洲,她一直在等他这句话。她天天和刘母相处得太尴尬,该由刘义洲这个当儿子的把话说清楚。
楚歌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子很快驶入车流,两人之间的气氛让不大的车内空间格外压抑。
“从回公司开始,就没见你开车。”刘义洲没话找话。
楚歌原本平静的脸色忽然大变,她的身体微微有些哆嗦,看向刘义洲的眼神里有仇恨蹦出。
刘义洲吓了一跳,试探着问:“楚歌,怎么了?”
楚歌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转过头去,看向窗外,轻描淡写地回:“没事。”
“晚上想吃点什么?”刘义洲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干,“一会儿我在市场停一下,去我们总去那家海鲜店买点东西吧。”
楚歌转头看向刘义洲,说:“那家海鲜店已经搬走了。”
刘义洲尴尬地笑着说:“没关系。我们换一家。”
楚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声音无波地回:“我吃海鲜过敏。”
刘义洲有些微地惊讶,脱口问:“你以前不是最爱吃海鲜吗?”
“刘义洲,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一天一个小时钟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更何况你说的以前,你还记得是多久以前吗?”
楚歌过于平静的语气,却犹如一颗深水炸弹,扔进刘义洲的心湖。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再开车,更不知道一向喜欢吃海鲜的她为什么会对海鲜过敏。即便是帮启航渡过难关的太太团,他虽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轻视,却也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一件有意义的善事。楚歌说的对,这世界上的人和事,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他们之间隔着的是人生的巨变。
再次面对面,他们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
刘母来了大半个月,儿子只见了一面,还是在外边请她吃了一顿饭。儿媳妇虽然大部分时候回家,与她相处的气氛却总有些怪怪的。刘母一如既往买了一大堆菜,给楚歌补身体。
饭菜刚上桌,门铃就响了起来。
刘母听到门铃声一喜,还以为是刘义洲或是楚歌回来了,也没看门镜,就拉开了门。
下一瞬,她脸上的笑一僵,看着门前陌生的年轻女人,狐疑地问:“小姐找谁?”
“阿姨……”女人委屈地咬了咬唇,“我是专程来找您的。”
“你是?”刘母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我叫谷倩玲,是董事长的秘书……”谷倩玲的声音哽咽,泪水已经噼里啪啦掉了下来,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刘母的心情越发沉重,却不动声色地说:“进来说吧。”
刘母始终平静,神情冷淡地请了谷倩玲进门,丝毫没有面对楚歌时的温和。
“谷小姐,你坐,我去给你倒水。”刘母客气且疏离地招呼道。
谷倩玲抹去眼泪,赶忙说:“阿姨,不用忙了。您叫我倩玲就行了。”
“谷小姐不必客气,来客人哪里有不招待的道理。”刘母的唇角微弯,看似温和的笑意里却透着凉意。
谷倩玲刻意奉迎的神情一僵,刘母摆出的姿态已经很好地告诉她,她在这里不受欢迎。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抹笑:“麻烦阿姨了。”说完她向后退去,走到沙发边坐下。
刘母走进餐厅,很快倒了一杯水出来,放在她的面前,自己则走到另一侧沙发坐下。
谷倩玲被刘母直射的视线盯得有些紧张,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端起面前的水杯。
“谷小姐,如果我儿子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刘母顿了顿,看到谷倩玲握着杯子的手一颤,又接着说:“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做背经离道的事情。”
这样的局面,以及刘母这样镇定的反应是谷倩玲没有想到的。
她努力整理了下情绪,放下水杯,眼中又盈起了泪光,委屈地说:“阿姨,我和董事长是真心相爱的。”
“真心相爱?”刘母轻蔑一笑,“如果他真的爱你,就不会让你自己出面。如果你真的爱他,也不会不顾他的想法,直接找上门来。”
谷倩玲被刘母的话堵得一哽,脸色一时间红白交加,很精彩。
“谷小姐,你和我儿子的事情,最好去跟我儿子解决。”刘母站起身,大有送客的意思,“孩子的事情,我虽然一般都不愿意多管。娶媳妇这事,必须我说了算。人品不正的,想进刘家的门,除非我死了。”
谷倩玲的脑袋里轰的一声,羞得整张脸烧了起来。她听说刘义洲的母亲是个农村老太太,她以为好对付,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老人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她。
她眼中盈着的水雾凝结成水珠,滚出眼眶,声音有些失控地问:“为什么楚歌可以,我不可以?”
计划里,本来没有这句话,可是刘母的羞辱让她忍不住如此对比。
刘母面色沉暗地看着她,并不打算回答她的话。这是一种蔑视,等同于在告诉谷倩玲,她没资格与楚歌相比。
谷倩玲激动得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唇边浮起故意加深的讥讽笑意,“我至少不会像楚歌一样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
她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直接将刘母劈中。刘母的神色一震,瞬间面如菜色,人如塑像一般僵在原地。
就在谷倩玲以为自己达到了目的,想要上前宽慰的时候,刘母忽然一弯身,拿起桌子上的水杯,动作利落地将水杯里的水泼到了谷倩玲的脸上。
谷倩玲的眼中刚刚泛起的得意之色被一杯凉水泼得瞬间消失殆尽,水珠顺着她的头发和苍白的脸颊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她惊愕地看着刘母,一时间无法理解她的反应。
“我的孙子如果有事,你的下场也不会好。”刘母发狠地盯着谷倩玲,这反应像极了母兽在保护幼崽。
“阿姨……”谷倩玲才委屈的一开口,刘母已经冲过来,扯住她的胳膊,向门口拉去,直接将她推出门去。
“你真以为什么女人都可以登堂入室?我刘家虽不是什么高门大户,也没有你这种恶毒的女人站的地。”刘母一番蔑视的冷嘲热讽后,嘭的一声关上房门。门外徒留一身狼狈,头发还在滴水的谷倩玲。
她是真的被刘母的气势给吓到了,却不知道在关上房门后,刘母挺直的身体不禁一软,勉强佝偻着走到沙发边上,人便瘫软下去。
她知道谷倩玲来的目的,所以她很清楚谷倩玲不可能拿她孙子的生死撒谎。
心底的那股子喜悦还在,这么快就成了噩耗。
谷倩玲红着眼睛盯着那扇紧闭的门,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迹,得意地笑了笑,向电梯走去。
刘义洲的车在小区停下,他没有下车。而是抬头看了看他家的窗口,那扇窗口的灯光,他这会儿看了依旧眷恋。
他转头看向楚歌,涩然地开口,“楚歌,对不起。我……”
“我先上楼了。”楚歌推开出门,下了车。她并不想接受他的道歉,因为她不会原谅他。
刘义洲懊恼地将身体靠在座椅上,拿出一根香烟点燃。烟雾很快散满整个车厢,淹没他的表情。这时,他的手机提示音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是徐征发来的微信。徐征说:等二次鉴定的结果出来,我就去法院帮你撤回离婚诉讼,好好地把所有事都告诉楚歌,就算是她暂时生气,也一定会原谅你。
刘义洲并没有因为徐征的鼓励而宽心,依旧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在楚歌这一席话前,他与徐征一样,认为他和楚歌之间有的是需要解释清楚的误会。直到这会儿他才真正体会“覆水难收”四个字。
谷倩玲的胸前湿了一大片,裙子黏贴在胸口上,隐约可见里边的胸衣。她看着电梯上跳动的数字,心情烦躁而慌乱,在心里祈祷着电梯里没有人。以免自己在别人的窥视下,更加狼狈不堪。
叮的一声,电梯的门缓缓开启,老天似乎并没有听到她的祈祷,一道人影随着电梯门的开启映入她的眼中。
电梯里的楚歌将将抬步,却因电梯外的谷倩玲,又生生顿住了脚步。
楚歌的迟疑也只是一瞬间,她走出电梯,打量了谷倩玲一眼,很显然她是去过她家了。
不用猜,她这一身的水也肯定是婆婆所赐。
楚歌在谷倩玲的面前停下脚步,问:“你跟我婆婆说了什么?”
她不担心自己回去要面对怎样的指责,她只是不忍心婆婆那么大年纪了还跟着两个孩子伤心难过。即便刘义洲背叛了她,毕竟这不是那个曾经爱护过她的老人的错。
谷倩玲微一昂头,示威地问:“怕了?”
楚歌轻皱了下眉心,不想再跟这个失去理智的女人多言,越过她向自己家的门口走去。
谷倩玲愤恨地瞪了她的背影一眼,走进电梯。
楚歌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客厅里的灯很明亮,气氛却压抑得让人心慌。刘母就坐在沙发上愣神,仿佛没有看到她。
她动作小心地换了鞋,放轻脚步走了过去。
“妈……”她这一声叫得有些艰涩。
刘母似被她的声音惊醒,连忙起身,说:“回来了,妈去给你热饭。”
“妈!”楚歌拉住她,“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谷倩玲了。”
婆婆的表情告诉她,一切都瞒不住了,那就说清楚吧。
刘母叹了声,拍了拍楚歌握在她胳膊上的手,拉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楚歌,妈替义洲给你赔个不是。”刘母的眼底泛起了泪花,自责地说:“是妈没教育好他。”
“妈……”楚歌的声音微哽,红了眼圈。
“孩子,让你受委屈了。”刘母握紧她的手,“等他回来,妈一定给你出气。只要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楚歌哽咽得无法出声,只是不停地摇头。她和刘义洲之间走到了这一步,已是覆水难收。但她仍旧感谢婆婆的爱护。
“妈,我和义洲不可能了。”楚歌艰难地说。
刘母忽然从沙发上起身,跪了下去,“楚歌,就当妈求你,再给义洲一次机会。”
刘母的反应让楚歌有些措手不及。她顾不得心里的疼,赶紧起身去扶她。
“妈,您先起来。”
“楚歌啊!”刘母的眼泪大颗大颗地从堆积着细细密密皱纹的眼角滚落,“你嫁进刘家的那天,妈就承诺过,一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可是,妈没有做到,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妈对不起你。”
楚歌扶不起她,只能跟着跪了下去,“妈,不是您的错。”
“是妈老糊涂了。要不是那个妖精找上门,我还不知道你和义洲之间怎么了。”刘母满眼的愧疚之色,抬起布满老茧的手去擦楚歌脸上的泪,“你答应妈,再给义洲一次机会。等他回来,妈一定帮你好好地教训他。”
“妈……”楚歌拉下她的手,强忍住哽咽,“我和义洲已经不可能了。有些事情,您可能还不知道。”
她想,刘母大概还不知道她打掉孩子的事情。如若不然,刘义洲都接受不了的事情,她是如何接受的?
“妈知道。快起来,地上凉。”刘母扶着楚歌起身,在沙发边坐下,“妈不会只听别人说,妈更相信你。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事。”
“妈……”楚歌刚刚止住的泪水,又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
“傻孩子。”刘母将她抱入怀中,“你这个时候不能哭,哭多了伤身。”
“妈……”楚歌咬了咬唇,记忆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她缓缓道,“因为撞车,我那天大出血。医生说,孩子生下来也会有缺陷,严重的话会畸形。我没有办法,我才会决定流掉孩子。”
她本以为,她一辈子都不会再解释这件事情。可是,刘母的信任,让她不忍心伤了这位老人的心。
刘母泛着泪光的双眼溢出疼惜和自责,却在扫到门口的时候,变成了愤怒。楚歌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是刘义洲。他正站在门口,泛红的双眼中含着泪花。
刘母起身冲过去,一巴掌毫不留情地甩在刘义洲的脸上。刘母这一下用了十足的力气,打得刘义洲高大的身体一晃,撞到身后的门板上。他斜倚在门板上,含泪的双眼正歉疚地看着楚歌。
“浑小子,你真让妈失望。”刘母责难的声音微微颤抖着,满脸泪水。
“我这辈子唯一认的儿媳妇就楚歌一人,如果你哄不好楚歌,你就给我打一辈子光棍。”刘母怒视着他,“那个女人找上门来,就是想弄散你的家,你可不能犯糊涂上当啊!”
刘义洲的脸色蓦地沉了,问:“谷倩玲来了?”
他们住的房子有两部电梯,他用另一部电梯上楼时,谷倩玲正好用另一部电梯下楼,也就错开了。
“义洲啊!”刘母软了声音,用力拍打着他的肩膀,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爱,“只要夫妻同心,没有迈步过去的砍。”
刘母叹了声,换鞋出了门。
只剩下刘义洲和楚歌的客厅里,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
“你什么时候出的车祸?”刘义洲艰难地问。其实他已经猜到答案,却还是忍不住问。
楚歌迎视着他愧疚的视线,冷声说:“看到你和谷倩玲在别墅里那天。”
刘义洲的身体微微颤抖,激动地问:“你是因为失去孩子,所以不再开车吗?”
“嗯。”楚歌的喉咙里滚出一个痛苦的音,“失去孩子后,我的身体和心情受到重创,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我吃海鲜会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楚歌含泪瞪着刘义洲,嘴唇颤抖着,“刘义洲,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告诉你吗?”
刘义洲不肯接话,因为他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就想,曾根深蒂固被我们爱着的,喜欢的,有一天你就是得放弃。即便你想勉强,你的身体也会排斥。”楚歌站起身,刘义洲下意识拉住楚歌的手臂,站起身。
“楚歌……我……”刘义洲哽咽着,已经泪流满面。
楚歌用力甩开刘义洲的手,冷漠地看着他,“刘义洲,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内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夫妻关系快点结束。”
楚歌实在不想与刘义洲共处一室,索性直接摔门离开。
刘义洲跌坐在沙发上,将脸埋在手掌里,泪水顺着指缝流出。这个向来流血不流泪的男人,这一刻不顾形象,哭得宽厚的背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