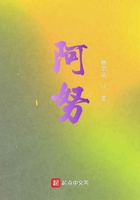然而我错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岩洞里空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人。
扫视过周围,心底寒意阵阵,他们是带着枪走的。赶紧摸了摸脑袋下面,幸好我的枪还在。
干粮和子弹少了很多,留下的倒也不少。这算什么?一种略带怜悯的抛弃?想丢下我,但又不好意思做得太绝,所以留些弹药和粮食?又或者是因为我身上带伤,行动不便,他们又碰上了十万火急的事情?
留个字条也行啊!哦,在他们眼里,我认不得字。那为什么不画个图?莫非我还算不上他们之中真正的成员?尽管我本质上就不是,可我加入之后的所作所为绝对超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换句话说,要是没有我,他们多半已是腐尸了。
吃过一些东西,在恼怒不安的刺激下,身体淡忘了疼痛,我在外边张望过一阵,决定暂且不着急,等等再说。
时间很慢,很难安然睡去,我发现自己的神经突然就回到了孤身闯荡时候的敏感,对任何声响都留心去分辨。不能安宁的躺着,一刻不停的翻来覆去,耳后传来一丝凉意,摸过来一看:是女老大的玉镯,用一根丝线绑了个精致的蝴蝶结。
握在手里,思绪又乱了。走进部队之后,蝴蝶结这样的玩意是全然接触不到的,那是一片完全属于男人的天地,假若谁能编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等着他的绝对是糟糕的嘲笑。但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有一段关于蝴蝶结零碎记忆的。
那还是中学时候,毕业前夕,班上组织了一次郊游,去的是道家圣地齐云山。那趟外出,留给我的印象有两个:第一个是有关于梁山一百单八将的纠结,因为方腊。齐云山里藏着一个方腊寨,由很窄很陡的石阶举在高高的山顶。这让我想起梁山好汉的悲催来,他们奉命前来与方腊对决,结果是血染山野,酿成了一杯让人唏嘘不已的苦酒。我在那个山顶曾反复去想:假如他们不做敌人,而是联合起来,那朝廷还能怎样?只是历史不容假设,悲剧好歹算是给后人的教训。可后人真会去吸取教训?我看很难,希特勒的狂想覆灭了,小小的越南又如此骚动了起来,可不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二个就该轮到蝴蝶结了,有个平日里极少接触的女生在方腊寨的一棵小松树上系了个蝴蝶结,然后拉我过去看,当时感觉很无聊,反应自然平淡,结果下山的时候,不经意发现那女生始终是一副落寞的表情。我才知道自己愚笨了一回,既然很快就要离开学校各奔东西了,又为何不留点余地,让人少一点不开心回忆呢?
人哪,最好不要忽视别人的善意,若不然,说不定哪个无聊的间隙回想起来,定然逃不掉隐隐的悔意。
真是扯淡!眼下的残酷里,我竟然还会想起这种琐碎无聊的事。但手里的玉镯依旧带给我很多纠结。这究竟是什么用意?抛弃之后的安抚?还是意味着他们这次外出极其危险,留下这个算是纪念?
天色如同我的情绪,阴暗不仅没有随着中午将近逐步散开,反而愈发浓密,山风更凉了,也更急了。而后我就在洞口的地面上看见了渗开来的雨滴,下雨了,这愁人的秋雨。
我曾听同学说过一段故事:有一个匈牙利人创作了一首叫做《黑色星期天》的曲子,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神秘自杀事件,最后真相大白:原来凶手就是这曲子。原本我只是把这说法当做一种人们基于对神秘事件的渴求而刻意装饰过的故事,可现在,我开始慢慢琢磨出一点道理来。
人的情绪并非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怎么说呢?你不经意的出门,碰上一场婚礼和撞上一场葬礼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尽管都与你毫不相干,但你的情绪却不会这么认为,它总会去凑个热闹,带给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复杂感受。
我坐到洞口,看着冰凉的雨点粉碎在石头、枝叶上,“滴滴答答”的如同一种神秘的述说。我在这种讲述里忘却了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心头泛起一阵一阵的酸楚:大姐在哪里?老头子和阿姨的尸体有没有被埋起来?雨点会打在他们身上吗?我留下的那么多的血污是否正在雨里一点点的化解?……。
雷声开始在山谷里翻滚,一个粗放的声音远远传来,像是在着急的嘶嚎,将我从无尽的纠结里拉扯了回来。
沿着山坡狂奔而来的是粗矮的家伙。
果然出事了!
与人沟通是需要技巧的,与一个“聋哑人”沟通是矮粗的家伙完全不能胜任的,他反反复复的比划很久,我只看见他着急得抓耳挠腮的模样,完全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终于失望了,木然的跌坐在雨地里,随后想起了画画。一直在地上画了篇幅超过几平米的图形,我才明白:大姐和瘦长的家伙被人抓了。
我能怎么办?从逻辑的角度,我根本不应当涉足这种危险。可手里还握着人家的“礼物”。短暂的思考之后,我开始准备行李:枪、子弹、手榴弹,一点干粮。
矮粗的家伙顾不得吃点东西,就火急火燎的在洞口催促着我,似乎我的出手相助是义不容辞的。这个简单的家伙,居然丝毫不担心我随时一枪解决了他,然后安然的离开。但也正是他的简单,增加了我下手的难度。
目的地是一个镇子边缘的加工厂,又像是半废弃了的仓库,胡乱堆放着一些锈蚀了的机器零件,木柱子撑起高高的屋梁,遍地灰尘,角落里全是蜘蛛网。
没有人的痕迹,我们是直接走进来的。时间恰好是午后,已经是我们离开山洞的第二天了。
粗矮的家伙从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里揪出来一个佝偻的老头子,我明白这是在打探消息,这样的老人能够清楚当地的很多事情,但自身并不是危险所在。
我们很快离开了,沿着镇子的边缘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又是一阵赶路,雨一直未停,淋淋沥沥的装饰着一切,冷冷清清的部署出一个阴冷的天地。渐渐地,我从矮粗家伙的动作上判断出:目标近了。
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隐藏在山脚的树荫下,矮粗的家伙这时候已经将手里的枪端了起来,一步一步靠近过去。
因为不停的雨,外面空无一人。我还来不及跟上,他就踹开了屋门。我赶紧助跑几步,跳了进去。
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危险,场面已经被矮粗的家伙控制住了,屋里空荡荡的很少摆设,一张桌子上摆着几个空酒瓶和满桌的狼藉。靠墙的床铺毫无遮拦,上面半坐着两个家伙,还算年轻,但都是瘦骨嶙峋的那种,露出来的上半身完全光着,在枪口下急促的喘着气,肋骨一顿一顿的显露出来,能瘦成这样,真是够努力的。
为了排除潜在的危险,我向前一步抓住被子的一角,扯落在地上。露出来的景象让我们大吃一惊:根本不是两个人,是四个人,躲在被窝里的是两个光溜溜的女人。
真是会打发这秋雨造成的无聊。更让我叹服的是:这种事情居然也能共享,真是难以想象,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在同一张床上。
矮粗的家伙开始问话,其中一个略带犹豫,但终究惧怕眼前的枪口,很配合的回答着。两个女人蜷着身子,恐惧得忘却了掩住羞耻之处,只顾蜷成一团,瑟瑟发抖。
矮粗的家伙收回了枪,掉头就往门外走,我正要跟着离开,眼光瞅见两支步枪靠在墙边,遂走过去拿了起来,走到门外,远远的丢在草丛里去了。这种老步枪对我没有用处,只是不愿意转身离开之后,被人从背后瞄着开枪。
转过一个山坡,矮粗的家伙跌坐在地上,神情沮丧。
我并不着急发问,等他回过神来,自然会告诉我的。过程依然艰难,不过我总算明白了:女老大他们开始是被刚才那两个家伙抓了,但现在交给了别人。在他的描述里,抓他们的并非只有刚才那两个,还有其他的人。
会是谁?不用猜,我就怀疑是那作为组织头目的丑陋汉子。问了很久,矮粗的家伙才证实了我的判断。
在他的详细描述里,我才明白事情的经过。原来上次他们出去交易枪支,带回的消息是和女老大关系密切的一个人被当地的混混给抓了,所以他们等不及我的伤好就出发前去解救,结果正中圈套,被一并抓了,矮粗的家伙因为被安排做接应才得以逃脱。
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按照他的性格,前面出了事,怎么会理智到回来搬救兵?应该冲上去厮杀才对啊。
我大致清楚了事情脉络,也开始从逻辑的层面理解了这看似复杂的故事。那丑陋汉子所掌控的组织为了清除我们几个人,结果除了间接灭掉了那个猥琐的瘦矮家伙之外一无所获。前后两次加起来还损失了四十多人,丢了很多枪。这无疑给他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这种损耗对于一个黑帮组织而言是极其沉重的,四十多人可是一个加强排了。再庞大的组织也不可能忽视这样的力量。元气大伤之后,他们采用绑架亲属的方式自然是合乎逻辑的。
事情很麻烦,杀人容易,救人可就难了。
但已经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跟着矮粗的家伙重新赶路。半夜时分,我们来到了那处砖瓦房子,养马的老妇人很惊恐的看着我们,显然知道出事了,我们都没有搭理她,牵出四匹马来,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