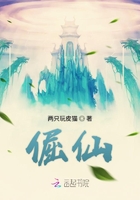白星回头看了看金洋,她不明白上课前金洋的那番眼神是想给她说什么。
“黑板上的寻物启事是为她写的,是金洋丢了本子,难,难不成她怀疑是我偷的???”白星突然想到了这一层层的关系。
“她为什么怀疑我呢?”
“我一直在教室。”
“不对呀,她怎么就确定我一直在教室,万一我没去体育课是干别的事了呢?这也不能推断东西就是我偷的了呀?”
“门?”
“门锁了!”
白星的心突然紧了一下,然后又紧了一下,她忽然觉得浑身发热,额头上紧张的渗出了细汗。她摸了摸额头,果真有汗,她使劲擦了擦。
“不是我干的,我为什么要害怕??”莫名其妙,但她还是觉得不踏实。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助感还有莫名的恐慌感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她突然就想到了“陷害”这个词。
不是她胡思乱想,作为一个思绪本身就敏感的人,这种想法并不过分,也不难理解。
她不是不相信同学,因为她难以相信人心。
自从上小学的时候被一个很信任的女生骗了之后,她就再也很难完全信任一个人了。在很小的时候,她开始相信书上的那句话了:对一个人有所保留不是一件坏事。现实证实了它的正确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让你会少受点痛的伤害。
白星低下头。
深深的无力,如此复杂。
还好,金洋并没有在上前来找她。她庆幸只是一场误会,也许真的是自己多心了。
窗外的阳光正好,万里无云,一片晴空。
操场上打羽毛球的,打篮球的,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被这群活跃的少年们演练的阳光充实。让年老的人都忍不住去尝试一下篮球的手感,投篮的快感还有羽毛球飞驰在空中美丽的划线。
“年轻真好啊。”年老的教师匆匆走过操场,恋恋不舍的投出羡慕的眼神。
每个人看到了宏观的世界,却不曾有人在意角落里那一桩桩,一件件细如毛丝的小事。你叹息的那一瞬,一只小蚂蚁也许已经在校园草丛边上的洞穴里生下了她的小宝宝。
还有,一个安静的身影,躲在树荫下偷偷哭泣。连哭泣都那样可怜,连哭都不敢大声。
雍怡然蹲在卫生间拐角的树荫下,抱着膝盖,哭花了妆。她怕别人看见,不敢出一点动静。只有一点抽泣,也憋了回去。
她可以无助,但不可以在外人面前无助,她可以软弱,但不能在别人面前软弱。
她能接受的唯一上限,只有她的骄傲了。她不剩什么了。如果连这点尊严都保不住,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在昨天和母亲离婚了。
而昨天她刚学会了弹那首叫《神话》的曲子。她最喜欢的曲子。
雍怡然不明白两个人好好的,怎么说离就离了。在他们的生命中,难道她不重要吗?不值得他们为了她去维护这个家的存在吗?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吧。
她不敢抬头,她害怕看到别的脸。那是在嘲笑她的脸,是无比丑陋的脸。
田森临悄悄走了过来,他找了她好久,终于在这里找到她了。
他不知道眼前的女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能打败这个外表刚硬的不羁女孩。他能看上她,就是这个原因吧。
“你,你没事吧?”田森临结巴,他还没哄过女孩子。
“……”弱小的肩膀紧缩在墙角,让人忍不住去保护,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田森临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不会处理这样的事,只有默默等着,等着她抬头,等着她开口。
“滚。”
“我叫你滚。”
雍怡然压低的怒吼颤颤巍巍穿过空气传到了田森临的耳膜里,刺耳,却没有引起他的怒火。
头一次,他竟然觉得不生气,头一次,他竟然觉得面子没那么重要。
不是为了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孩,只是觉得她和曾经的自己有那么一点像。
越过时光,一个过去,一个现在,你遭遇过的,我正在经历,说不上悲伤,却那么痛心。
“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田森临泛起怜爱,现在的他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我叫你滚听到没?”雍怡然猛然抬头,红肿的眼睛,黑色的颜色随着泪痕铺满这张娇柔的面容,花容失色。
她直勾勾,恶狠狠的盯着眼前的这个为了她半蹲着的人,仿佛他是造成她一切痛苦的来源。仿佛只有盯着他,拔下他身上那层皮,才能缓解她如此难受的伤痛。
蚀骨的疼,锥心的痛,有人在自己心上用银针肆意扎着洞,有人拿着千斤锤,砸在自己心口,压的自己喘不过气来。
这一切的根源,都不能说,不能对任何人说,这是耻辱,耻辱。这会让别人笑话她。她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被笑话过。
突然,一个温热的怀抱扑面而来,她跌落在一个坚实的臂膀里。
她吃了一惊。
两颗心贴的那么近。
她又吃了一惊。
长这么大,很少有人抱过她。她记得,小时候向妈妈要抱抱的时候,妈妈撇着脸对她说:“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她还不懂事。
她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