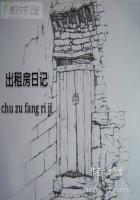他说的咬牙切齿,我听的胆颤心惊,他接着说:“我随你信不信,但是,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承受不起,我和阿墨做那事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她,阿墨临走叫我一声相公的时候,我是当她在叫我,我也只能去想想而已,是我来的晚了,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来不及,我来不及和她相伴,来不及见芝芝最后一面,来不及救我爹娘,现在,趁我还来得及,我只能这样保护着她,你懂吗?你会如何去保护一个人?你用你的刀,你的命去保护山上的兄弟,但是,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保护我爱的女人,你明白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里渗出的泪来,我从未想过,在他的心里竟然藏着这么多的东西,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的锦儿,真实里是个暴虐的人,表面上看着放荡不羁的星儿却是个内心坦荡的男儿,且不管真假,只是听他这一番话,便已然让我心惊,现在的他,已然愿在我面前承认自己的内心,让我看到他的孤独与痛苦,我一直以为,他和锦儿才是最贴心的好兄弟,那便是我看到的表相,现在,才是真相吗?
他看着我,突然邪魅地一笑道:“我与你初见时,我便是个面目可憎的坏孩子,我曾骗你进入圈套,曾骗他们陷害你,山上愿与我称兄道弟的没有谁,我不在乎,但是,我现在说的话,你信么?”
我思忖道:“你说的话,我会有法子去判断真假,但是,我既然带你回来,不指望你不骗我,对我如何忠诚不二,你们每一个人自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我只能做到让你们保住性命。上官云星,你不是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你行得正站得端便足够了,你爱着谁,便去爱,你懂道义,便是对的,你受了什么委屈,我有些并不知道,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我拿你从不见外,在这天下,我从不依靠着谁活着,我也希望,你便活出你的自在,如果你爱的人让你委屈,你便不去爱,这天下爱着你的人还不够多么?谁对你耍了手段,你当他是兄弟不计较,便是你的胸怀,若是外人,你早一刀宰了去,也不会对我讲,你跟我说,那是你在乎。
“你听着,能伤你的人,便是知道你软肋的人,在这江湖上活着,软肋越少,才越能强大,现在的我已然不够强大,因为我在乎的人太多,而你还未入江湖,很多事还来得及去选,你只这一颗心,想把谁放在这里,是你的事,谁伤你,请他出去,只放不会伤你的人,而那些不把你当兄弟的,便一笑而过,学会给自己穿一层护甲,逍遥天下时,便是爱也逍遥,恨也逍遥,做不到,便逼着自己去做到。
“我再告诉你,老子的那些男人,只是老子取乐的工具,除了你柱子哥,其他人就是这样,我当着他们的面也是这么说,我回答你的问题,你柱子哥是老子唯一的男人,没有什么偏房,以后也只他一人,老子在他之前,该玩的也玩够了,除了他,谁能伤我?而他也是不舍得伤我,你有一日也要有这样一个人,其余不能和你共生死的,都是玩乐,懂吗?”
他的目光慢慢淡然着,又坐了回去,垂着头,两手紧紧地握着泥土,我叹一声道:“别人的女人与你无关,从心里割一刀是会痛,却是对你有益的,你不看不听不想,便不痛,有些事总是要经历的,你这孩子要面对的太多了,便是在这山上也讨不到个好人脉,更别说广结天下善缘,女人嘛,不是真心对你的,或者不能让你动心的,玩玩便好,何必认真。”
他看我一眼道:“你不也是女人?”
我横他一眼:“在我这里说法就变了,男人嘛,不是真心对我好,不,就算是真心对我好的,入不得老子法眼的,或者是不能和老子……哎,反正,你也看到了,老子在生死关头,能出手相救的男人也不少,你呢?何时,你有什么不测,便有江湖上黑道白道各种女人涌来护你,才算你有本事,你明明把他们都睡了,他们还要替你换命,上官云星,你还要好好修炼呢。”
我得意地说着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土,他将腿一盘道:“睡女人谁不会。”
我嘿嘿一乐凑到他耳边道:“你会?会什么?光是这事,你要学的都多了去了,这天下间的事,没那么简单,有空多跟你二当家学学,这里面的学问也是博大精深,懂吗?”我用手背拍了拍他的手臂坏笑着。
他嫌弃地看我一眼道:“看你那色迷迷的样子,今晚又不会放过柱子哥了,你快去吧,我要和黑虎说会话。”
我伸手一捏他的下巴凑上去一些道:“小子,你现在这小模样倒是会让那些姑娘们发了花痴,你不多学些,小心让一些小妖精们把骨头都嚼了,要不,老子也教教你?”
他一把推着我的脸把我推开道:“你快走远些,你这千年老妖,还是嚼那块木头吧,离我远远的才好。”他有些惊恐地看着我赶忙趴起来往自己的房子跑去,我嘿嘿笑着摇摇头站起身来道:“唉,还是太嫩了,这么一吓就吓的屁滚尿流,要是来真的,还不吓破了胆?”
“什么来真的?”有人突然说着自暗处走出来,吓我一跳,回头一看,却是柱子,我吁一口气,遮遮掩掩道:“没,没什么,嘿嘿。”我冲他笑了笑,又问他怎么在这里。
“那会我在房里听见你的脚步声,正去开门,却见你又后院去,以为你是又看见什么,便也跟着你,却看见星儿在那里坐着,我便去找郎中说了会子话,再出来时,见你们还在说话,却见他怎么扑到你面前去了,当时便想上去,却见你们只是说话,但已然走到树下了,又怕被你们察觉打断你教导他,便一直在此。”他对我说着。
我走上前伸手揽着他的腰仰头看着他问道:“那你都听见了?”
他看了看天道:“有些听见了有些假装没听见。”
“听见什么了?”我问他。
“听见你说,你有个唯一的男人,叫什么来着?”他还是看着天,我笑着说:“那你唯一的女人是谁?”
他低下头笑着看向我正要说话,又听一阵脚步声来路过我们身侧时说道:“回暖和的房里去快活不好吗?站在这里碍事。”我一回头,便看见星儿又跑了回来,自坟前拿起自己的一个香囊,那是祝芝芝送他的那个,转身又走了,又说一句:“柱子哥多发些力,省得她一天有力没处使。”
我正想抬脚踢他,他再一次跑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