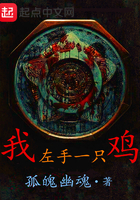“天哪,真的是你啊?”
方水苏坐在座子上看着对面精致的男人有些自愧不如,她今天连妆都没有化,只不过就是随便涂了支口红让自己看起来有气色些。
王浚站起来,有些不敢相信,他印象中的方水苏哪里会留这么长的头发,能到肩膀就已经很不错了。
“别人出国回来都是改头换面,你这跟难民逃荒有啥区别?”
骆屿梵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看来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觉得。
“别贫了,我在国外没有时间,能把课上下来已经很不错了……”方水苏有些疲累地向后瘫着,“快给我换个形象吧大设计师,我要从头开始。”
王浚有些嫌弃地捻着她的长发,“这个发型跟你艺术家的气质还蛮搭的,就别剪了吧。”没有烫染的长发,发质柔 软顺滑,让人爱不释手。
方水苏笑了笑,“哪有什么艺术家形象,我要管那么打一个公司,你认为我这样能镇得住董事会那帮老狐狸?”
“你要回来继承公司?”
骆屿梵皱了皱眉头,越发觉得事情不对。她一向不喜欢那些市场上的尔虞我诈,那些人情世故对她来说一向是繁琐的。
“那的确这样是没有气场,你等等,我仔细想一想。”
王浚把准备好的衣服全都扔到了沙发上,匆匆忙忙地一头扎进了衣帽间 看样子一时半会是出不来了。方水苏拿起其中一条香槟色长裙,有些无奈地在自己身上比划,然后放下去随口说了一句。
“她一定会喜欢这条裙子。”
那样柔 软的水流一样的女孩子,天生就跟小裙子很搭,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方水苏要做的就是把最漂亮的那条买下来带回去,送到她手里,并且轻吻她的额头。
说送给你,说我爱你。
这些已经习惯到她血液里的动作和台词让她无奈,以至于说完这句话之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默,而骆屿梵在听到她要回来继承家业之后就一直面色严肃,如果方水苏在国内并且还是在方氏财团里做总裁,他们就完全没有逃避催婚的理由。她的学业是最后的挡箭牌,如今他们都失去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你的课程学完了?”
方水苏回过神来,扬了扬下巴,“你知道的我一向是比较勤奋的那个学生,所以在回来之前我已经修完了全部的学分。”
骆屿梵赞赏地看着方水苏,后者放下了裙子,“所以才能尽快逃离那里啊……”
才能逃离那个就算是站在街口听着无聊的风声,因为身边站着的人不是喜欢的人,呼吸都变得苦难。
“她结婚了,跟一个男人。”
方水苏手指揉着无名指上的戒指印,“我们的感情熬过了磨合期之后,没有变得幸福,压力排山倒海的涌来,她逃跑了。”
她何止是逃跑,简直是落荒而逃。
她们两个人,在陌生的国度相依为命,可是远在天边的那对父母,确实用同一种方法把他们心爱的小女孩召唤回国。病床上的妇人喝了安眠药,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口吐白沫多时,整整一个夜晚的抢救她终于醒过来,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要见囡囡。
“苏苏,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她穿着米色的长裙,褶皱上有玫瑰花印记,头发黑色,瀑布一样的倾泻而下在身后,在她的手臂,肩膀,脊背。方水苏没有说话,只是躺在那里,装作睡着一样看着她,她的脊背和肩膀都在颤抖,她一定在掉眼泪。
心疼年事已高的父母为她的一次任性埋单。
又在自责于为什么直到现在她能做的就只有一次又一次的退缩,后悔,推翻重来。
方水苏伸手想要去摸她的头发,但是在触碰到之前她就已经起身,步履匆匆,她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方水苏感到恐惧遍布全身,可是这个结局她很早就已经知道,迟早有一天。
她怎么得到她的,就会怎么失去她。
没有人知道,当她割开手腕的时候,血流不止让她多么害怕,直到开始眩晕开始眼神涣散,觉得天堂之门已经近在咫尺的时候门被狠狠地踹开,她听到母亲歇斯底里地痛哭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你们他妈的终于来了。
仅有一次的生命突然开始消逝的时候,态度强硬的人会动摇。
方水苏站起身,手按住她的行李箱,笑着问,“你要去哪?”
她没有抬头,细碎的刘海盖住了眼睛,方水苏伸手拨开她的头发看到了那双眼睛,水蜜 桃一样的红肿,轻轻地将她抱在怀里,听她的哽咽变成啜泣,随后嚎啕大哭,像个孩子。
“不要哭啊,你会回来的,不是吗?”
方水苏不知道,她的脸上早就是泪流满面,她的眼睛也红肿的像两颗水蜜 桃,还有她的声音,嘶哑又颤抖,像是大风中一个破风箱。
“你什么都不懂。”
她突然推开她,大声地,疯了一样。
方水苏就站在那看她哭了又笑,整个人像极了她之前演舞台剧一样的忘我。
“你走吧。”
激烈的言语之间的对峙结果就是她很容易便败下阵来。
她最不能看到的事情就是别人因为她的存在而感到痛哭,这让她心情沉重,忘记生活本能。
很显然,这三个字对于现在的局势来说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只是这三个字说出来之后,方水苏捂着胸口趁自己没有反悔前,几乎是快速吼出来。
她楞在原地,行李箱呆呆地站在她身边,和她一样像是遭受了晴天霹雳。
“你说什么?”
方水苏一句话不会说第二遍,但是今天为了她,她又一字一句地说。
“你走吧,不要回来了,找一个好男人结婚,让你的父母放心。”
话没有说完,脚边就已经碎了一个玻璃杯子,她最喜欢的那一个,平常拿来喝果茶。
“走吧,不要闹小孩子脾气,谁都没有办法了。”
方水苏顿了顿,看着她把家里的东西砸个遍,最后才说。“没关系,我可以再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