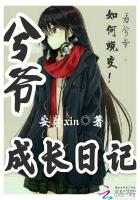想来当初壮志踌躇未尽,也是因着他这番爱惜才华而甘愿为之肝脑涂地,但在看清他的真面目之后,智真只觉自己当初是瞎了眼。
不论心下如何想他的不是,面上智真也一如往常地不骄不躁,同胡度一般甚至更甚地恭敬回话。做戏做全套,想起他的夫人就差那么一点就真的无力回天,智真眼里也泛起了湿润。
胡度见他这般,也不忍地上前两步拍了拍他的肩头,安抚道:“可你这般没有头绪地就遣人去寻医问道的,万一遇上了江湖骗子,夫人岂不是更不好了?想来你遣人去寻而非亲自去也是瞒着夫人的,万一下人对夫人的病情没那么熟悉,大夫以为自己能治那病,去了又发现治不了,岂不又是空欢喜一场?”
智真听出他的未尽之意:“大人的意思是?”
胡度宽厚地笑了笑:“左右廖御医无事,家中也还有其他大夫在,廖御医又更熟悉夫人的病情,让他与你那寻医问道的下人同行吧,也能省去许多麻烦。”
智真面露惶恐:“这如何使得!这些年拙荆已经够给廖御医添麻烦了,如今还有叨扰他忙碌奔波,这……恐怕不妥啊!”
胡度宽慰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当然此事老夫会过问廖御医的想法再做决定,但想来他也会很乐意为夫人出一份力的。毕竟也是好些年头的交情,老夫也看得出来廖御医也是很担心夫人的身体状况,何况他可是老圣手了,他都治不好的病,想来是想与人多交流交流的。”
“这样……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智真俯身施礼道谢,却被胡度搀扶住。
“应当的,没道理你替老夫做了这许多事,你家中出了事,老夫便全然不管不顾的。”胡度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智真知机,起身施礼告退:“在下就不打扰大人了,先行告退。”
“先生慢走,老夫让老仆送送先生。”胡度抬手做请。
智真出了节度使府,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但细一想又有些忧心,他命人做出寻医问道的姿态已有一段时日了,胡度到今日才察觉此事,想来是在那之前有旁的事绊住了他,此事引去了他的所有注意力,以至于眼下才发现他这头的不对劲之处。
虽说完成了柳玉竹给的交代,但到底不知道是否误了事。将来他夫人的解毒可全依仗着柳玉竹那头的人,即便俞文延一再强调他夫人全然无辜,必会好好照料,但提个醒这样的小事还是做得的。
俞文延隔三差五地才会来一趟智府,不巧的是里俞文延再到智府还有几天,智真想着此事不好耽误了,就让下人跑了一趟,到约好的联络点去递了个信。
收到信的柳玉竹确实很担心胡度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但同时也很感谢智真愿意递这个信,即便不递这个消息来,也没人知道,对智真这样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也多了些好感。
于是收到信的柳玉竹又让吕博带着人多观察了几天,节度使府后院派人去弄的小动静还是照常做着,但节度使府的侍卫已经懒怠去查看了,反正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小动静,那么紧张反倒累得慌,让吕博去问了在节度使府后院弄出动静的人,却也没看出什么旁的不同来。
不怪智真给的消息太模糊,毕竟这消息也是他自己揣摩出来的,自己这头小心些倒是无妨,左右眼下只等赵子易点头应下就是了。
在外搜寻猎豹行踪的施韵舟反倒更容易接触到吕博的人,左右都是夜间搜寻,他们扮作类似匪贼的模样接近自己倒也不算可疑。
“近来她那边如何了?”
来者也知道这个“她”指的是谁:“少夫人那头一切顺利,眼下就等着赵家的应下了,虽说赵家很大可能会答应,但事情还没定下来,少夫人难免有些忧心,近日夜间睡得不太好。”
施韵舟垂眼思索片刻,取下藏在衣领里的玉环坠子,递给吕博的手下:“去回了她,让她不必过分忧思,即便赵家的不允,总是有其他法子。也不怕叫他们告发了,他们知道那个宝贝嫡长孙的事捏在我们手里,总会怕我们不管不顾泄露出去,到时他们也要吃挂落的。”
手下收下玉环坠子点头应是,又接着道:“那猎豹还在范围之内,有些偏离原来的位置了,但并没跑出去太远。”
施韵舟粗略盘算了一下,往外搜的这一圈会粗略些,没搜到人还说得过去,但回来这圈就得将猎豹抓回去了:“让她注意点时间,也就剩四五天时日了。”
手下应下了,见施韵舟没有旁的事吩咐,就径自退下了。
捏着玉环的柳玉竹静默着听完吕博的回禀,瞥了他一眼:“敢情你们还当起了他的耳报神了不成。”
吕博知她这句话并无怪罪的意思,只低头行礼:“施小将军也是关心您的身体。”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让人往赵府那里催促一下。”柳玉竹剐了一眼边上满面促狭的秋离,“能有这么一出,一准是你的主意。”
秋离无所畏惧地朝她吐了吐舌头:“谁叫小姐不听我的,我当然得找个镇得住小姐的咯!”
柳玉竹撇嘴,斜着眼看她,突然想起什么,调侃道:“话又说回来,你和墨蓝,最近走得很近嘛?若是想要婚配,说一声便是,我还是很乐见其成的。”
秋离的促狭凝在面上,霎时涨得通红:“这才哪跟哪呢就什么婚配的……小姐你一个未出阁的闺女家,说这话也不知道害臊的!”
柳玉竹坦然地耸了耸肩:“有什么可害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是最正常不过的吗?再说了,又没叫你立时嫁与他就入了洞房,你怎么就这么紧张呢?”
听出了她的调侃,秋离别开脸不爱搭她的话茬:“总之,小姐你今天不许再独自对月坐等天明去!别打量着我不替你守夜就什么也不知道,今晚你要再不好生休息,我就能再去少爷那里告你一状!”
“是是是,我知道了……”柳玉竹摆手讨饶,看来今晚再怎么愁也得闭目养神会,别到时候连施韵舟都劳师动众偷跑回来就为了盯着她睡觉,以施韵舟的性子她简直猜得到他真干得出这种事来。
“最好是真知道了!”秋离嗔瞪了她一眼,搀着她起身就要往里屋去,“看时辰也差不多了,该回屋休息去了。”
见她一副要守着自己的样子,柳玉竹都有些怕了她了:“行行行我知道了,我还没老到需要人搀扶呢,你也回去休息吧,我保证回去了立马就去睡,睡不着我也会去闭目养神的。”
自她被柳玉竹要来跟着她之后就从来没有让她守过夜,今天必然也会是这样,秋离自然是知道她不会让自己守夜。
一个是她自己不习惯,再一个她也不愿意因为她的方便就让秋离睡得不踏实,屏风里的矮榻虽然能让下人躺下歇息,但确实算不得舒坦,至少不如下人们的炕头舒坦,那矮榻小得都不够人翻身的。
柳玉竹向来体恤下人,尤其是对数次与她出生入死的秋离,因此自然是不肯让她在那矮榻上守夜的,秋离就是吃定了这一点,催着柳玉竹赶紧上床歇息一会。
虽说于下人而言,秋离此举无疑是逾矩了,在主子面前拿乔,不被主子反手卖给人贩子就不错了,更别说对主子威逼利诱的。放在仍在施韵舟身边伺候时,秋离断然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许是与柳玉竹相处久了,久而久之也有些懂得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什么,因此两人与其说是主仆,不如说是朋友更贴切些。
秋离的良苦用心,柳玉竹当然知道,所以即便秋离作势要怒,她也只嬉嬉笑笑地哄着让秋离消消气,兀自回屋歇息去了。
柳玉竹安寝时从不点灯,一个是耗油耗烛火,再一个也是觉得太亮了怕睡不着,再说数次夜间遇袭,也让柳玉竹实在不愿意夜里点着烛火,还让人能大喇喇地看到自己具体在哪,方便人来害自己不成?
因此,秋离替她熄了满屋的烛火便退了出去,柳玉竹则撑在窗边看了会夜色。
还有五天啊,只待赵府那里回了准信,这边便早些发动好了。
过去的一年里,她习惯了靠自己靠秋离唯独不靠男人过活的方式,甚至还觉得施韵舟真要靠自己的话,也不是靠不住的,却不想一年不见,施韵舟也愈发可靠起来。
在她仍惴惴不安的时候就利索地罗列出一整套的计划,并在日益熟悉局势之后不断推进着全盘的局势,在她忧心得夜不能寐时仍在稳健地做着他该做的事,甚至能腾出空闲的心思主动关心她的情况,想来也是他那头进展顺利吧。
指尖轻抚着玉环坠子,实在没什么地方好放置它,柳玉竹想到了之前的香囊袋子,便将坠子放了进去,又想起俞文延的鼻子很是灵敏,尤其对药草,有机会倒是该叫他看看这香丸都有些什么药材。
柳玉竹以为今夜又该苦眠,许是那安神的香丸起了功效,难得好眠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