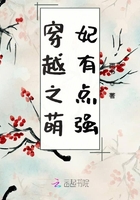楚文珏看向铜镜中自己脸上那一圈红红的牙印,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嘶…这丫头怎么这么狠啊…”他苦不迭地放下那面铜镜,皱眉道。
她莫非是属疯狗的?咬哪儿不行,还偏偏是他这张俊脸。
他房里大丫鬟青见端上来膏药等给他处理脸上伤口的用品,“世子,请上药。”
楚文珏打开药罐子,咬着牙给伤处涂抹一番。这膏是济方堂的,燕京城最好的药铺,用上后愈合快,还保他的脸不留疤。
可一旦要是留了疤,毁了面容,他一定拎着楚婳的领子丢出府送进荒山野地喂狼。
到时候她怎么哭着求他,他也不会饶命…
除非…
…
五日后。
春寒料峭,晨光熹微。
展渊正要出宫,路上却与从乾明殿回来的展修御打个照面。
两行人,都住了脚步。
展修御看他衣冠整齐,是要外出的意思。眼含玩蔑,他盯着他那张柔美的面:“正是倒春寒的时候,二弟这是要去哪儿啊?”
展渊已淡笑迎上他熟悉的目光,语气清和:“皇兄怎么开始关心这个了?”
“不关心怎么行?二弟你身子柔弱,不知道哪天就死了,到时候父皇岂不是要怪本宫这个兄长没尽心。”
展渊垂眸凝着石板缝中仍躲着丝余雪,在苟延残喘。
展修御怎么会不尽心?
他可是要尽全心地除去自己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的。
展渊笑着点点头,迈步前行而未顾。他不去看他是怎样挑衅,不再听他冷冰的客套,不管他被自己忽视后是怎样一张讥讽燃怒的面孔。
此刻他只怕耽延了他的事,误了见她的时间。
展修御被他冷落一番,阴着脸,立在原处好一会,拂袖而离,对身后的人道:“去找人跟着展渊,看看他到底去哪。”
而展渊也料到他会如此,便教苏别异驾着一车带几个随从去昭平庙,自己则等展修御派去查的人被障眼法迷惑跟着苏别异走后,再带好几个人上了路。
他已除了锦央宫里大半的展霄的狗,换成干净的一批,可以忠心为自己做事。
这样他行动也更方便,不怕背后有人乱嚼舌头,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今日便要是去荣兴侯府和楚震云把楚婳的事放在明面上来说说。
马车走街穿巷,车辘轧轧,沾染声声喧闹。
停在荣兴侯府。
当门口小厮报给楚震云说二皇子正在门外时,楚震云登时惊得起身抛下案牍,暗道事已不妙。
沉忖一时,只得让人打开大门,恭迎皇子殿下。
他也易服整发,快步去迎接。
两人见过面后打好了招呼,移步来在荣兴侯府的季安正厅。
展渊一勾手指,随从把一个蒙面的人摘了斗笠推上前。
“楚大人,此人你可面熟?”
楚震云看向那人的脸,一刹间瞪大双眼,拿着茶盏的手已有不稳。
是刘德。
展渊将他的表情神态尽收眼底,笑了笑,他不想和楚震云周旋太长时间,直截了当:“不瞒楚大人,令嫒眼疾一事,本宫早已知晓。”
楚震云一滞,沉默着低下头喝茶。
刘德见到楚震云也是吃惊,但想起侯爷之前嘱咐自己的话,只颔首静立。
“本宫一向好奇,因此也派人查了查,能查到的都查出来了,可唯独有一事不明白。”
楚震云这才抬眼。
“殿下…您想问什么?”
“楚婳的眼疾,至于让楚大人将人禁足于府中、隔离外世?”他其实对宫宴那事,内心还有些不舒服,不过知道是赖不在她头上的。“在本宫看来,她的一双眼,能看得清楚,只是颜色异于常人罢了。”
楚震云未想到他连这些都知道,这么说来展渊定是已深入调查一番,且之前也看过楚婳的脸的。
“…殿下,正因为小女的眼睛异于寻常,臣担心会招致祸乱,才很少让她出府见人。”
“是这样…那为何又匆忙将人从山上接回燕京?”
他目光如炬,开口犀利地问。
楚震云方才已猜到他要问这事,叹了口气,决意要把事情大概和他说一说。
本来这事也不牵扯什么,只关系到他们家内部,并不涉及政治等敏感领域,和他说个一些也不碍什么。
楚震云倒觉得,若真以谎话诳了这二皇子,敷衍过去,恐怕依他的性子,咬住不放,查出事有蹊跷,情况将变得更棘手。
于是他先让一旁杂役等下人出去,展渊会意,也让随从跟着走出,屋内留下他们二人。
楚震云沉吟片刻,最终正式地把有关楚婳的事缓缓道来。
他讲了他是如何捡到她,并简单说了她对楚文姌的意义,关于道士算命破劫的事他只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并未细讲。
他讲这些,也是希望展渊能明白,这是他们的家事,不是他该掺和进来、也没有必要掺和的。
“楚婳会替楚文姌受了那劫数?她会怎样?”
展渊已褪了和气,沉声问。
“这…臣也不清楚,道士只说是命劫。”楚震云在此处有意模糊处理他的问题,他怕展渊对楚婳有什么打算。
命劫。
看来,她的下场,很可能会是魂归九泉。
一时间,他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滋味,五味杂陈搅得他心口燥乱。
默了半晌。
只微微点点头,“楚大人,本宫有些东西要当面交与她。”
楚震云一惊,他有什么东西要给楚婳的?
但自知过多询问难免惹得他不快,何况他现在面已收了笑而露几分淡漠。
楚震云便传唤来下人:“把二小姐传来。”
下人便奔去楚婳的院子。
半柱香时间,楚婳一脸懵然地进了正厅。楚震云起身和她说:“婳婳,二殿下单独找你有些事,放心,爹爹在外等候。”
楚婳望望展渊,又看了一眼楚震云离去的背影。
她上前一步,作揖:“参见二殿下。”
展渊朝她招招手:“过来。”
“本宫之前答应你的东西带来了,还有你在函北留下的。”
随从把几个包袱呈递上来,展渊拿在手里,又转交给她。楚婳抱着装有几个布老虎的包袱,又看他把一包眼熟的包袱放在她眼前。
这正是她落在函北的。
顾不得想他是如何得到的,只面上一喜:“谢二殿下!”
展渊起身近她一步,从袖里拿出那串手链,套进她素白的腕子。
“本宫近来会很忙,因而不会再多来见你,你自己便好好地吃饭习字。”
他极力要抽身而出,他已预见她给他布下沼泽深渊,他怕沉陷下去便再不得脱身。
他若选择沉沦,则要注定面对与她阴阳两隔,承受浩劫,忍耐痛苦。
他是个精明的人,工于算计,趋利避害,是活着的信条。十七年的风霜寒雪告诉他,耽于女色酒臭,则于亡身送命不久矣。
又有什么错,他不是豪情万丈的霸王,也做不了谁的盖世英雄。
因而要开始尽力疏远她,逐渐成为两个不相干的过客,这样,于他于她,都是好事。
楚婳欣喜地点点头:“婳婳知道了!谢二殿下!”她复而看了看失而复得的手链,对展渊突然的开明有些惊讶。
展渊看着她那双纱下的眼,隐隐的蓝仍是那样灵动有神。
便到此为止吧。
他点点头,收回目光:“本宫回去了。”便一路不顾地大步走出,消失在视线中。
楚婳看着他不似寻常那样,像是有些丢了魂儿的,刚刚看她的眼神也复杂得难以揣测。
他这是怎么了?
好像是要和她划清界限似的,从此不相往来。
真是奇怪,她明明也没有做什么让他厌烦的事。不过他这样也好,她便不用再担心他突然的造访或传唤。
而且,手链也回来了!
他送她的布老虎,那么精致惹人喜爱。
还有她的这些个宝贝,也重回她的怀抱了。
抛却疑虑,她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喜悦里,笑得明媚。
展渊却笑不出来,他一路回宫,阴沉着脸。
有一点他确实没和她说谎,他真的要忙起来了。
永朝立王储吸取前朝灭亡教训,以贤为尊,嫡长次之。因而立储本身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哪里有所谓的手足情深、李代桃僵。
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更加繁乱。
他早劝说自己练就喜怒不形于色,却唯独今日,他难以控制,直接表达出不悦来。
心底涌泛几丝浮躁、不安。
仿佛是一块到手璞玉,又推出去转给别人,而且还要看着那人把这块玉砸碎。
叹一口气,他思绪有些混沌地看着自己的腰间佩玉。
尽人事,听天命。
他能否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