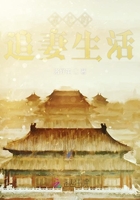陆昭九在李府待了近一个时辰。
听见外面的声淡了下去,玉色的影自树上轻盈的一跃而下,捡起地上箭筒长弓,跟了上去。
江府大门外,一主一仆搬着一张凳子坐着,江挽舟在前,成景在后。
江挽舟的手在桌上有规矩的轻声叩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乱了,他看着路北,望眼欲穿也没见着看个人影。
夜里天降了寒,成景冻得搓了搓小手,只想回家,“将军您要是担心,不如直接去宋府找她好了,人就在宋府又不会跑,这么急做什么?”
谁说在宋府就不会跑?宋府就是龙潭虎穴!
江挽舟漠然的看着远处,“谁说我在等她,云扶柳又不是没长腿,自己不知道回来。”
可他还没说是谁,他怎么就答上了?成景看穿了江挽舟死鸭子嘴硬,偏偏这人还不承认。
“不等人,您半夜跑这里来坐着做什么?”
叩叩两声,“乘凉。”
成景猝,睁着眼说瞎话他见过最厉害的,大概就是他家将军了。今年天气古怪,雨水多得很,刚热两日又开始下雨降寒,根本就没怎么热起来。
乘凉是乘凉,就是凉得直打哆嗦。
陆昭九还是第一次回这么晚,两人在江府大门口从黄昏等到日色落尽,又从暮色四合等到眼皮四合,也没见她的影。
等着等着,成景又吱声了,“将军还是去宋府看看情况吧,兴许宋夫人一直没能顺利生产,公主殿下还在等着。这女子生产,就是一两日也是常有的,要是这儿熬下去,公主的身体也扛不住。”
江挽舟拒绝得很果断,“不去。”
陆昭九摆明了是去宋府给宋溪止送点心!上回她说得好听,做好了吃的等自己回来,结果他到现在还没吃成,她倒是给宋溪止先送去了。
她特意去见了别的男人,还有备而去,他要是亲自上门去接,岂不是绿得明明白白?
他不要面子的啊?
最气人的是,这人在宋府外面和临月争风吃醋打架就算了,不知道怎么买了一张凳子还是赊的江府的账!人家老板要凳子钱都要到江府来了!
他今日人在家中坐,绿帽就稳稳当当从天上往他头上掉,躲都躲不开。
女人打架这么剽悍,他猜都是陆昭九抗凳子砸人把凳子给砸坏了,要赔钱赔不上,才可怜兮兮赊了账,找到了江府来。
老远跑去给宋溪止送吃的献殷勤,出了事还不得找他擦屁股。
江挽舟正气着,缓慢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抬眼看去,瘦弱的身影远远的靠近了,身上披着,嗯……逶迤到了地上,一看就是男子的披风。
“将军将军,是公主回来了!”
江挽舟冷淡的扫了他一眼,“我知道了,不瞎都能看见,淡定。”
他们又不是等她来了,有什么好激动的。
“是是!属下明白!”成景心领神会点点头,“我们继续乘凉。”
陆昭九走得近了,江挽舟才看见肿的像核桃一样的眼和通红通红的鼻尖,他掀袍起身,匆匆迎了上去,“乘什么凉,还不赶紧接公主!”
成景:
他怎么有点摸不着头。
“你怎么回事,这么晚才回来!”江挽舟轻声呵斥一句,朝着她一步步靠近,逐渐看清她脸上的神情,脚步越走越快。
停在他面前没说话,陆昭九吸吸鼻尖,从他身侧绕开,走了。
江挽舟伸手拉她,扑了个空,转过身看见她瘦弱的身体被包裹在宽大的披风下,莫名的心疼。
陆昭九疲惫了,不想应付江挽舟,一步步缓慢却坚定的往前走。走出两步,背上忽然一暖,她涣散的瞳孔有微光,脚步停滞下来。
“好了,对不起,我刚才急了。”江挽舟从身后环抱住她的肩,不知道怎么就语无伦次了,“我只是担心你。”
她走开的时候,神情陌生的像是另一个人,仿佛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陆昭九只贪恋半刻,往前走了一步,从他怀里走出去,“我有点累,先回去休息。”
目送着她走进江府大门,江挽舟的脸色才缓缓往下沉。
“成景,去查看今日在宋府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母后!母后!快开门!”临月赶回宫中,不听御医的劝说去太医院包扎伤口,径直赶去了太后现居的郇安殿。
太后已经睡下,外面的奴才不肯替她传话,她只能自己在外面敲门。
太后睡得浅,几声便被吵了起来,大病未愈,她脸色泛着蜡黄,不大好看,“孙嬷嬷,怎么一回事?”
“回禀娘娘,是临月公主来了,她一定要见您,我们也拦不住。”孙嬷嬷左右为难。
一边是刁蛮任性的公主殿下,另一边太后下了命令,今晚不许任何人打扰她。孙嬷嬷刚升调到太后身边来,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虽说是升调,可前面有陈嬷嬷惨死的教训血淋淋的摆在眼前,她身处其位,只觉得惶恐。
太后沉了一口气,坐起身来,“让她进来。”
“是。”孙嬷嬷刚应声,有了太后的许可,临月把门推开就闯了进去。她脚步匆忙得趔趄,跑到太后榻前险些摔了下去,“母后,母后,你救救儿臣!”
她声音抖得厉害,浑身战栗得像是筛子一样,心惊胆战的还未舒缓过来,“儿臣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想要帮她,谁知道她这么不经吓,看见屏风倒了就这么死了。
母后,我应该怎么办?
宋公子没看到,可这些事情迟早会传到他耳边的,他的贴身奴才就在那里,那个人一直帮着云扶柳,他肯定会告我一状的。
怎么办?我怎样才能让公子相信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真的不想害她啊!”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临月的话让太后根本听不懂,她头昏脑涨,被她吵得头疼得快要炸裂,“你冷静下来再说。”
孙嬷嬷这才赶上来,在内殿掌了灯。
灯火一映,临月额头上和脸上的血骇人!
太后一惊,伸手抓住临月的手,“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去做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做,可是她就死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临月一心想着宋溪止,现在应该没办法把前因后果好好说上一遍。
太后对她也没报什么希望,慵懒的倦容在一瞬间清醒过来,“孙嬷嬷,去传召公主身边的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