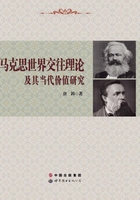白帝城外,十五万大军分陆军水军,在两岸和江面上驻扎。小丫头兰衡站在一艘大船上,趴着船栏,望向天边云霞,愣愣出神。
一个青衫男人坐在她身后的甲板上,一手握着酒壶,一只手撑在船板上,目光散漫,也好像在望着远处天空的绚烂云霞。
他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真是应景啊。你爹要是带军来打我,跑起来也方便不是?”
兰衡回头看向他,皱了皱眉:“你怎么又喝酒?”
正是潘瀞的男人笑眯眯问:“怎么的?你管天管地,管得了老子喝酒啊!?”
兰衡哼了一声,上前去抢他手中的酒壶。潘瀞轻轻躲开,将小丫头拉在身旁坐下,“小姑娘家家的,矜持一点,别动手动脚的,以后哪个男人敢娶你?”
兰衡气红了脸,“你又神经病胡说了?”
潘瀞闭嘴了,上一次打趣兰衡,没想到兰衡的脸皮那么薄,把她气的哭了一个多时辰,还是他后来主动道歉,承认自己有癫疯病,兰衡才没跟他计较。
他可是怕了这妮子的哭功了,那叫一个惊天地泣鬼神!
兰衡见他不说话了,却还是不停地灌酒,她闷闷地道:“你这样会死的。”
潘瀞不以为意,“谁不死呢?”
“你这样会死很快的?”
“那你告诉我,早死晚死,有什么区别?”
兰衡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当然有区别了。”
“哦?什么呀?”
兰衡很认真地道:“早死了,你就看不到晚霞,闻不到花香,听不到下雨。”
潘瀞噗呲一笑,“我已经看过了晚霞,闻过了花香,听过了雨声,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值得留恋吧?”
兰衡摇头道:“你没有死过,你不知道,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死过?”
“我也没有,但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鬼是闻不到气味看不到颜色的,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潘瀞转过头看向她,微笑问:“你到底看过多少书?一本一本的,没完了?”
兰衡含蓄地道:“一般般啦,那……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潘瀞伸手敲了敲她的额头,道:‘我觉得你比较恐怖。”
兰衡皱了皱精致的小鼻子,不说话了,准备伺机去抢他手中的酒葫芦。
然而一个人走来,让她的计划落空了。那是一个少年,也可以说是一个男子。介于少年和男子之间吧,兰衡暗地里猜测,他可能还不到二十岁。
他叫萧七,是个疯子,但潘瀞说他是个聪明的疯子,大概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才疯。
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袍子,披头散发的,走起路来十分潇洒,腰间还有一个酒葫芦晃来晃去。
兰衡不太喜欢他,他见了兰衡也只是轻淡的象征性地笑一下,不是真心的。
他坐在潘瀞的身边,没有行礼,坐姿比潘瀞还要随意。
兰衡偷偷地看了他一眼,真是个疯子。
他笑眯眯地也看了兰衡一眼,点了点头,甚至还甩了一下头发。
兰衡:“呕……”
他问潘瀞:“喝酒吗?从白帝城里打出来的杏花酒。”说着拽下腰间的酒葫芦,在潘瀞眼前晃了一下。
虽然他样貌清俊有君子风,但兰衡还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她鼓起腮帮子喊道:“他不喝!”
萧七啧了一声,叹道:“真是可惜了,春天啊。”
兰衡道:“明明是冬天了。”
他晃着酒葫芦,“但是这里面有春天的味道哦。”
兰衡:“呕……”
潘瀞惬意地躺在甲板上,笑道:“你再进城打酒,记得上城头去找那个叫陵余的疯子,他也许会和你喝一杯。”
萧七摇头:“不行,我怕他把我打下来。”
“胆子如此小,如何能成大事啊?”
“要成大事,得先有命在。”
潘瀞哈哈一笑,“不错。我就喜欢你这副怕死的样子,像我。”
萧七“哦?”了一声,“可我不觉得你怕死啊。”
潘瀞眯眼叹道:“早年我怕死的时候,你还蹲在地上玩泥巴呢。”
萧七面露可惜,“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潘瀞问:“想好了没有,怎么祸害那城墙上的望夫石啊?”
兰衡没好气道:“那是官哥爹爹,不是什么望夫石。”
潘瀞道:“你瞧他坐在城墙上的模样,不像是望夫石吗?”
兰衡怒道:“你再这么说官哥爹爹,我一定不给你读书了!”
潘瀞撇撇嘴,“算了算了,他是英雄行不行?”
萧七凑过来笑道:“你别这么怕一个小姑娘好不好,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啊?我给你读书!”
“滚!”潘瀞骂道:“就你长这副小白脸的样子,还想给老子读书,老子不砍了你就是菩萨心。”
萧七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长的帅,不能怨我吧,你得去怨我老子。”
潘瀞瞥了他一眼,点头道:“嗯,你这不要脸的精神,也有点像我。”
萧七问:“你不会是我爹吧?”
“我不记得了,把你娘找来我看看。”
萧七撇撇嘴,不说话了。
兰衡在旁边听这两个厚颜无耻之人的对话,实在是难熬,想要起身离远点,却被潘瀞察觉,他坐起来,一只大手掌按住小丫头的脑袋,“别乱跑,仔细水里有大龙,把你抓去了当媳妇,我可怎么和你娘交代?”
兰衡被他按住脑袋,手脚乱舞,却也不能脱身,气的脸都红了。掐腰站在原地,叫道:“放开我,你们两个狼狈为奸,要商量怎么害人,我才不听。”
潘瀞斜了旁边的萧七一眼,忽然笑道:“我瞧你们俩挺配,有意撮合,兰衡你怎么还害羞了呢!”
兰衡眼睛一红,又要哭。
潘瀞连忙道:“打住!你别瞧不起他啊,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将来这个天下,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家官哥,一个就是他了。”
兰衡瞪眼道:“别扯官哥。”
眼前这个邋邋遢遢的无赖,怎么能和官哥相提并论!兰衡可还记得她第一次见这个人的情形。
他蓬头垢面的,从头发里捏出一点黑黑的虫子,问她吃不吃!
从此她对这少年就只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恶心,很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