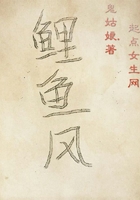麝珠顿时噤若寒蝉,低下头不敢再强辩。不知不觉间,那个戴笠人出现在阴先生的身后,麝珠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深怕他一言不合又要给自己一脚飞踹。
姜冬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个黑影,觉得十分诧异。麝珠虽然喜欢仗势欺人,但她自身的功夫并不弱,她在阴先生面前好像十分畏惧这个人,不是打不过的那种畏惧,而是根本不敢与之对抗。
姜冬想不明白,在阴愁岭中除了阴先生和宋修臣,还有第三个人会使麝珠如此畏惧吗?畏惧,且十分不服气。
阴先生合上了那本所谓的《抱朴决》,对那个人道:“你赶上好时候了,湖底水闸打开了。”
那人负手而立,沉默不语,似乎毫无兴趣。
阴先生自言自语叹道:“风起云涌,东吴要易主了,要易主了,才三年不到……”
那人忽然问:“你有什么打算?”
阴先生道:“鹬蚌相争,我为渔翁。”
那人闻言,呵呵一笑,似乎极为不屑。
阴先生丝毫不以为意,起身,将两本手册递给那人,淡声道:“虽然不是这妮子所谓的什么《抱朴决》,但却是潘瀞亲笔所写的寻龙点穴心得无疑,倒是有些用处。”
姜冬听他识破了自己的胡诌,却破天荒没有动怒,一时心情起伏不定。原因显而易见,阴先生似乎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好事,他心情不错,现在并不想与她计较。
那人接过手册随意翻看了几页,置之不理,问:“潘瀞和宋修臣都在皇宫吗?”
阴先生笑道:“应是如此。想不当我那徒儿竟然能叫墨家重新打开浮水房机关,我真是小觑他了。”
姜冬心中道:“你还敢小觑宋修臣?哄鬼呢!在那祁连山地牢中打的不是你吗?”
那戴笠人沉声问:“他们要杀东郡王?”
阴先生呵呵笑道:“走,你我不妨守株待兔。看个分明。”
戴笠人问:“要去湖上?”
阴先生目光看向姜冬,姜冬浑身一颤,立刻放下帘子。
只听阴先生在外面道:“两个妮子,也跟过来看看好戏吧!”
姜冬握住华衍的手,正迟疑,戴笠人在车帘外温声道:“不要怕。”
他的这句不要怕,温和平正,带着点鼓励和安慰的意思。姜冬没办法,与其在这里磨磨蹭蹭最后被阴先生拽出去,不如她自己大大方方的下车。
她握住华衍的手,掀开车帘子,戴笠人还颇有风度地伸出手臂,给她充当扶手。
姜冬扶着他的胳膊跳下了马车,又将华衍扶了下来。
阴先生给麝珠使了个眼神,麝珠不情不愿地退下了。华衍躲在姜冬的身边,姜冬不停地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抚。
阴先生道:“腿在你身上,嘴也在你身上,但是你和这小公主的命,在老夫手上。你知道该怎么做?”
姜冬微微点头,阴先生无非是告诫她不要跑,不要喊。
戴笠人率先走在前面,阴先生走在最后,姜冬和华衍在中间。姜冬走的较慢,她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每走一步都是咬牙坚持。
戴笠人与她的距离渐渐拉大,阴先生在后面不耐烦道:“走快点!”
姜冬被他推了一下,向前踉跄几步,戴笠人稍稍停顿,温言道:“不必走那么快。”这一次,他等姜冬走上前,然后在她身侧缓步行走,只稍稍超出她半个身位。
阴先生被气得不行,“你小子,一定要一个地方摔两次,是不是?”
姜冬忍不住侧首望向身边的人,他脸上蒙了一块布,看不见面目。
戴笠人似乎察觉到姜冬在看他,但他没有停步,也没有转身,只是温言道:“我与姑娘算是半个旧识。”
姜冬心头猛地一震,心中涌出一股诡谲难言的感觉。他顿了顿,又笑道:“我认识你而已,你却并不认识我。”
姜冬闻言,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她松了一口气,收回目光,看向道路前方,她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要去湛王府吗?”
他点了点头。
“湛王府守卫森严,如何才能进去?”
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道:“最近潘姚和湛王,似乎闹了一些不愉快。”
姜冬心说不是“一些不愉快”,而是大不愉快,但这画蛇添足的话,她自然是不会说出口的。
戴笠人自顾自道:“潘姚是至情至性之人,那南尘君之死,实在是要了她半条命去。”
姜冬见他对这太安城暗中的局势竟是了如指掌,疑惑道:“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
问完之后,立即觉得不妥,她现在还是个俘虏,未免问的太多了。
阴先生果然冷声道:“你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了吗?”
戴笠人摆了摆手,“既然落到你手上,对你卑躬屈膝难道就有好果子吃?与其战战兢兢,不如从容处之。”
姜冬心中一安,暗自觉得他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同时,她心中有生出了一个猜测,会不会这个人也是“落到”阴先生手上的呢?出于某些原因不得不为虎作伥,但实际也是身不由己。所以他才会对阴先生是这个态度。
阴先生阴恻恻道:“可若是逾矩犯禁,就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转过头,对阴先生道:“我说了,不要触到我的底线。”
阴先生拂袖冷哼一声,居然没有一掌将这个出言不逊的下属打飞过去,而是不说话了。
姜冬心中惴惴,只觉得神奇,当年宋修臣做阴先生徒弟时,应该也没有这种待遇吧?如此猖狂嚣张,到底谁说的算?
她道:“我不问了,走吧。”
几人沉默,在寂静的街道上走了一段后,转入了一条巷弄,姜冬忽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须臾,她猛然醒悟过来,这不是她以前常走的巷道吗!她的小院子,在陈平湖府后院,这不就是朝她小院方向走的路吗?
果然,如她心中所想,几人来到了小院门前。姜冬抬头望着这个久违的院门,有一种亲切感,更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戴笠人推开了院门,率先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