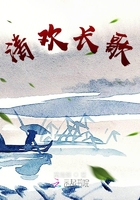玉兰手把手教她如何把帕子打湿、拧干、敷在静训额头上,单冰冰认真地跟着学,正说着,一个小厮送来一包药:“李大夫说了,三碗水熬成一碗药,趁热让程小姐喝下去,每两个时辰喝一副,要是喝两副还烧,就派人去叫他。”
“哎,知道了。”玉兰接过药包就张罗着煎药的事情,单冰冰的丫鬟也跟着转悠,整个客院一副忙碌的景象。
这是单冰冰长这么大第一次干正经事,她紧紧地盯着静训,还是不是上手摸一摸她额头上的手帕还热不热,要是不热了就赶紧换一条新的,连她的丫鬟莺儿想帮忙都被她赶出去了。莺儿只好去院子里找玉兰说话,“玉兰姐,你说大小姐能坚持多久?”
玉兰掀开黑砂锅的盖子搅了搅,不让药材沾到砂锅底部免得焦胡了,“大小姐好不容易想干一件正经事,你别打击她的信心。天色不早了,你去将大小姐的饭菜领到这里来吧,我估计大小姐是不会回去吃了。”
莺儿看看天色,说:“的确不早了,我去领大小姐的晚饭。”
玉兰拉住她,吩咐道:“你到了厨房看看有没有口味比较清淡一些的粥,程小姐现在不能吃饭,先用粥垫一垫吧,总不能什么都不吃。”
“哎,知道了。”莺儿应了一声就出门去了,不多时就将单冰冰的晚饭带来了,她将饭菜从食盒里拿出来,说:“大小姐你先吃饭吧。”
单冰冰将手中的帕子递给她,说:“那你先照看着,我先吃,一会儿换你。”看到桌上放着的粥碗问:“怎么还有一碗粥?”她向来不喜欢喝粥的。
莺儿解释道:“这是给程小姐喝的。”
“那就先喂她吧。”单冰冰放下碗筷端着粥碗走到塌边,“你将她扶起来。”
莺儿坐在床头将静训扶起来靠在自己身上,这两天静训迅速地瘦了下去,莺儿被靠着也没有觉得吃力。
单冰冰舀了一勺粥,细细地吹凉了送到静训嘴边。静训并非得了绝症的人,她这两天为了尽快回来搬救兵,饮食基本上都是在马上解决的,饼子又干又硬,吃饼无非是为了维持生存。这时候闻到米粥的香气,不自觉地张开了嘴,不多时一碗粥就喝完了。
“呼!”单冰冰呼出一口气,说:“还好还好,还知道吃,就没多大的事。”
放下粥碗狼吞虎咽地将自己的饭菜吃完了,她从小挑食的厉害,这还是第一次将饭菜吃光呢。
刚放下碗,玉兰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进来了,单冰冰闻了闻,嫌弃地说:“怎么这么苦?”
“良药苦口,药都是苦的。”
三人又是一顿忙活,不过喂药可比喂饭费劲多了,静训一闻到苦味本能地将头撇到一边,洒出来的比喂进去的都多。单冰冰从来不是个好脾气的,吩咐玉兰:“你扶住她的身子。”又吩咐莺儿,“你捏住她的下巴。”
“大小姐,你要做什么?”
单冰冰嘿嘿一笑,伸手捏住静训的鼻子,静训迫不得已张口,就被她灌进去一碗浓稠的汤药。
莺儿:
玉兰:
还是大小姐有办法。
见静训安静地睡着,单冰冰说:“你俩也都去吃饭吧,吃饱一点儿,晚上要熬一夜呢。”大夫说了,只要熬过了今晚,明天不发热了就是好了。
有了一碗汤药打底,静训的热度明显退下去不少,不等三人的松口气,她又烧起来了,整个人连身上都是红的,三人又是一顿手忙脚乱,如此这般,到了第二天早上静训的热度才退下去,只是整个人病怏怏的,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当她知晓单冰冰照顾了她一夜,非常感动,然而这姑娘却不以为意,打着哈欠说:“困死了我,我要回去补个觉。对了,我问过三哥了,他已经将消息递出去了,估摸着明天就有消息了。”人跑得慢,但信鸽飞得快,他们二贤庄饲养了不少帮忙传递信息的信鸽,人用两天的时间,鸽子一天就能打来回。
静训做了一晚上叔宝哥哥被砍头的梦,梦中她无能为力,现实却朝着好的方向走,放松之下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了,她一睁眼就看到玉兰满是笑容的脸,“程小姐,好消息!”
静训顿时就清醒了,“是叔宝哥哥有消息了?”
玉兰笑着说:“是,那边传来消息,说秦少侠被关在县衙里暂时性命无忧。”
“那就好那就好。”静训拍拍胸口,梦果然都是反的,“扶我起来,我去找单二哥。”
“这、”玉兰有些为难。
“怎么了?还有别的事情吗?”
玉兰说:“的确是有一件事,是关于大公子的。”
“你们大公子?他找到了?”
“是,秦少侠发现的。”
“这可奇了,叔宝哥哥不是被关在牢狱中吗,他去哪里找到的你们大公子?”
“就是在牢里。秦少侠传信出来,说大公子被人诬陷,如今与秦少侠一起关在牢里,而且两条腿被打断了,已经断了近两个月,再不想办法营救,恐怕腿就真的废了。”
静训大吃一惊:“怎么这么严重?”
玉兰点头:“就是呢,二庄主和大小姐急的跟什么似的,连大小姐说要去劫狱,二庄主都没驳斥她呢。”
静训掀开被子,“我去看看。”
玉兰急忙上前扶住她,“你现在身子还没好利索呢,晚上风大别再加重了病情。”
“你去为我取件披风来。”
见她执意要去,玉兰也不好一直拦着她,只好去取了一件披风过来,将她裹的严严实实的,两人才出门去了前院。
刚进了前厅,就看到单雄信坐在上首长吁短叹的,单冰冰坐在下首哭得眼睛跟兔子一样。见她进来了,单冰冰哽咽着说:“你怎么来了?”
静训向单雄信点头算打过招呼,然后坐在单冰冰身边,说:“我刚醒就听说了大公子的事情,赶紧过来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
单雄信道:“自从收到秦兄弟的消息后,我们的人知晓单冲被关在监狱里两个月之久,也是大吃一惊,立即着手去查,刚刚又传来了消息,说冲儿在那边得罪了张朝的妹妹,被他诬陷为采花大盗,被张朝的妹妹用记迷晕关进监牢里,那孩子宁折不弯,被人硬生生打断了双腿。”
“那姑娘这么恨得心?究竟是什么仇怨?”
“你有所不知,我那侄儿相貌不错,走在街上经常收到姑娘们送的鲜花、手帕,这次就是因为张朝的妹妹看上了冲儿,冲儿不从还出言嘲笑,这才惹怒了那个毒妇,那毒妇仗着她兄长是县令,让人在冲儿喝的水里下了迷药,冲儿一时不查就着了道。”
静训无语,这张姑娘怎么跟强抢民女的恶霸一样,只是这性命掉了个。
“那得尽快将他救出来,伤筋动骨一百天,大公子已经伤了两个月了,若是当初没有接好断骨,骨头歪着长,若再想接好,得将骨头再打折,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单雄信叹息:“我何尝不想将他救出来?若只是冲儿一个人,我们这就去劫狱了,但秦兄弟跟冲儿一起,我们总不能只救冲儿不就秦兄弟。”
静训无语,这事还真有些棘手。“对了,徐道长回来了吗?”
单雄信摇头:“好没有,也没有传信回来,我心急如焚啊。”
静训咬咬牙,说:“要不,单二哥先派人去救大公子吧,到时候别管叔宝哥哥就行,这样就能表明叔宝哥哥跟二贤庄没有关系,以后再为叔宝哥哥洗脱罪名就好办了。”
单雄信低头沉吟了一下,说:“等我回去再想想,若明天徐道长还没有消息传来,我们就准备动手。”
第二天一大早,徐道长终于送来信了,信上说蔡太守已经答应将秦叔宝移交到潞州审讯,至于能不能洗脱罪名,还要再审讯一番才能有结论。
静训开怀不已,对单雄信说:“如此,我们就趁着押解叔宝哥哥去潞州的时候,去监狱里将大公子劫出来。”
单雄信与众兄弟又商讨了一番,定下计谋,马不停蹄地赶往平顺。然而,连他们都没有料到平顺竟然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这张朝自从做了县令之后,就鱼肉乡里,搜刮民脂民膏,弄得辖内百姓苦不堪言。不仅如此,稍有不顺从,就会被县衙的人用各种罪名关进大牢,轻者关个两三个月,罚没全部家产就能出去,重的就要关个十年八年的,弄得一家子妻离子散的。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平顺县衙里的监狱关满了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被压迫的没有活路的老百姓只能凑在一起密谋逃狱。
因为秦叔宝和单冲两个的罪名太大,所以将他们单独关押起来,所以另一边的监牢里的密谋并不知晓。
这夜,众人似乎都睡着了。秦叔宝正睡得迷糊的时候,突然听到另一边有喧哗之声,他立时就醒了过来,他竖着耳朵听,似乎是谁发了急病,同一个牢房的人正在呼叫狱卒。
狱卒睡得正想,被打扰的好梦自然没有什么好气,大声斥责着那帮贱民打扰人休息,没想到他打开牢门想进去看看如何了,刚一进去就被人按到在地抢了钥匙。他大声喊叫,却阻止不了罪犯们如潮水般涌出去。
拿到钥匙的老百姓将所有的牢门都打开,让所有的人都跑出去。秦叔宝拉住给他开门的那个中年男人,说:“你可知道逃狱是大罪?”
那人挣脱开他的胳膊,“横竖都是个死,我宁可死在外边也不愿意被人冤枉死!你要逃就赶紧逃,不逃就老实待着。”
秦叔宝看看隔壁牢房里的单冲,他的双腿不能再耽搁了,咬咬牙,跑到隔壁牢房里,顾不得后背上的伤,将人背在后背上顺着人潮往外冲。
因为是半夜,县衙里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大门就被人打开了,众人如鸟兽散,瞬间消失在大街小巷中。等张朝带着人来追,秦叔宝已经背着单冲跑了二里路了。如今城门未开,他们出不了城,又没有落脚的地方,秦叔宝问:“你们二贤庄的据点在哪里?”
单冲说:“我对家里的买卖不感兴趣并不知晓,不过我在平顺有个朋友,要不咱们先去他家避一避?而且他的叔叔跟我二叔有交情。”
“你的朋友靠得住吗?”
“自然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