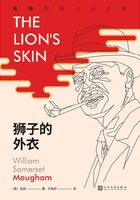红薯和玉米一度是胶东人的主食,到现在“地瓜粑粑饭”还是农家饭的代称。地瓜就是红薯这个不用解释,粑粑在不同的地方是多种食物的代称,在胶东只是指玉米面儿加小苏打,充分揉搓后贴到铁锅内侧熟后所成的饼状物,颜色金黄,底部烙出一层深棕黄的硬硌巴,香。玉米面儿的用途大半用来做粑粑,还可以做糊糊喝,别的做法少。地瓜的做法就多了。
地瓜可以直接烀来吃,好的地瓜蒸出来瓤儿金黄稀软,甜到黏手。
大宗地瓜被切成地瓜干。刚收获的生地瓜,就在地里用一种铁擦子擦成大片,直接晾晒。秋天路过胶东的田野,常常看到大片大片的洁白,就是在晒地瓜干。地瓜干当然比地瓜本身脱水快,晒好了就可以粉碎或者直接使用了。地瓜干可以人吃,也可以喂牲口。烀熟了的地瓜干硬而面,少水分,不好吃。
地瓜干可以粉碎成地瓜面,地瓜面和水蒸食,成品微黑,半透明,有弹性,我们叫它“肉儿粑粑”,微甜,比地瓜干可口些。地瓜面也可以做成面条,因为它没有韧性,只能是在热水锅上架上长长的擦子,将面团擦进锅里,指头长的一段一段,黑黑的,甜不唆的,是有的人的最爱,我却最不爱吃——小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点着油灯,我们小孩子跟姥姥坐在炕上等饭,一闻到又是地瓜面条子的味道,我就哭。
地瓜生的时候,不切片也可以用擦子擦成地瓜丝。地瓜丝晒干了,蒸熟,放到一个大缸里当做猪食。刚蒸出来的时候,人也可以吃。我妹妹从小爱吃饭,好养,我们这里形容这种孩子“泼食”。她从幼儿园回家,又饿又着急出去玩儿,就从大缸里捞一把地瓜丝团成球,又进屋拿一块蒸虾酱,大口大口吃着就跑出去了。圆圆的红脸蛋,戴着虎头帽,帽上嵌的小铃铛叮当作响。
地瓜最细致的做法,可以出门见客的,是做成熟地瓜干儿。生地瓜干一般被叫做地瓜干子,地瓜丝被叫做地瓜丝子,都带着一股不待见的味儿,惟有熟地瓜干加个“儿”字,透着软和,带着亲切。地瓜蒸熟去皮,切片后晾晒,到一定程度后入纸缸叠放,到糖分析出,地瓜干通体履上一层洁白的糖霜,就成了。这层霜,我一直认为跟鲁迅嗜食的“柿霜糖”有同等效用,而且产生的程序也大致相同。
别看熟地瓜干儿家家会做,成品差别可就大了。我舅妈今年八十岁,她一辈子糟蹋了无数地瓜。不是晾晒得不够,水分太大,成品不出霜,发酸,就是晾晒太过,水分太少,成品出霜不良,又薄又少,硬得硌牙。我爸爸的姨妈今年九十五岁了,晒得一手好熟地瓜干儿。糖霜又厚又白,地瓜干儿又甜又软,咬开后金黄半透明,特别好吃——这东西原料很重要,老太太家处山区,地瓜品质好。我舅妈家全是泊地,地瓜水分大,品质差。
王小波的姥姥家是胶东的,他的哥哥王小平觉得胶东农民太奇葩了:吃着牲口都不吃的饭,干着牲口都干不了的活。尤其是长年吃地瓜,造成胃酸过多,他家好几个亲人得了胃癌和胃炎。他说得太对了,可那是帝都人民的看法——地瓜不是粮食,但总是食物,有得吃总比饿死强吧,得病总比去死强吧,而且地瓜产量那么高。
现在地瓜是点缀了,烤地瓜且卖得很贵。乡下的亲戚给我送来自己种的花生榨出来的油、自己种的麦子磨出来的面、自己种的地瓜晒出来的熟地瓜干儿,这些东西,超市里都有,也不贵。可这些东西里有花钱买不来的手工,有花钱买不来的郑重和真心。我咬一口洁白金黄,温暖的亲情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