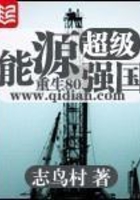华延心听儿子这样说,心中有几分疑惑:“你不是说那大姐姐是严国人么,怎么会和父王长得像呢?”
可华瑾心就是坚持,说:“大姐姐像父王,也像延德皇叔。”
“哪里像了?”
“眉毛,还有眼睛。大姐姐眉毛弯弯的,眼睛像皇爷爷赐给瑾儿的琥珀球。”
华延心笑了,道:“琥珀色的瞳仁儿,景国人皆有之。又岂是父王和你皇叔才有呢?父王知道了,你说的那个大姐姐,大约是在严国出生的景国后裔吧?又或者父母之中有一方是景国人,所以也生得一副景国人的面孔。谁能想到在这异国他乡竟能相遇呢?这也算一段好机缘……”
他说着这话,低头看去,小家伙已经在自己怀里睡着了,小小的手上还捧着一个琥珀球儿。大约是逛了一天累坏了,他在父亲怀中睡得格外香甜。
华延心抚摸着那张小脸,宠溺的笑了,连忙呼宜章进来,将小王爷好生抱出去安置。他自己又泡了一阵,方才起身,换好就寝的中衣,披上墨色狐裘,步至寝殿。见宜章和乳母正在外殿小床,守着华瑾心睡觉。他便叫了宜章一声,让他跟着自己进入内殿。
华延心进了内殿,随随便便坐在床上,侍女端上茶来给他漱口。宜章垂手侍立,华延心漱了口便问他:“今日瑾儿在街上遇见的那个女子,是何来历?”
宜章答道:“回王爷,那女子做严国人打扮,说话亦是严国口音,模样却是景国人的模样。”
华延心亦肯定了心中的想法:“她大约是身在严国的景国后裔吧。”
宜章表示赞同:“奴才也这样觉得。她说自己姓越,多半是景城人士了。”
“听说她送了瑾儿一套做奶茶的铜吊子?”
“是。”
“拿过来给我看看。”
宜章便吩咐人拿了那个包袱来。华延心见那包袱皮小小一块,却是密国织锦,心中纳罕,道:“看来看来此女家世不俗啊,这样贵重的织锦,她竟拿来做包袱皮,还随随便便就送与萍水相逢的人了。”
宜章到不觉得稀奇,他身为下人,习惯了察言观色,也见惯了人家的察言观色,只说:“那女子大约是见咱们小王爷衣冠不俗,才送的吧。”
华延心听他一语,也是了然,道:“也是,景城多商贾,她多半是越家的人,察言观色是会的。”
说着打开那包袱皮,将铜吊子提在手上,掂了掂重量,笑道:“精制黄铜。”
又仔细看了看那三个盒子,一一打开来,当打开最后一个盒子,满是皆是奶香,华延心又是一笑:“这是醍醐。”
心想那女子若不是大富大贵,此番也算下了血本了。
想着便将盒子盖起来,把整个包袱递给宜章:“好生收着吧。”
宜章忙接过包袱,命人收了下去。
华延心又自言自语道:“瑾儿竟然在街上偶遇这样的好事,也算他有福气,只可惜他年幼,人家纵使拿醍醐调味的奶茶,他只觉得腥咸难喝吧。”
说着又笑了,又摇摇头。忽然想到瑾儿说那女子长得像自己,不由得问:“宜章,那女子究竟是何样貌?”
宜章便用心回忆起她的样貌来。
他伺候小王爷喝茶的时候,那女子于桥上踱步而来,身边带着婢女侍卫,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或少夫人,闲逛至此。她听见小王爷跟老板娘的对话,似乎很有趣,就过来问老板娘要茶喝了。
她模样俏丽,笑起来的样子甚美,那时他对她的印象很深。后来那女子上楼了,他伺候在小王爷旁边,见得多的是她的背影和侧脸,那轮廓看上去,只觉得有一股寂寞之感,却不像是妇女闺怨,到更像是英雄成名之后的那种寂寞。
他偶尔看见她的侧脸,暗暗觉得她像一个人。
“那女子……眉目之间,有几分像……像王爷。”
“哦?”华延心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连宜章也这样说。
“哪里像我了?”
宜章低声道:“眼睛……像极了王爷。”
说着微微抬眼一看,看见华延心一双星目流转生辉,那华丽的淡彩,竟像是猛烈的药,害他心中一紧。他赶紧向后退了好几步,远远的站在一旁发呆。
华延心见他有此举动,也是一愣,俄而,缓缓叹一口气,道:“……已经七年了,你还是放不下么。”
宜章并不回话,依旧保持躬身的姿势,那低垂的眉目,却是暗暗红了。
半晌,他道:“能****跟在王爷身边,伺候小王爷,已是宜章最大的福气,宜章并不奢求。”
华延心默然,出了一回神,才道:“是我对不起你。”
宜章身子微微一颤,道:“王爷若无吩咐,宜章先退下了。”
华延心道:“你去查一查那女子的身份。咱们现在在风口浪尖上,不得不防。你……下去吧。”
“奴才告退。”宜章说完,逃一般的退出了内殿。
华延心躺在床上,侍女帮他盖好锦被,又将脚炉拿出来换上新炭,放回被子里捂好,静静站在床边。华延心也不抬头看她,只挥了挥手。侍女便放下帐子,自己在床边的地上放了一个软垫,坐下值夜。
帐内传来微弱的念佛之声,还有佛珠撞击的清脆声音。侍女知道,王爷睡前必然念佛的。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华延心嘴唇微弱翻动,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念着这一长串字眼,脑海中却忽然回响起母后说过的一段话。
“……只是可惜了那宜彰,他的眼神再无光彩了。”
那是母妃和氏,在他成婚之后不久的一次觐见中,同他说的一句话。那时陶瑶正刚怀上瑾儿,父皇封了他近文王,离宫之前觐见母妃,和妃娘娘同他相视而泣,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和妃谈到他的新婚妻子,谈到未出世的小孙儿,甚是开心,只是不知为何,突然讲了这样一句话。
这一句话却像一把最锋利的刀,不经意间,狠狠刻在他的心里,伤痕深不见底。从此宜彰的名字,成了‘宜章’。只因他的眼神,再无光彩。
他不知道母妃到底是不是知道。他心里觉得母妃定是不知道的,景国礼教森严,母妃若是知道那些事情,大概决不能允许宜章活着,更不许他留在王府,留在自己身边。
他很庆幸,庆幸他们藏得那样好。他也很痛惜,痛惜他们藏得那样好。
一晃就是七年了,他们瞒过了所有的人,大约也瞒过了自己的心。若不是今日不经意的对视,也许这一辈子也就平静念佛,心如死水了。
华延心只觉得心跳骤然,有一种十分微妙的感觉盘桓在他的心中。今日瑾儿在街上偶遇的那个红衣女子,竟然打破了他七年的心如止水。这究竟是什么兆头呢?
若是心延寺的青灯主持在,他便可以问他求一个解了,又或是求一支签,问一问吉凶。可惜他此时身在周国,周人是最不屑景国那念经诵佛、祭祀问天的那一套的。
心绪翻飞至午夜时分,华延心才渐渐睡着了。手上握着的玉佛珠,本是触手生凉的寒玉,却慢慢的变热起来。那一颗一颗的珠子,变成了一根一根的手指,根根火热,与他紧扣。
他几乎是本能的握住那双手,手却一阵微疼,紧接着感到一阵冰凉。他迷迷糊糊的感觉到,手上还是那串玉佛珠,触手生凉,像是成亲那日的心。
他紧紧攥着那串佛珠,好像是攥着那个人久别重逢的手,一颗颗珠子硌得他手心发疼。他的手却像是着魔了一样,无法松开,慢慢的竟然开始抽筋了。
入夜的寝殿静的出奇,能听见侍女上夜的脚步声,床边值夜人的呼吸声。他屏住自己的呼吸,想要听一听外殿的声音,想要听一听他的呼吸,却听不见。
忽然之间小孩夜哭的声音传来了,稚嫩尖锐的声音划破寂静,殿里顿时闹起来。
华瑾心在那边殿里哭泣,他听见一个声音在哄着孩子。
“瑾儿不哭,哥哥带你怕树树,爬上树树捉松鼠,喂那松鼠吃谷谷……”
听到这里,华延心再睡不着了。他翻身起来,侍女帮他穿上鞋,披上墨狐裘。两三步走到外殿,华瑾心还在梦里哭闹,宜章抱着他在屋内转圈儿走着,轻轻抖着拍着小家伙的身体。
看见华瑾心那小小的身体,华延心便想到好久以前的那两个小人儿。大约也是瑾儿这般年纪,或者更小一点儿,他记不清了。那时候和妃的羲和殿前院有一棵松树,他年幼时最喜欢在那松树下玩耍,母妃也不拦着他,还告诉他松树上都有松鼠的,他便总想着要捉一只。
有一天他跟着太傅进学,母亲领了一个同他一般年纪的孩子来,告诉他说,这是特意选来陪他读书的,多了小伙伴,他很高兴。再有一天下了学,回去之后,他指着羲和殿前院那棵无数次经过的松树,对他说:“母妃说树上有松鼠呢,我捉一只给你养着玩儿。”
他侧着头问:“怎么抓呢?”
他答道:“爬上去抓。”
“抓住了怎么养呢?”
“拿谷子养它。”
……
他回过神来,宜章仍然抱着瑾儿在转着圈儿,嘴里轻轻念着:
“……带你爬树树,爬上树树捉松树,喂那松鼠吃谷谷……”
华延心只觉得心中一阵抽搐,又凉又疼,打断他道:“罢了,这样哄不好的,将他唤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