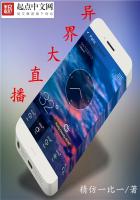“没事了,出来吧。”
时春生走后,谢延才开了门。时悦正满脸苍白地坐在房内,她盯着墙角,浑身都在微微颤动,卷翘的睫毛上有阳光落下,那跳动的光斑清楚地传达了她不自觉的颤抖,听到谢延开门的声音,她才下意识抬头,眼睛里盛着水光,眼瞳幽深。她的眼睛里,没了平日的活泼和灵动,而是带了淡淡的绝望和哀伤,他看着她,仿佛在凝视深渊。
谢延这时也才看清,时悦脸颊边的泪痕,还有不断从她眼眶里涌出的泪水,她在哭,肩膀的颤抖也是因为哭泣。
“谢延你没事吧?”她流着泪,努力克制住情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谢延摇了摇头:“没有,他自己走了。”
此刻时悦看到谢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故作潇洒和不羁般的用力胡乱抹了抹脸上的泪痕,想要挤出个微笑,然而眼泪还是扑簌簌地往下掉,止也止不住。
每次生活给予了她任何希望,她的父亲似乎都迫不及待想要毁掉。时悦甚至有些绝望,她曾一直坚信靠着自己努力能够摆脱如今的生活,能够拥抱明天的美好。然而如今这种信念也动摇了。她真的能摆脱掉时春生吗?她真的能够甩掉他不断烙印在她身上的卑微和不堪吗?
她的心里太难过了。
时悦拼命想忍住呜咽,她死死咬住嘴唇,然而那无法控制的声音还是断续从她的嘴里泄露出来。她的脸上布满眼泪,却仍然漂亮的让人心惊,像是一支带着露水的玫瑰。
谢延觉得心里什么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戳了一下。他情不自禁地走到时悦身边,他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自己的手,放到了时悦的头上。
“没关系的。都会过去的。”他轻轻抚摸着时悦黑亮的长发,把她的头带向自己怀里。
靠着温热的人体,时悦终于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她压抑太久了,总觉得憋住泪水,伪装笑容,就能战胜困境。但是现实从不是这样简单的。她开始伏在谢延身上痛哭。
谢延把时悦揽在怀里,他的思想斗争只进行了一秒,手便不自觉地抱紧了她。这时候的时悦小小的一团,缩在谢延怀里,即便如此痛苦难过,她还是用力压抑着哭声,谢延感受到自己不断被时悦泪水沾湿的衣襟透出的湿意和温度,谢延觉得这些湿意和温度透过衣襟和皮肤,一路传递到了他的心里。
“对不起。”她抽抽噎噎和谢延道着歉,“谢延,对不起。”
谢延温和地拍着她的后背:“没什么需要道歉的。”
“对不起,本来该让开开心心吃顿饭的,没想到发生这种事。”
时悦终于从谢延的怀里抬起头来,她的样子看起来充满了羞耻和难过:“大概把你的心情都破坏掉了。”
“这不是你的错。”
“真希望我今天没约你……”发泄过后,时悦的情绪稳定了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谢延怀中,轻轻地放开了之前揪住谢延衣襟的手,十分讲分寸地移开了和谢延之间的距离,嗓音还因为刚才的哭泣有点哑,“如果今天没约你,就不会让你看到这些事了。”
“我反而觉得你今天约我完全是对的。”谢延顿了顿,“今天约我是最好的时机。”他盯着时悦的眼睛,“如果今天我不在,他是不是会打你?那样我都帮不上忙。”
“谢谢你,谢延。”时悦刚说完,就突然看到了谢延手上被茶杯碎片滑破的伤口,她紧张道,“你流血了!我送你去医院。”
时悦此刻双手捧着谢延的手臂,谢延的手就躺在她温热小巧的手心,他的手在流着血,但谢延并不感到疼痛,他只能感受到和时悦相触的那块皮肤微微的灼热。
“没关系。小伤口,没必要去医院。我讨厌去医院。”
“那我帮你简单处理下吧。”时悦见谢延坚持,她走过狼藉的客厅,来到柜子前,拿出了医药急救箱,她动作熟练又迅速地帮谢延做了清理和包扎。而她自己脸上明明还有因为时春生那一个耳光而嘴角挂下的血丝。
“我来帮你处理你的伤口。”谢延的声音非常温柔。
时悦迟疑了下,才点了点头:“你只要清理一下伤口就好了。其实不处理也没关系,我以前从不处理,也没什么事。”
她这样无意间透露出的信息让谢延有些心疼,她以前都是过得什么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她更小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抵抗时春生那些拳头的时候?
“你是女孩子,脸上的伤不管多小,都是要紧的。”谢延一边说,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然而他的动作却更加小心翼翼了,时悦瓷白的脸已经因为那个耳光青紫了起来,相当明显,像是有了裂痕的瓷器,谢延恨不得呼吸都放得更轻,仿佛一不小心就会碰坏时悦。
在他温和的态度和关照下,时悦的情绪终于渐渐复原。
“你会不会……会不会不想再和我做朋友?”时悦抬起头,看着谢延,“或者说,我们算朋友吗?”
她有些难堪。她很害怕,谢延像是生活在她不可企及世界里的阳光,他或许并没有因为贫穷而疏远自己,但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呢?对于自己的贫穷,时悦已经学会了坦然接受,贫穷不是她的错,然而时春生的丑态,总是打碎她的自尊,让她恢复成那个因为家境而自卑的小女孩。
让人看不起的并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是灵魂的贫乏,而她的父亲,展现出来的内心是那样丑陋。
“你会看不起我吗?”
谢延几乎是被迷惑了,他摇了摇头:“不会。不会的。”鬼使神差,谢延控制不住自己,他俯下身,亲吻了时悦的额头。
这样的时悦让他把持不住,她太美了,此刻又这样脆弱无助,近在咫尺,大概会唤起任何男人的保护欲。
然而亲吻之后呢?谢延的脑子一片混乱,他并没有想好……
做朋友,自然并不用在意对方的出身和家境,也不用在意对方的亲属品行,因为结交朋友,只要认可对方的为人就可以,何况即便朋友,每天所相处的时间也有限,更不可能需要应付对方的极品亲属;然而如果是另外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对方亲属的品行就不得不纳入考量了。
时悦的脸有些红,但是她近乎勇敢地看着谢延。谢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姐!我回来啦!怎么门都没关?”幸而时亮的声音解救了谢延的尴尬。
时亮走进屋内,很快就发现了满屋的狼藉,桌子翻倒了,到处都是玻璃渣子,他变了脸色,很快朝着时悦跑来。
“他回来了?!”
“恩。没事了,已经走了。”时悦朝时亮安抚地笑了一下,然而牵动了嘴角的伤口。
时亮满脸都是愤怒和紧张:“姐,你没事吧?他又喝酒了?又打你了?让我看看,其他地方还有受伤吗?”
“没其他地方。”时悦有些疲惫,“谢延也在,他没敢怎么样。”
“谢老师!谢谢你!”时亮得知时悦无碍,这才感激起谢延来,男孩子大大咧咧,倒是没有敏感地意识到其余什么。
“没关系。”
时悦见时亮回来,强打起了些精神:“谢延,今天对不起了,下次再请你吃饭吧,我们出去吃,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和时亮收拾一下屋子。”
谢延却没有告辞,他看得出,时悦很疲惫了,她一早起来买菜洗菜准备这一桌子菜,大概起得也很早,昨晚又有蟹本道的打工,想必睡得也不早,外加刚才那一场痛哭,力气透支。
“你进去休息吧。”
时亮也瞧出时悦的精神不济:“姐,你先去休息会儿,我来打扫就行,待会我送送谢老师。”
时悦也无力再强撑,她如今头痛如裂,脸上和嘴角的伤口也火辣辣的疼,眼睛因为哭泣也酸涩难忍。她再次感谢了谢延,才回了房间。
而她走后,谢延仍并没有离开。
“我和你一起打扫吧。反正下午没什么事。”
时亮拒绝再三,然而谢延的态度坚决,他便也接受了。
谢延先清扫了碎落在地面的各种玻璃碎片,他一边收拾,一边状若不经意地和时亮说起话来。
“你们的爸爸,经常这样吗?”
“是啊,从小挨打,其实算是家常便饭了,不好意思这次让谢老师看笑话了……”时亮的语气也有些苦涩,“不过我还好,小时候每次我爸喝多了打人,都是我姐护着我,她帮我先挡着,让我快跑。我一直记得有一次,他赌钱输光了,特别生气,拿了皮带抽我们,我姐拼命推着我出去,可是我跑了才没多远,就听到我姐的惨叫。我跑回去一看,他把我姐后背抽得都血肉模糊了!”时亮说到此处,似乎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语气里全是愤怒和痛恨。
他有一些咬牙切齿:“你不知道他下手有多狠毒,就像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仇人,如果我不回去,他说不定真会把我姐活活打死。那一次,我姐伤口感染,发了一星期的烧,差点就没熬过来。”
谢延的内心是震动的,他不知道时悦的童年是这样充满了伤痛。
“你爸爸,之前欠了赌债?”
时亮有些意外:“啊?他确实一直赌钱,但是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欠钱没有,好像没听到,这次回家又发狂,可能只是输了钱外加喝多了。”
谢延心下了然。时悦这次对于帮忙还清自己父亲的五万赌债,并没有告诉时亮,她自己一个人扛了下来。他也突然理解了她为什么之前突然急需用钱,甚至不惜去全裸做人体模特。
这种感觉很神奇。即便距离第一次见时悦,已经过去了很久,然而谢延好像直到现在,第一次才真正重新认识了时悦,了解了她的人生和经历。
时悦在他脑海里,似乎并不再是那晚那个说话粗鲁的问题少女,也不是捉襟见肘的贫困打工女孩,更不是在画室里不着寸缕的漂亮肉体,她只是她自己。
她只是时悦。
“你姐姐打架很厉害吗?”谢延突然想更了解时悦一点。
“厉害。”时亮说起姐姐,脸上也漾出了笑容,语气也带了淡淡的骄傲,“以前因为一直被打,我姐就偷偷去附近的武馆学,我们住的这一带小混混也多,常常有打劫的,学得久了,老师人也好,愿意免费教,我姐又常常得和这一代的小混混打架,就变得很厉害了。”
谢延诚心实意道:“你姐姐确实很厉害。”
谢延此刻正在清理干净地上的碎玻璃渣,突然被墙角一副油画吸引了目光。画中是近乎纯白的世界,一列火车穿梭在雪原,整幅画运用了很多白色色调,然而却丝毫不单调,因为那白色里自然的蕴含了丰富的层次,天、地、雪和山,静谧地伫立在画中,一切都显得冷然而肃静,又这样的浑然一体,而那列行进的火车,即便是静止的画面,但仿佛仍能感觉到它飞驰而过而破开的雪面和轨道边飞溅出的雪沫。外面是冰雪世界,而车内一小节车厢中却露出温馨的黄色灯光,一切的笔触都相当细腻,谢延用手指摩挲着画面,那车厢里有一对年迈的老夫妻,紧紧交握着双手。
“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冬天。我一直记得去往网走的路途上,列车行驶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天、地、雪和山,都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那时候好像能感受到雪花降落坠地的声音,一切安静的不像话,心里也没有任何杂念的安宁,是一个纯净的白色世界。”
谢延陡然想起自己曾和时悦说过的话。她从没有去过网走,也或许根本没去过雪原,然而只是从自己只言片语的描述里,就画出了这样的作品。冷冽中透着温情,粗犷里又带了细腻,像是她本人,凶狠又温柔,勇敢又害羞。
“这是你姐姐画的?”
时亮凑过头:“是的,都是她画的,她画画可好看了,她从来没上过什么正规的油画课程,这些都是她自己摸索的。”
然而让人惋惜的是,两人都发现,这幅画的右下角,被刚才时春生掀翻的汤汁泼到了一个酱色的油点。
时亮的声音也失落难过了起来:“我姐还画了很多,真的很漂亮,就像是画廊里展出的那些一样,可惜很多都被我爸发酒疯时候撕掉了……”
“她很有天赋。”
时亮笑笑,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竟然也很快把杂乱的屋子收拾了干净。时亮再三谢过了谢延,才把他一路送回了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