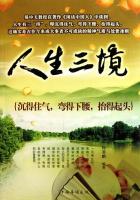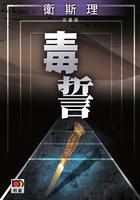虎庆从来没有说过话,冷冷的眼神要么望着旱水池子出神,要么就看天空,怅怅的看,然后狠狠地往下咽一口唾沫。夜里秋搂了虎庆睡。秋说:“虎庆,说句话我听听,不说憋在肚里的话是要把你憋坏的。”
虎庆不说话。
“你娘就死在这窑里地上的,我不是你娘,你有娘,对吧?”
虎庆不说话,望着窑梁,窑梁上挂了收割下来的玉茭穗。
秋说:“我做不了你娘,只有娘才能这样搂了你睡,你到对面炕上睡吧。”
秋想将一将虎庆。虎庆不说话,翻起身下了炕到对面的炕上去睡。这时候他突然看到窑梁上吊着的玉茭不是玉茭是娘,拖下来的穗子不是穗子,像娘的肠子麻绳一样疙疙瘩瘩坠下来,看到地上涌流的血,血地上躺着娘,一个日本人他败坏了一池水,一池水里躺着全凹的人。他开始呼吸急促起来,霎时面色如土,痛苦地将扭曲的头颅歪向一边。他一下翻起身跳到了对面炕上把头埋到了秋的妈妈穗中间,闭上了眼睛。秋叹了口气,搂紧了虎庆。秋睡不着了,想以往。
以往的事情里老有一个人影晃,是武嘎。这人要是他在外面的大山里被杀了,这山沟里的狼也早就该把他吃了,武嘎不想也罢越想就越觉得他人是死了。武嘎的二胡在窑墙上挂着蒙了很厚的尘,秋等虎庆睡熟了起身摘下它,透着窗户漏过来的光吹了几下。秋听到了羊屎蛋“吧嗒,吧嗒”往下掉,秋的脸就热了一下,返身把二胡挂到了墙上睡下了。秋用手搂了搂虎庆,虎庆瘦小的身体像干柴棍子。秋摸着他的头,干瘦脸儿,背和屁股蛋子,胸脯上的骨头横排着秃显出来,往下摸就摸到了他的小锤锤。大拇指长的一个肉虫儿,摸着摸着,就一挺一挺长出来一截子,秋的心喜了一下,那个小锤锤就越发的挺了起来。你见水儿就长,见风儿就扬吧,它果真就长就扬了,一股水射出来,射了秋一肚子。秋笑了一下挺起肚子让它射,等它不射了,就把虎庆挪了挪,自己暖着那一片湿,秋的心里也是一片湿。
拴柱在后柳沟住,后柳沟的房屋被日本人烧了,烟熏的屋子里漏着天光,他趴在灶火前用嘴吹火,结果锅溢了,稀汤灌了他一脸,拴柱有些愤怒了,拣了块石头把铁锅砸了个大窟窿。拴柱肩了铁锅往山神凹走,他要秋看看,他的日子叫什么日子。明明有媳妇,媳妇突然的就和自己没有了一点关系,日本人杀得就剩咱了,咱不疼咱谁疼咱?咱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几个?山神凹后柳沟也不过就我一个,我怕他谁了,我背了锅找你,一个透了窟窿的锅,你得养我,给我做饭,你不给我饭吃,我背着个烂锅坐的你窑门口。
拴柱是个没有欲望的人,但并不等于说他没有念想。他的念想使他梦想着生活,他的念想使他的梦想看见的永远是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和以往的行为方式已经超越和瓦解了他的生存秩序。拴柱想,秋你是我的媳妇,可是我干不了男人干的事情。秋,你不是我的媳妇是谁的媳妇?武嘎的?不对。秋你明摆着就是我的媳妇嘛,我要去找你。拴柱肩了铁锅从风脉山上下来,拐了个小坡坡就看到了秋在院子里给羊剪毛。羊很舒服地躺在秋的腿圪旯,被秋剪了毛的羊在院中央吃着一堆青草,秋的脸红扑扑的,湿濡濡的、很暖昧的气味,给拴柱一种好似到了秋天的梨树下,闻到了烂梨的味道,女人的味道就是烂梨的味道,那些羊闻着这样的味道它们肯定的舒服死了,我拴柱也要闻这样的味道。
虎庆看见了他,拿了羊铲出了篱笆院站到了小坡坡下。
“狗!”
虎庆提起羊铲对正了拴柱,不说话,那目光像皇军的刀一样敌视着他。拴柱身上的汗毛孔就大了,看到深深凹下去的两腮像两张黄纸紧紧地贴在骨头上,拴柱想,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长了这么个样样呢?拴柱紧了一下子尿扭了头想走,又想,我来干啥来了,找秋,一个娃娃家敢来管我!
东洋鬼子给他留下个很不好的毛病,见不得有个事,一有个事就尿紧。拴柱就想骂,骂谁?骂东洋鬼子:
“我日你妈,东洋鬼子,你要再敢来一趟山神凹,再敢来一趟后柳沟,老子要再给你下跪,就不做这人了!”拴柱把铁锅放到地上说:“秋,我的锅烂了,你看着怎么办吧?”秋抬起头说:“后柳沟的房屋烧了,锅又炼不成铁疙瘩,后柳沟十二户人家的铁锅,够你用,你一下子砸也砸不完!”拴柱想:我是天底下最贱的活物了,我活的还不如一头羊!拴柱的屁股蛋上潮湿得淌水,扭了头回了后柳沟。
夜里秋搂了虎庆躺在枕上说话。
虎庆无话。
秋说:
“他来了,就让他进来嘛,他也是个可怜人儿。”
虎庆咽了口唾沫。
秋说:
“活过来的不易啊,像狗一样爬着活过来的能有几个?也就是咱吧。那么多人在你眼睛里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就连一条黑也没有放过,那些个不仁慈的日本人,你要和那些个禽兽计较吗?孩,你得说话。”
虎庆不说话,埋在秋胸前的脸上有些潮湿。
秋说:
“他是我的男人,我现在要不理他了,他活着还有个啥意思。”
虎庆把身子掉了一下扭到了墙前。
秋说:
“你还小,有些事情不懂,人是懂情份的,恨一个人,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睡了就不会恨一辈子。”
虎庆不出声,有一会儿,他扭过来身子搂住了秋。
秋说:
“我不恨他,他活着也是个人,可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秋的脸上有泪水流下来,溽湿了虎庆的头发。虎庆摸着秋脸上的泪扯起被子擦了一下。秋就抬起手抓住了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她要他在自己的身体上划行,她要给他的生长新添一种冲动。
夜是多云的,秋在黑暗里无法看清,但她等待着他的抚摸的时候,仿佛听得见一种轻微的声音,她希望抚摸能给他带来意气扬扬的情感,秋希望他在行将踏入成年的时候,那种冲动因他的长大而使绝了的人口兴旺。秋感觉到了他的心跳,她让自己的心跳慢些,她要慢慢的将深长的意味传递给他,她要撕破她一切天生的羞怯和庄重来纵容自己的激荡。她说:
“虎庆,撩开被子看看,看看我长了个什么样儿。山神凹就咱俩,我不是你娘,但现在到老我们都得在一起,都得相依为命,我要你长大,你要快些长啊。”
虎庆停顿了有一会儿坐起来掀开被子,微弱的星光下他看到秋白色的人体像一条鱼。这么一想他咬了下嘴唇开始机械地抚摸,他的抚摸迎合了秋内心愈来愈响亮的呼声,秋抬起身体一下把他搂进了怀里。
拴柱把黑的皮子搭在柴上翻晒,毒毒的阳光把黑的皮晒得淌油。他翻晒皮子的那份专注神态仿佛是有一件大事等着要办,那目光里满含了看到了神仙的光芒。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也端了碗坐到柴下的石头上看,饭吃完了他看着黑的皮舔着空碗,舔完了对着太阳照照,放下来看着黑的皮继续舔。
拴柱想:狗皮褥子铺到秋的身板下面软软的,秋呵出来的小音会拖得很长。秋的妈妈穗卧在它的上面就像两小鸡子,刚刚拱出了蛋壳壳,他这么着揉着秋的妈妈穗,秋会叫道:揉,揉,揉呵——
拴柱就卷了狗皮褥子往山神凹走。走着走着就想唱了:
闺女好,好个啥?
好了一个下身子。
拴柱不唱了。自己是啥也不懂的人,瞎唱得是个啥?
拴柱从风脉岭上走下来,没等下了坡就看到了秋。秋挑着两桶水从旱水池子里上来,拴柱说:
“秋,我来给你送黑的皮,天凉了铺在身子下暖和。要不我来给你暖吧?”
秋说:
“放窑里吧。你回你的后柳沟住去,我不要你暖。窑炕上有给你做好的棉裤你拿了去。”
拴柱说:
“虎庆他人在不在?”
秋挑着水喘着气说:
“在不在你进去拿了走人,没有人拦你。”
拴柱一听觉得满胸脯都是底气,梗了梗了脖子往窑门口走。
“狗!”
山垴垴上的羊群里传来一声“吼”!
拴柱吓得后退了一步,裤裆里一下子没紧住出了水儿,扔下狗皮褥子就往回走。
秋挑了水倒进水缸里,返回身叫拴柱,看见了黄土小坡坡上漏下了一长溜儿湿,拴柱搂了肚蹲在窑垴上愁着脸想骂娘。秋进屋拿了棉裤递给他,看他那可怜样儿,伸了手拽起了他。
拴柱也不管裤裆湿不湿拿了棉裤就往后柳沟走。
秋在他背后撂了一句话:
“你要是缺甚想要就来吧。”
拴柱没有回头,朝前喊着:“我就是缺你,你就是不回后柳沟。”
虎庆在旱水池槐枝低垂的浓影处坐着,对面秋提了桶给羊饮水,她的背后是几眼空洞洞的窑洞,窑里的人就死在这个旱水池边,他亲眼看见鲜红的人血流着积聚在了池子里,他现在就吃这里的水,羊也吃。想到这些的时候虎庆是孤独的。在后柳沟看到最后的枪声静下来,看到人像跳大神一样倒下去时,他发现他张着的嘴说不出话了。虎庆在秋的臂弯里几次张了嘴想说,可就是说不出。唯一说出口的一个字是“狗”。
虎庆把眼睛拉向秋的脸,他觉得秋的脸就像五爷庙里供的哪个观音菩萨的脸。
这时候他看到秋把刚生下来的一个羊羔子剥了皮,在旱水池边用桶冲洗干净,他知道这是秋给自己煮肉吃,秋要他快快长,他也想快快长。他在秋的身上发现了娘身上看不到的东西,这样想着脑海里就滑进了古怪的恍惚之境,想起窑洞里武嘎抱着她在努力做一件很剧烈的运动,秋裸露着上身扭头看羊窑口爬进来的自己时,面色红润。虎庆想,真是像一条滑溜溜的鱼啊。她脸蛋子朝上,脸上淌着泪,还用拳头打着枕头哭。他走近她身边时,她返身抱起了自己,紧紧地抱在怀里,嘴里叫着:“你怎么还不长大呢?长大,长大!”
虎庆喃喃说了一声:
“长大!”
发出来的音却是:“狗狗。”
夜里秋搂了虎庆说:“你枕着我的胳膊怎这样重?”
虎庆抬起头让秋抽出胳膊。
秋说:
“你一来一来就长大了。”
秋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摩挲着。
窑洞里透着冰霜将至的寒意。天下雪了,雪落无声,秋偏偏就听到了雪落的声音。雪从黝黑的窑垴上落下来,落在院子里的枣树上,又被风吹落到突出地面的树根上。干瘪枯萎的芋头秧子散乱地爬在院中央,雪这时候落在上面就比雨的声音浅。
窑地上的羊卧着,自从羊和人住在一起了,秋就没有把它们再赶出去。羊不断地增加,她不要增加,她把那些个生下来的羊羔子弄死煮了给虎庆吃,她要他长个儿。地上飘起来羊身体上的膻味儿,一下唤醒了她脑子里使她兴奋的东西,在这种兴奋的情绪之下,她开始抚摸他的脸,他的身体,口中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想说的话在胸口反复滚动着。秋的手再一次滑下到他的下体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上面细小的绒毛。秋越过黑暗看他的脸,然后在他的耳朵眼里悄声说了句:“你真的要长大了。”
秋仰面躺着,不看虎庆看窑顶子,窑顶子上有个啥,有个未来。就听得窑门外有脚步声走来,秋知道是拴柱。拴柱夜里不睡,起来捉麻雀。麻雀到天暗下来宿窑檐儿,从窑洞上的麻眼钻进来,扑入草料堆过夜,拴柱知道秋爱吃。用料叉赶麻雀飞起来,飞起来的麻雀往马灯的地方躲,马灯下早有拴柱用小棍儿支起来的荆条筛子,麻雀乱飞撞翻了小棍儿,筛子兜头扣下去,一回能扣住十来只麻雀。用红胶土糊了烧得土裂开缝,把它们一只一只放进篮子里,提了到山神凹,放到窑窗户上,要秋吃。秋不吃,要虎庆吃,拴柱不知道他送去的麻雀都让虎庆吃了,拴柱要是知道了,会生气,一生气就会坐到旱水池子边上骂,骂日本龟孙子把他的日子搞得人不是个人,鬼不是个鬼。拴柱就是不知道秋那个心头恨,秋心头的那个恨是要用一辈子和几辈子来对抗的,拴柱就是知道了也只能垂头耷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