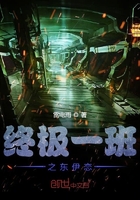山神凹眼下除了虎庆和虎昌,还有一个人活着,他是放驴汉武嘎。
武嘎是山神凹唯一的一个青皮后生,其他的都给充军走了。他之所以没被充走,是他整日在外放驴,他给外村几个大户合起来放驴也掺了几只羊,驴是泉沟的驴,羊是山神凹的羊。他不在泉沟放,也不在山神凹放,要到后柳沟放。他说:
“泉沟的山上树稠有狼,后柳沟有一块缓坡地,草厚。这地方十年九旱,哪里有草让驴吃,就把驴放到哪里呗。”
其实,无论山神凹还是后柳沟的人都清楚武嘎是想后柳沟拴柱的女人。也就是说,武嘎没有女人,他的女人是拴柱的女人。
拴柱的女人叫秋。
秋是民国十九年拴柱他爹从中原买回来的童养媳。秋被买回来时,10岁的她不及7岁的孩子高。黄皮寡瘦的脸皮儿上扣着一双大眼睛,睁开看一只眼睛比嘴大,两只眼睛占了半个脸。一张小嘴凹进了两颊,两半儿脸蛋上就点出了两个小酒窝。由于旱灾,又因为是闺女,拴柱他爹五尺土布就买回了她。
当春水还异常寒冷时,秋抱了一家大小人的衣服到后柳沟的旱水池洗涮。拴柱给她搬一块搓衣石板,石板下有旱瞎子挑了尾巴来回跑,秋就揪住瞎子的尾巴摔在旱水池的石垛上。有人看见了说,河南来的“草灰”杀生,谁也不待见她。没想几年光景下来,秋就像春天潮湿地带长出的小黄菊,灿灿的,像是见到什么就受到了什么的滋润,在青枝绿叶间亮得嫩爽,清朗活泼得像刚脱了蛋皮的小鸡子。
17岁时,拴柱他爹给他们圆了房。圆房只能算是一个结果。因为,打小人们就知道拴柱没有小锤锤,两条细麻腿中间是一个肉球球。秋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星月的阴影挂起来后,她才知道人这一辈子活了个啥。在山沟沟,十五、六岁的闺女都抱娃儿了,儿女房事打早婆家人就示范,秋的婆家却从不提及此事。
月黑的夜里,秋摸着那个肉球球,摸着摸着就睡了。到半夜,听得对面炕上有翻迭声,是公公在摸索婆婆。夜很静,他们的出气声却很粗,有响声冒出来一个气泡,那个气泡一下就撞疼了秋的心。她狠命地拧了一下那个肉球,拴柱被拧疼了,听到对面炕上有动作,就拿腔做调的咳了一声。对面炕上那些个冒出来的气泡就飞远了,气息声就小下来,只是喘息声,还在,还继续,细小的气泡儿还在冒。拴柱就用嘴咬秋的肩,这一咬倒咬出了秋的痛快。秋感到全身像木炭遇了火星子,热烫地叫道:
“咬啊,咬啊,咬啊,咬——啊——”
后一句“咬啊”如鬼魂的游丝,长长的,悠悠的呵出来,对面的土炕上的喘息声像麻绳一样断开了。
白日里,有好事者把秋夜里的音调呵出来,秋听了脸上就好像有耳光掴打后的热疼,心里窝着的羞辱像藏匿了无数串烧红的蚂蚱。
秋肩了锄到坡上的玉米地里锄苗。黄土坡地上因为干旱弥漫着阳光的焦糊味儿。她把锄扔下,坐到地垄的一块石头上生气。风吹来,玉米叶子拥动出哗哗的响哨儿,她把手插进土里揪出一疙瘩野小蒜,放到鼻子下吸吸,香辣青涩的温暖就汪洋了一脯胸膛,脸上有粉粉的红晕浸出来。
“吆呵——”
远处悠悠的滚雷一样,滚来一声男人的喊叫声。
秋把手蓬在额头上抬了头看,见山梁上墨黑的油松现出紫金,有一层烈烈的烟尘铺在上面,那是夜的地气在日头下生出来的张狂,往下看,看不见吆喝的人影儿。秋呆呆地看着远处,不由地想了心事,她恨爹娘把自己卖了,落脚在这山沟里。落脚在山沟里也罢了,一辈子还拴死了这样一个男人。泪水不听使唤流了下来。
这当口,武嘎赶了驴和羊顺了沟口进了后柳沟。把驴和羊赶到缓坡地,见秋在地垄上坐着,四下望望没见有别的人,绕了一圈走到秋跟前。见秋脸上淌泪,武嘎说:“大白天的,哭个啥?”
秋抹了抹泪看看是山神凹的武嘎,说:“没哭啥,瞎想。”
秋又回头看看,说:“坐吧。山神凹的驴赶到后柳沟来放,也不怕路远?”
武嘎说:“远怕啥,再远的路能远过咱这双脚?什么样的山头登不上,什么样的弯道拐不过。”
武嘎说这话时,眼睛转了一个大大的圈,除暸了周围的山上,还暸了秋的脸。
他暸到秋的脸上贴上了红晕。一个女人要见了一个男人,脸上贴上了红晕,那种事情八成有门。
秋不说话,望着地垄边的深沟,沟中蓄满了燥热,正当晌午,热气涌上来捂烫了秋的脸。
武嘎把身上穿的粗布褂子脱下来,揉成一团在脸上抹了一说:
“这天闷热得要死。”
秋闻到了武嘎身上的汗臭味儿。
武嘎把布衫夹到掖下,往前坐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手在自己的身体上搓来搓去,搓下了一些泥撅撅。武嘎说:
“人住的地方就怕缺水,人要是没有了水气,就和这地一样干得能裂开个纹儿。”
秋说:
“裂就裂,遇了雨水倒好,灌得猛。”
武嘎说:
“你就是旱得干裂的地。”
秋没有言语,好象在品匝着武嘎的话。
武嘎用手轻轻擦了一下秋的胳臂肘,秋就一蹶趔,双手往腿中间夹了一夹,顺口叫了一声:“驴。”
武嘎说:
“驴还知道个跳马,鸡还知道个打鸣儿,猫狗都知道个二八月,是吧?人就这么个日哄日哄算了事啦!”
秋的心里浸浸地淫起了一团热燥,一团火。
武嘎进一步说:
“咱打个比方吧,要是你就是那个芦花儿母鸡,咱就是那个黑花儿公鸡,我追着你打鸣儿,你蹶屁股不?”
“没皮脸。”
秋抬起头又低下头笑,把双手抽起来捂了脸。粉嫩的指尖尖上沾了黄土、野蒜汁味儿散开来,秋歪了脸看玉茭地的青苗儿。
武嘎对着远处叫了一声:
“黑——”
岭尖上闪过来一条黑毛狗。
武嘎站起身看着秋,看着看着弯下腰“嗨!”了一声,抱起秋走进玉茭地深处。
黑在玉茭地外面四下里吐了血红的舌张望着。看人。
多少日子燥闷焦枯的山梁上,开始有了一些别样的味道。玉茭的动荡似乎是洪水卷流的头,上下起落,把山脉撞得一片洪荒汪洋。
玉茭熟时,武嘎和秋转移到了后柳沟的羊窑内。天寒窑暖,天热窑凉。铺了干草,秋天的草厚,厚厚的草把驴和羊养得肥腻。武嘎把羊毛薅下来捻成线,削了荆条针绾毛裤,生羊毛织出来的毛裤硬邦邦的,武嘎织了要给秋穿。秋说:
“裤裆中间留下个口,我添了布,生羊毛磨得裆疼,也痒。”
武嘎就笑了说:
“那活儿就是绝痒。”
十几只羊和十几头驴在窑口聚成团,日照的光影从畜生的皮毛中间漏进来,有青白色的滴答滴答声响起,秋知道那不是水声,也不是树声、草声、间或虫鸣声,是羊屎的吧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