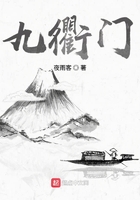高高的红毯尽头,金发的少女垂眸单膝跪地,站在她面前的绝色男人微笑着将一顶王冠戴在她头上。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
底下端坐的血族们站起来欢快的鼓掌,殿堂里的氛围一再拔高。
爱德华站在角落里,双手扶墙朝那里遥望,他虽然也接受了隐先生的初拥,却并没有举办如此盛大的仪式——那个男人对他并不看中。
但是他很喜欢姐姐爱丽丝,这样其实就好了。
静谧的光从身后的窗户里投在小少年的脊背上,他轻轻的眨眨眼睛,转身看向背后刚靠近的两位女仆。
她们满脸温和无情,伸手请他回卧室休息。
“我可以见到姐姐吗?”
“暂时不可以,爱德华少爷。”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不清楚。”
他恋恋不舍的回头看了那个抱住隐先生的少女,她笑容洋溢,浑身好似开着太阳花,可是离自己却好遥远。
女仆们隔绝了一切,他才看向前方步步失落的朝光暗交错的长廊走去,把自己紧紧的锁在房间中。
房里的家具都是人类贵族才用的起的,床上堆着很新的布娃娃与人偶,是女仆们擅自加进来的。
她们以为自己会喜欢。
爱德华披着一层冷光走向小小的窗户,他蹑手蹑脚的推开窗,眺望外面绵延不绝的森林山河,偶尔会有红色屋顶的小房子得以窥见。
他站在原地好久,被冷风吹红了双眼,受过初拥不久的他身体其实并不好,亚门管家嘱咐过好多次,一定要自己多静养,撑过这段时间,身体就会完全结实了。
天空光很白,一些云很灰,如同厚涂过后的草稿画,洋洋洒洒的雪缓缓飘落而下,他深处手接住几片,仰起脸闭上眼睛。
风吹个不停,但他没有感觉很冷,浑身并不难受,甚至觉得好极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好多话,可是好像不太管用。
伤心是止不住的。
他想起还是人类的那时候,每到下雪的日子,家居的那条街上的孩子都会围好围巾,戴上手套冲出家门。
堆雪人,打雪仗,或者躺在雪地里画翅膀。
他和姐姐很喜欢堆雪人,第一个是爸爸,第二个是妈妈,第三个是姐姐,最后才是他自己。
只是母亲走的太早了,父亲因此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姐姐为他付出了太多泪水与代价,那以后,雪是一种奢望,即便下了,也和他们一家毫无关系。
屋外是小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屋内是姐姐倔强的不服输,爸爸的打砸谩骂。
“爱德华,你知道恨是什么吗?”
“不知道,姐姐痛吗?我给你吹吹就不痛了。”
“嗯,我会保护你的,爱德华,姐姐希望你永远都不用体会恨所带来的一切,姐姐爱你。”
“我也爱你,姐姐。”
某一日,爸爸拿起木棍打肿了姐姐的腿,他站在门缝后惊恐的看着一切,用哭声阻止了接下来的惨象。
姐姐当时没有流一滴眼泪,她拖着腿带他藏在地窖里听着上头屋内的打砸与翻箱倒柜声——爸爸不知道从哪里得罪了很多人,妈妈走后,家里便一直是这样了。
然后,姐姐对他这样温柔的说道,他不明所以,但他知道姐姐是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的。
姐姐永远不会离开自己。
这日醒来后,爱德华从床上坐起来,距离姐姐接受初拥与血族身份已经有两月,他没有见过她一眼,也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
那些女仆与下人们嘴巴很紧,每当他问及这些问题,他们要不就是保密,要不就是转移话题,他逐渐感到厌倦与焦躁。
“我想你。”
“姐姐。”
他将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和曾为人时一样抽噎起来,只不过没有眼泪。
这样的日子反复过去,寂寞的洞在他心里一点一点的放大,完全吞噬他的仅存理智。
他想见姐姐,现在就想。
等回过神儿来后,爱德华满身是血的站在一座钟楼前,红色的门紧紧闭起,上方传来铛的悠长声响。
他愣愣的望着自己的双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抬眼伸出手推在门上,一脚踏上守门血族的尸体钻进钟楼。
“血族的应酬可真多,说吧,我还要忙活多久才能休息?”
“你刚刚就位,不可急于一时。”
“父亲说我不用遵守那些东西。”
“但我是你的礼仪老师。”
“唔,你还真是负责任,或许我该给你一些感恩?”
“爱丽丝小姐,安静。”
最高层的房间内,少女的笑声与男人平静的声音格外清晰,爱德华靠在墙上,垂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嘴角抿起,两边好似坠着砝码。
“我的弟弟还好吗?你究竟为什么不准许我见他?”
“他情况有些不对劲,隐先生希望我能在观察一段时间,确保他不会出现意外在让你去见他。。”
“我弟弟怎么了?”
“目前不清楚,你放心等待。”
“如果真是你说的不对劲,那我更应该去陪着他。”
“等等,这样太危险,我甚至没有找出他的异常……”
“是我求隐先生将他变为血族,也是我把他带过来,他一觉起来发现自己成了如今的模样,就算有什么不对,那也全是因为我。”
“爱丽丝。”
“我自己担着,祭司你可劝不了我呢。”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爱德华扭过头看着门口,少女从里面推开走出来,目光一下子就被他吸引过去,她愕然无措的站到他面前,抬起手颤抖着贴在他的脸上。
“爱德华,你怎么了?”
“我想你。”
“这些血…你……”
“姐姐,我想你。”
“……爱德华?”
“不要抛弃我,姐姐,我不想一个人。”
少女紧紧的跪下来抱住他,止不住的发抖呜咽,小少年呆呆地望向钟楼外飞翔的鸟儿,还有远处的日暮群山。
他伸手缓缓的搂住姐姐的脖子,空洞的笑起来。
如果这一刻能成为永恒,如果的话。
然而,别说永恒。
梦已经到了破碎的边缘,只差最后那一滴冰凉的雨,将它砸的七零八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