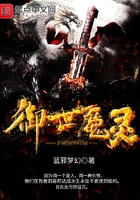设想一下,有一天你刚刚吃完晚饭,正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步,还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刚好够你吸完一支雪茄。你在心里盘算着今晚的活动,想着自己到底是去看戏剧呢,还是去看杂耍。突然之间,你感觉到一只手拍了拍你的胳膊,回头一看,正对上一双亮闪闪的眼睛。一个漂亮女人正站在你身后,满身珠光宝气,穿着华贵的貂皮大衣。只见她迅速往你手里塞了一个滚烫的奶油卷,然后亮出一把小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你大衣上的第二颗纽扣,大喊了一声“平行四边形”,然后撒腿就跑,麻利地拐进了一条小巷子,一边跑还一边时不时地回头看。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遇,你喜欢它吗?恐怕不会。你尴尬得满脸通红,手足无措,拿着那个奶油卷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扔到街边了事。你沿着百老汇继续走你的路,同时绝望地在地面上四处扫视,试图找回那颗丢失的纽扣。面对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你十有八九会是这种反应。除非你身上的冒险精神还未完全泯灭,你还称得上是一位冒险家,那么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说起真正的冒险家,这种人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人们总觉得世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英雄。随手翻开一本书刊杂志,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简直比比皆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真正的冒险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许多人只是徒有虚名,充其量只是手持各种新奇玩意儿的商人罢了。他们上刀山下火海,不过是为了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金羊毛[1]啦、圣杯[2]啦、公主啦、财宝啦、王冠啦、名誉啦,等等。而真正的冒险家则不同,他们只管出发,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刻意追寻什么,只是在不经意间邂逅了未知的命运。对此,我们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浪子回头”[3]的故事,特别是他决意回家的那一段。
至于半吊子的冒险家,我们手头倒是有一大堆。他们大多勇猛非凡,形象光辉,从十字军侵到哈德孙河边上的攀岩能手,这些勇士无疑给历史添彩,给小说增加了许多素材,顺带着也让文学市场繁荣了一把。但这些人总是有些别的目的,不是有丰厚的奖赏需要争取,就是有宏伟的目标需要达成;不是有盛大的比赛需要参加,就是有重要的消息需要传达;不是有尊贵的兵器需要磨砺,就是有伟大的决斗非要进行。他们总想让自己的名字千古流芳,所以说,他们追寻的都不是纯粹的冒险。
在这个大城市里,冒险总是和浪漫结伴而行,到处寻找着合适的对象。当我们在街上闲逛时,它们俩就偷偷摸摸地藏在某个角落里探头探脑,变幻莫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试探着我们。有时候当我们抬起头,猝不及防地发现橱窗玻璃上映出一张神秘而陌生的面孔;有时候我们走在一条静谧的大街上,突然听见一声恐怖的呼喊,感觉到一阵阴冷的气息从空旷萧瑟的老房子里传出来;有时候当我们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发现眼前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目的地,而是一扇陌生的大门,仿佛正微笑着等我们走进去;有时候,一张字迹斑斑的纸页从命运的窗口飘下来,刚好落在我们脚边;有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眼神交会之际,相互传递着憎恨、欢喜与恐惧的信息;有时候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我们撑开了伞,好心地遮在另一个陌生人的头顶,而在你伞下的,可能正是月亮的女儿、星辰的孩子。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地都会有一块手帕掉落在地,引来许多蠢蠢欲动的手指和迫切的目光,一场交织着遗失、孤独、爱恋、神秘、危险和动荡的冒险就此展开。但很少有人能够把握住机会,将冒险进行下去。我们已经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很久,早已磨平了棱角,变成了乏味的人,对种种诱惑视而不见,只顾埋头匆匆赶路。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走完了平淡无奇的人生,临终时躺在床上,开始回忆属于自己的故事。这时我们才发现,人生在世,我们的日子都花在了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面,比如常常为了一个坏掉的散热器而焦头烂额。诸如此类的琐碎小事吞噬了我们所有的时间,真正的浪漫却屈指可数,全加起来也不过是一两次婚姻,以及锁在抽屉深处的一块花手帕罢了。
鲁道夫·斯坦纳则与我们不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冒险家。几乎每个夜晚,他都会锁上自己公寓的大门,出去探索奇妙的大千世界。在他看来,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奇遇永远都在下一个街角等着他。有时候,他对冒险的狂热追逐也会把他引上歧路,让他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他曾经两次在警察局里过夜,也掉进过各种各样高明的骗局,有一次还被一个巧舌如簧的家伙骗走了金表和所有的现金。但他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每当命运向他挑战时,他总是勇于挺身而出。
有一天晚上,鲁道夫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闲逛。人行道被两拨人挤得水泄不通:一拨人步履匆匆,急着回家;一拨人正从家里出来,赶往灯火通明的俱乐部寻欢作乐。
而我们那位年轻的冒险家悠闲地踱着步子,不慌不忙地打量着四周。鲁道夫是一家钢琴店的销售员。他的领结很特别,别人都是用一根别针固定住,而他则别出心裁地在中间套了一只玉环。他还曾经给一家杂志写过信,和编辑讨论丽波女士那本《詹妮的爱情测试》。这本书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可谓是他的最爱。
走着走着,一阵猛烈的牙齿磕碰声传到了鲁道夫耳朵里,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声音是从路旁一个橱窗里发出来的,鲁道夫疑惑地看了一眼,然后就明白了。他面前有一家餐馆,旁边有一道门,一个招牌高高地悬挂在那儿,上面由霓虹灯管组成了“牙医诊所”几个大字,在夜色中明亮地闪耀着。一个高大的黑人站在路边,很滑稽地穿着一件红色的刺绣大衣和一条黄澄澄的裤子,还戴了一顶迷彩帽,正在那里向行人派发名片。
这种形式的牙医广告,鲁道夫见得多了。通常情况下,他会从那个发名片的人身旁快步走过,不给他任何递名片的机会。但这一次,那个黑人用一个出奇灵巧的动作,把名片塞到了鲁道夫手里。出于对他精湛技艺的赞赏,鲁道夫微微一笑,没有立刻把名片扔掉。
鲁道夫走出几码远,漫不经心地瞧了瞧手里的卡片。正是这一瞥,让他吃了一惊。他把名片翻转过来,颇有兴致地研究了起来。卡片的一面完全空白,另一面也只有两个字:“绿门。”鲁道夫抬起头,看见他前面两三步远的地方,有人把一张刚得来的名片丢在了地上。鲁道夫走上前,把那张名片捡起来,看见上面印着牙医的名字和地址,还有那些镶牙洗牙、无痛手术之类的常规介绍。
这事儿让我们这位富有冒险精神的钢琴销售员在街口停下了脚步,细细思量了一番。然后他过了马路,走过一个街区,再拐回来,隐在人流中重新经过牙医诊所门口。走到那个黑人身边时,鲁道夫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再一次接过那张递过来的名片。走出十步开外,他低下头看了一眼,发现上面依然用相同的笔迹,写着“绿门”两个字。鲁道夫周围散落着三四张被其他路人丢下的名片,都是空白的那一面朝上。鲁道夫把它们一一翻过来,上面无一例外都印着牙医先生的信息和丰功伟绩。
鲁道夫是冒险之神的忠实信徒,从来不需要它召唤第二次。既然它已经发出了两次邀请,那么,一场冒险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鲁道夫慢慢往回走,再次来到橱窗跟前,听见里面牙齿咯咯作响的声音,从路边站着的黑人身旁走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那黑人并没有递名片给他。抛开那一身花哨而滑稽的衣服不谈,这个埃塞俄比亚人其实风度不凡,他身上有一种粗犷而天然的气质。只见他庄重地站在那里,有选择性地发着名片,有些人走过去时他显得无动于衷,并且,每隔一会儿,他就咕哝几句难懂的话,听上去既像交通引导员在发指令,又像是在哼着某一段歌剧。鲁道夫这次没有从黑人那里接到名片,他得到的只是黑人那冷漠而轻蔑的一瞥。
这眼光刺伤了我们的冒险家,鲁道夫从那里面品出了谴责的味道。无论这神秘的卡片是什么意思,那个黑人已经在人群之中,两次选择了鲁道夫,而现在,他似乎又在怀疑鲁道夫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承担这项重任。
鲁道夫站在汹涌的人潮中,打量着面前这栋大厦,认定自己的冒险就要在那里面展开。这栋楼有五层,最底层是地下室,开着一家小餐馆。第一层大门紧闭,看上去像是一家经营女帽或是皮毛生意的店铺。第二层,根据那个闪光的大招牌来看,应该就是那家牙医诊所。第三层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识,勉强可以辨认出裁缝、音乐家、医生和占卜师的牌子。再往上就是最顶层,根据低垂的窗帘和窗台上的牛奶瓶子来看,应该就是住宅了。
观察完了之后,鲁道夫敏捷地跳上楼前那陡峭的石头阶梯,一口气跑上两层楼梯,然后停了下来。门厅里很昏暗,只有一远一近两盏微弱的灯光。他看着左手边离自己较近的那盏灯,发现在它昏黄的光圈下,赫然就是一扇绿门。他犹豫了几秒钟,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个黑人轻蔑的冷笑。他终于下定决心,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等待门开的这段时间,最能凸显出一场冒险的紧张和神秘。谁知道这扇绿门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也许是一群疯狂的赌徒,也许是正在等待猎物上钩的骗子,也许是一位坐等勇士前来共浴爱河的美人。危险,死亡,爱情,失望,玩笑——这鲁莽的敲门,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事件。
门内传出一阵轻微的响动,然后那扇门慢慢地开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站在门后,脸色苍白,摇摇晃晃。她松开门把手,一个踉跄就要往下倒,一只手还无助地摸索了一下。鲁道夫赶紧扶住这姑娘,把她抱到靠墙的沙发上。他关上门,在闪烁的煤气灯下环顾四周。屋里虽然整洁,但处处都显得极为贫困。
那姑娘无声无息地躺着,好像是晕了过去。鲁道夫扫视着房间,想找找哪儿有一只大桶,好把人放在上面滚动滚动——噢,不对,不对,那是给快淹死的人用的。于是,他开始用自己的帽子给姑娘扇风,这一招见效了,因为他的帽檐撞上了姑娘的鼻子,把她弄醒了。她睁开了眼睛,那张脸完全就是鲁道夫朝思暮想的容颜——真诚的灰色眼眸,小巧而上翘的鼻子,棕色的头发像豌豆藤那样打着卷儿。这简直就是对他此次冒险的最佳奖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张脸消瘦得可怕。
那姑娘平静地看着鲁道夫,然后笑了。
“我晕过去了,对吧?”她虚弱地问,“三天不吃东西,你也会的。”
“啊?”鲁道夫叫道,跳了起来,“等着,我马上回来。”
他冲出门,奔下楼梯。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怀里满满的都是从杂货店和餐馆买来的东西。他踢开门,把东西都放在了桌子上。有面包,黄油,蛋糕,馅饼,泡菜,牡蛎,一只烤鸡,一杯牛奶和一罐红茶。
“三天不吃东西,这简直太荒唐了!”鲁道夫吼道,“再也不许这样乱来。快来吃晚饭。”
鲁道夫把那姑娘扶起来,让她在桌子前坐好。
“这里有茶杯吗?”
“在窗户旁边的那个壁橱里。”
鲁道夫拿着杯子回来,看到那姑娘正兴高采烈地从一个纸袋子里掏莳萝泡菜。他笑着,从姑娘手里把泡菜拿开,给她倒了一杯牛奶。“先把这个喝了,”他说,“然后再来杯茶,吃点鸡翅。明天等你好一点了,再吃泡菜也不迟。现在,如果我有幸可以成为你的客人,就让我们一起吃吧。”
鲁道夫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杯热茶下肚,姑娘的眼睛明亮了起来,脸上也恢复了一点血色。她不失优雅地向食物发起了猛攻,仿佛一只饿了很久的野兽。她很自然地接受了眼前这个男人和他带来的东西,这并没有什么失礼之处,因为任何一个饿肚子的人都有权把一切虚伪的客套抛到一边。但随着体力的恢复,吃饱的感觉让她倍感舒适,言行举止也就得体起来。她开始向鲁道夫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外乎是个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故事,人们听不了两句就会打哈欠。作为一个商店店员,她的薪水本就少得可怜,还总是被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克扣,最后都进了老板的腰包。后来,她又生了病,丢了工作,丧失了所有希望,然后就有一个陌生的冒险家来敲自己那扇绿色的房门。
但在鲁道夫眼里,这故事几乎和《伊利亚特》[4]或《詹妮的爱情测试》一样曲折离奇、惊心动魄。
“你的生活真是太艰难了。”他叹了一口气。
“这些经历的确让人痛苦。”姑娘严肃地说。
“你在纽约就没有亲戚朋友吗?”
“没有。”
“我也一直是一个人生活。”鲁道夫沉默了一下,说道。
“噢,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姑娘迅速答道。不知为何,这话让鲁道夫很开心。他觉得这姑娘很欣赏他的生活方式。
突然,姑娘垂下眼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觉得很舒适,”她说,“有点困了。”
于是,鲁道夫站起来,拿着他的帽子,说:“那我就告辞了。安稳的睡眠对你有好处。”
他跟姑娘握了握手,但对方的眼神是那么坦率而迫切,看上去楚楚可怜,让他不得不继续说:
“我明天还会再来看望你的,别想这么容易就摆脱我。”
当鲁道夫走到门口的时候,姑娘终于开口问他:“你为什么会来敲我的房门?”但姑娘的口气表明,既然他已经在这里了,理由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鲁道夫看了姑娘一会儿,想起了那张卡片,一阵妒意涌上心头。要是这些卡片落到其他冒险家手里会怎样呢?他迅速打定了主意,永远也不告诉姑娘实情。他永远不会让她知道,自己很清楚她的所作所为。她在贫困的驱使下,不得不耍这些奇怪的把戏,他对此了然于心。
“我们店里的一个调音师住在这栋楼里,”鲁道夫最后说道,“我来找他,但敲错了门。”
在大门关上之前,他最后朝屋里瞥了一眼,看见那姑娘在朝他微笑。
走到楼梯口时,他停了下来,好奇地四处看了看。他朝门厅的另一头走去,然后又折了回来,上了一层楼,继续探查了一番。然后他震惊地发现这栋楼里每扇门都是绿色的!
鲁道夫迷惑不解地走下楼,来到大街上,那位神奇的黑人还在那儿。鲁道夫把两张卡片都拿在手里,朝黑人走去。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给我这两张名片吗?还有,这上面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问。
那个黑人微微一笑,拿出一张巨幅海报给鲁道夫看。
“就是这个,先生。”黑人一边说,一边指着街道那头,“不过,恐怕您是赶不上首场演出了。”
鲁道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剧院入口处那鲜明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今晚的最新节目——“绿门。”
“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是超一流的节目,”那位黑人说,“代理商塞给我一美元,让我在牙医的名片里夹几张剧院的宣传卡。我给你的就是那个,对吧?”
鲁道夫走到他居住的那个街区,在街角处停了下来,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根雪茄。然后他从店里出来,嘴上叼着烟,扣好自己的大衣的扣子,对着灯柱坚决地说:
“这些都无所谓。我相信是命运之神指引着我,让我找到了那个姑娘。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
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这句话彻底证明了,鲁道夫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冒险家,坚定地走在浪漫与冒险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