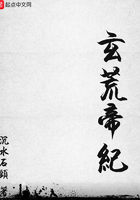卧床七八天后,绯儿终于下床了,这期间幸好有碧儿和沈妈周旋着,舒夫人才没有发觉,不过,舒夫人被另一种愁绪完全占住了心神,忧得她竟然消瘦了一圈。
“老爷,你说碧儿嫁到飞天堡,哪里会做个夫人呀?这些年,我什么都没教她,女儿家该会的她一样都不精。”她忧心仲仲地对舒富贵说。
舒富贵没好气地一甩袖,“你问我我问谁去?那个君堡主就象是瞎了眼,唉,他真的该见见绯儿的。”事情过去一些天了,他仍不能忘怀。
“现在说有什么用呢?婚期都定了。不过再想想碧儿都能嫁这么好,绯儿一定差不到哪里去,不知道韩少爷会不会中意绯儿?”舒夫人悄悄盘算着。
舒富贵脸皱成一团,没有作答。他也这样想过,可是不知怎的,他有种预感,绯儿这丫头象时运不济,不然煮熟的鸭子怎么都飞了呢?
绯儿闭上眼,仰起脸,深深地呼吸着清冷的空气,任冬日的暖阳洒在身上,她的心情可以说是还不错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坠了胎,又巧秒地让碧儿替她应下了婚事,她终于可以一身轻松的等着心中的那个人凯旋归来了。
当他得知她为他放弃了什么、又吃了这么多的苦,一定会比从前更爱她的。想到这里,绯儿脑中浮出一张英武的面容,嘴角不知觉绽开了一丝娇媚的笑意。
“舒夫人,小的是飞天堡的家仆,奉堡主之命,特地来接二小姐到堡里做客。”
绯儿听到大门内传来几声马啼声,扭头一看,一辆华丽典雅的马车缓缓停在舒园外,两个衣著光鲜的男子和一个侍女跳下车,对着舒夫人恭敬地行礼。
她的好心情象被一阵风吹走似的,荡然无痕。马车上的镶金饰银,象一根刺,狠狠扎在绯儿的心口,泛着莫名的痛。一种属于女子本能的妒忌从心底泛上,她撇撇嘴,转身往碧儿的厢房走去。
碧儿白着一张脸,头发随意扎成一束放在身后,穿着舒夫人一件半旧的青色棉袍改成的棉裙,倚在门边,半面身子在阳光里,半面在屋内,表情也象是一明一暗。
“碧儿,你下辈子作牛作马,都还不了我对你的恩德。若不是我把君堡主让给你,你能嫁得了这么好吗?”绯儿酸酸地白了碧儿一眼,杵在门外。
碧儿漫不经心地瞟了瞟她,“我不稀罕,你若后悔,现在还来得及换过去,不是还没成亲吗?”
“我才不会象你那样无耻,言而无信的。我大仁大德,好事做到底,不过,日后我要求你做什么,你半点都不准拒绝。”
“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你还是少开尊口。”碧儿滴溜溜的大眼发怔地不知看向何处,不怎么费心地应付她。
“你敢?你不怕我把你厚颜无耻自己跑去要替嫁的事抖出来?”绯儿杏眼圆睁,一张脸都涨红了。
“哈,你讲得我真怕!”碧儿打了个哈哈,转身进屋,不愿与她争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舒夫人象个肉球滚了过来。
“娘亲,怎么跑得这样急?”她走下台阶,扶着舒夫人,按抚着她气喘喘的后背。
“快,快,去涂点胭脂,抹个唇红,换件衣衫,君堡主派人接你到飞天堡做客。”
碧儿莫测高深的拧着眉,这个君问天要干什么?她不会白痴地理解他是想和她搞好关系,以便于婚后好好相处。想想都是好委屈,她连恋爱都没谈过,现在却要结婚了,而且是嫁给那个阴魅诡异邪恶的君问天。虽说婚约有期,但几百个日子,只怕人未老,就花落人亡两不知了。
“你在发呆什么,快进去呀!”舒夫人急得差点蹦出来。
“不换,我就这样子。”她想说君问天看中的是红松林那块地,又不是她这个人。她扮得象朵花似的,他也不会多瞧。再说,女为悦已者容,他还不够她为他对镜贴花黄的资格。
“可你这样子,连个使唤丫头都不如,怎么见人?”
“不怕,再不如,也没人敢对我大呼小声,我不是飞天堡的未来夫人吗?越是低调到越显得出我的不凡。打扮得漂亮又什么用,丫头就是丫头,能不成还能飞上天?”她示威地斜睨着绯儿,绯儿一张俏脸突地就铁青,碧儿优雅地一笑,背挺得直直的,往前园走去。
“一定要象个大家闺秀,说话要慢点,走路要看着,千万不能闯祸。”舒夫人不放心地追在后面叮嘱。
碧儿笑,如果君问天惹恼了她,有必要闯个小祸也不错。
“舒二小姐好!”三个家人礼貌地问候,碧儿上车时,很不小心地看到跟来的小侍女不屑地冷冷一笑。
轿帘一拉,轿内瞬时暖了起来,坐在厚厚的羊毛毡子上,侍女麻利地递过一个手炉,在她的膝上盖上一条狐裘。
碧儿抿了抿唇,她穿旧袄,盖狐裘,也太不搭了吧!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很斯文有礼地问。
“春香,是堡主夫人起的,哦,是故世的堡主夫人起的,小的原来叫青格,夫人说不雅气,就改了名。”侍女扬着个尖下巴,脆脆地回话。
碧儿瞪大眼,“那是不是还有谁叫秋香?”
“二小姐怎么知道?”春香惊道。
碧儿咂了下嘴,“飞天镇上有姓唐名伯虎的公子吗?”
“好象没有。”春香皱眉,想了好一会,摇摇头。
“真是可惜了。”要不然,就是一出连续剧了,唐伯虎点秋香。雅气的名字,碧儿浅笑。“春香,你是不是很崇拜你家夫人?”她慢条斯理地问。
“嗯,在这世上,没有哪一个女子有我家夫人那么美、那么聪慧了。”春香抬头,看到碧儿淡然的神情,一愣,察觉失言,“小姐,我的意思是……”
“我懂,可惜天妒红颜,那种几百年才会出现的大美人连天公都会喜欢上,凡人是无福消寿。”
“对,对,夫人曾经说,她只要挑一下眉,这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会臣服在她的脚下,可是她正眼都不愿瞧他们。夫人开心的时候,就会给我和秋香讲一些男人看到她出糗的事,想想真是有趣得很。”春香把碧儿误作了知已,津津乐道起来。
碧儿小嘴半张,然后缓缓闭上,星眸微荡,呵,确是很有情趣,君问天有这样的夫人,一定不会太寂寞,不知那位夫人看君问天时,是用哪只眼?
马车穿过宽大的车道,停在飞天堡正厅前。一溜子家仆列队迎候,君问天没什么表情的站在廊下,看到碧儿倾了倾嘴角,象是硬生生把惊讶咽了下去。
“路上还好吗?”他问,等着她走近。
“我觉得走过来会更暖和。”碧儿把手炉还给春香,跺跺发麻的脚。
“好,那下次我走着去接你。”他伸出手欲牵她的,她刚好打量一园的冬景,错过了他的伸臂,他借势环着她的腰,“我带你参观一下飞天堡,过一个时辰,该用午膳了。”
“让春香陪我就行了,你忙你的吧!”她的身子在他的掌下一僵,不自在地说。
“我今天没别的事。”君问天收回手臂,低头看她泛红的面容,浅浅一笑,领步向前。
左一进厢房,右一进楼阁,前一个院子,后一个园林,君问天非常细心地讲解着,每一间房、每一座院,都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可碧儿瞧着就是一堆花团锦簇的华丽,没什么区别。她唯一加深的印象就是飞天堡富得其实,毫不夸张。
“从这里就会到达后面的湖泊。”他们走过一个硕大的园林,弓着腰钻过一个拱形的小门,碧儿发现自己正站着一个狭小的河湾上,脚下是坚硬的白色圆石,她听到了湖水拍打岸畔的声音。
景色的骤变,让碧儿惊得失去了呼吸。冬日的湖水深邃得令人心悸,映着岸边的树林,越发深不可测,她不禁打了个冷战。
“说来好奇怪,不管下多大的雪,天气冷成什么样,这湖都不会结冰的。”君问天拾起一块石子,丢到湖水里。
“可能湖底有暖泉。”碧儿轻轻退后几步,象是害怕会不慎跌下去似的。
“明年三四月,春暖花开草青时,你可以到湖上坐船游玩,和你喜欢的朋友,吹笛弹笙,喝酒狂欢。”君问天俊容突地抽搐了下。
“这是你喜欢的方式还是尊夫人喜欢的方式?”碧儿怕冷,环着肩,走到后面的树林中躲风。
“你不喜欢?”君问天有些羞恼,眯细了眼,脸色苍白。
“在这之前,我没尝试过,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她耸耸肩,听到远处传来赵管家的喊叫。“堡主,堡主!”
君问天不耐烦地回应,“我在这!”
“堡主,拖雷王子派哲别将军来提运铸造武器的铁块,还有些事情要和堡主商量。”赵管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哦!”君问天一挑眉,长袍一甩,抬步就进了拱门,赵管家紧随其后。
碧儿眨了眨眼,他是故意还是无意忘了她的存在?啊,人微身也轻,商人重利轻别离,前一刻还谦谦君子样,斯文多礼,这一刻就露出势利的嘴脸了,若是换作他的大美人妻子,他也会这样走开吗?
不过,她不在意,君问天不在身边,她才可以轻松地欣赏一下四周的景色了。和那种吸血鬼一样的冰人走在一起,什么好心情都会冻住的。
她沿着小河湾,慢慢地走着。如果不带有成见,这飞天堡真是一个度假胜地。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就连这大冬天的,也有一番壮丽的美景。
岸边的树林越来越密,阳光被挡在上面,射不进来,光线突地昏暗,四周一片异样的沉寂,碧儿屏气凝神,走了好一会,才走出树林到了草坪上,望见屹立着的那一幢幢坚实牢固的楼阁,心头一阵喜悦。
围墙边一扇高大的木门半敞着,那应是通往正厅的后门吗?
碧儿抬脚,正准备走过去,忽然听到门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她本能的退到一棵大树后,屏息伫立,一动也不敢动。
“新夫人是个美人吗?”低柔如丝绒般的温柔的华丽男音。
“美人?她下辈子再重修吧,一幅寒酸像。堡主若不是为那块地,会看上她?”这是早晨去接她的春香的嗓音,尖利带着脆。
“你是不是很妒忌?你日日侍候莲儿,怎么就没学会莲儿半点本事,不然正夫人做不着,小夫人也该临到你了。”
“我才不稀罕,表少爷不要拿我开心了。我给你拿点你爱喝的贡酒去。”
“春香好乖!”
“表少爷你真坏。”
话语声没了,碧儿听到衣衫的摩搓声和重重的喘息,脸儿突地一红,想从原路走回。
“啊!”门里突然跑出一条黑色的大狗,飞快地朝她站着的树边扑来,碧儿吓得大叫出声,脸唰地就白了。
“阿奴!”一个紫袍男子跨出木门,正对碧儿一双惊恐的大眼。她从未见过有谁露出那样的满脸惊讶之色,仿佛她是天外来客。
大狗欢跳着回到男子身边,围着他兴奋的直摇尾巴。
“请你原谅,你吓着了吗,二小姐?”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脸上慢慢挂起微笑,那种会丢给任何女人的耍帅的微笑。
唐伯虎没来,周星驰来了,碧儿心中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紫袍男人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脸膛黑里透红,英俊之中颇带几份流气。他生着一对顾盼风情的桃花眼,那种眼睛往往使人想到纵情声色,眼袋很大,显然夜生活过度,身上隐隐还散发出一股隔夜的酒气和脂粉味。
碧儿从树后走了出来,很诧异这个男人认识她。
“但愿阿奴没有吓着你。”紫袍男人又说,“不然问天该责怪我了,初次见面,就惊着了他的美人儿。”
这男人讲话的腔调不禁使碧儿暗暗吃惊,听上去好像他和君问天很熟悉。“哪儿的话,当然没有吓着。我只是迷了路,以为这儿可以走回正厅。”
“当然可以走回,天,”紫袍男人做作地瞪大眼,露出自以为是的迷人笑容,“这群下人真是胆大了,竟敢把二小姐一个人丢在堡外。如果二小姐不介意,我带你回正厅可好!这飞天堡,我闭上眼都能分辩出哪座庭院、哪间房。”
“哦,那就麻烦公子了。”碧儿无由地讨厌这个男人唐突无礼的语调,还有他看着她的眼神,象穿透她的衣服似的。
“表少爷,酒来了。啊,二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春香捧着个酒壶,直愣愣地盯着碧儿。
“春香,你来啦!你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快来替我介绍一下?”紫袍男人暧味地对春香挤挤眼。
“二小姐,这位是堡主夫人的表兄潘念皓公子。”春香面无表情地说,语气相当勉强,碧儿觉得她并不情愿把他介绍给自己。
“你好!”碧儿现在的万福礼已经行得非常熟练了,她优雅地盈盈欠身,为了不显得无礼。
“好了,春香,现在我和二小姐已经认识了,你先忙去吧!哦,酒,我吃午膳时再喝,现在陪二小姐要紧。”
碧儿看见他朝春香丢了个抱歉的眼色,春香眼睛里快冒出火来了,瞪了碧儿一眼,身子一扭,气呼呼地跑走了。
是不是气她坏了他们韵事?碧儿如是想。
“二小姐,你需要我带你逛下飞天堡吗?”潘念皓用亲昵而又唐突的语调问。
“不了,君堡主刚刚已带我逛过。”她生硬地回答。
他们一起穿过甬道,走进门廊,在一个空落的厢房前,潘念皓瞧四下无人,突地把两只手臂撑在墙上,将她圈在里面。
碧儿眨眨眼,幸好他长得不象周星驰,不然她真以为周星驰也穿越了。这动作典型的周星驰的招牌动作——搞怪、滑稽,她很好奇他到底要干吗?
潘念皓看碧儿没有惊叫,胆大了起来。
“二小姐,知道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感觉是什么吗?”他抓住她的手,亲亲热热地把玩着。“你让我惊艳,眼前一亮。你的美不是那种庸脂俗粉,你美得很有个性,卷发亮眸,肌肤如雪,高挑修长,如果把发打散了,披在光洁的肌肤上,那将是一种狂野得无与伦比的美,会让男人发疯的美。”
说完,他歪着头,闭了闭眼,等着她的反应。
碧儿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轻笑,“潘公子,你需要我做出哪种表情来配合你这番话?”这只乱展翅的公麻雀,自恋成什么样了,她真佩服他胡谄的本事还有狂妄的本领,这里是飞天堡,她怎么说也是君问天的未来妻子,他竟然敢对她说出这种话,难道他以为每一个女人都逃不过他那双桃花眼?
“你的什么表情,我都会心动的。”
这男人脸皮真不是一般的厚!碧儿微笑地瞪着他放肆地握着她不放的手,突地一挣脱,迎脸就是一巴掌。
掌声在空荡的庭院中回响着。
潘念皓眼一眯,捂着脸,腥红的舌缓缓舔了舔唇角,眼中闪出兴奋的光泽,“二小姐,你这样我更难忘了。知道吗?你挑起了我的兴趣。在这飞天堡里,只要我想,没有一个女人舍得反抗的,就连莲儿也一样在我身下欲生欲死。你没尝到那种滋味,尝过一次,你就会跪着哭着求我抱你的。我喜欢你的野性……”他突地喑哑了嗓音,用力地按住碧儿的双臂,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他淫笑地缓缓俯下身,“君问天还没尝过你吗?哈,处子的清香真令人神迷,那我就不客气了。”
夹着酒气的男子气息渐渐拂上脸颊,碧儿不悦地蹙起眉,罢了,是他先无礼的,就别怪她不客气了。她突地一抬脚,对着男子的小腹狠狠踹去。虽说不是美女,但防身术,她可是也学了一点点,以防不测,现在还真派上用场了。
潘念皓没有设防,当然,更是没有想到,一个后仰,狼狈地直挺挺地倒下,跌得眼前金星直冒。“你这个疯丫头……。”他迅速爬起,朝着碧儿扑了过去。
碧儿拎起裙摆,灵巧地在廊柱间窜来窜去,潘念皓瞪着血红的眼,大概体力在风月场上消耗尽了,不一会,就气喘吁吁,脸红得象个血泡。“给我站住,丑丫头!”他怒吼着,扶着廊柱,气快及不上来了。
碧儿好整以暇地跳到最边上一根廊柱,俏皮地对他一吐舌,扮了个鬼脸,“大情圣,原来你就这么点本事呀!想碰我,你省省吧!莫谈你一个,两个本小姐也不怕的。看在你是堡主夫人亲戚的面子,我今天先不计较。以后见到我请放尊重些,不然我对君问天说,让他把你列为拒绝往来户。”
“哼,你以为君问天会听你的?”潘念皓狞笑着,喘个不停。
“难道听你的?”碧儿捉侠地一笑。
“告诉你,君问天很习惯戴绿帽子的,你若太贞节,他会不习惯的,哈哈!”潘念皓前俯后仰的大笑,“他以为找了你这么个祸害精,你会无人问津,谁知道你这么惹火,我一样有兴趣。”
碧儿怔住了,“你可以把话说清楚吗?”
“听不懂?”潘念皓一挑眉,“不懂就算了,不过,告诉你一声,我可是君问天今天特地请过来陪你吃饭的。”
碧儿脸色一下就变了,她咬了咬牙,一言不发地突地转身,不顾潘念皓在后面高呼呐喊,进门就见,进院就转,七拐八拐,让她竟然转到了正厅前,还没跨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争论。
“问天,你真是疯了,怎么能娶那个祸害精呢?我上次去舒园,一见到她,就被她的秋千架撞得鼻青脸肿。若是让她进飞天堡,你日后只怕没好日子过,我和你大嫂你觉着你应再三思而后行。”
“呵,大哥你不必再说,我已经考虑好了,婚期都定了,你这次回来就不要再外出,留在堡里帮我准备婚事吧!”
“问天,大哥没和你开玩笑。那块地再好,也犯不着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呀!这堡主夫人,怎么得也该选个闺誉良好的小姐呀!”
“我觉得二小姐就很合我的心意。”
“你真是病急乱投医。”
“说不定这乱投的就能治病。”君问天凉凉地说。
碧儿在外面,止不住的想冷笑。这飞天堡里住的都是些人吗?她好怀疑。
“二小姐,站在外面不冷吗?”赵管家象个幽灵似的,不知从哪里突地冒了出来。
“不冷,我热着呢!”碧儿特地提高了音量,厅中的议论声一下消失了。
赵管家抬头看看被一片云彩遮住的太阳,皱皱鼻子,他怎么就觉得这么冷呢?
“碧儿!”君问天跨出大门,淡然一笑,“正准备去接你呢,能自己找回来,看来你已经对飞天堡很熟悉了。”
“熟悉谈不上,有你请来的好向导,我怎么可能找不回呢?”她讽刺地瞪着那张俊美的面容,真是替他可怜。
君问天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大哥。”他作势要牵她的手。
碧儿甩开,扭过身,走进厅中,君仰山青着脸,难堪地对她拱拱手。碧儿轻蔑地一笑,自顾坐下。
“问天,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府。”君仰山不自在地瞟了碧儿一眼,心想刚才的话一定会被她听到了,不好意思再呆下去。
“哦,君大少慢走,请代我向少夫人问好。”碧儿忽然笑魇如花。
君仰山和君问天都一怔。君仰山讷讷一笑,“好,我替贱内谢谢二小姐关心了。”说完,他低头走了出去,赵管家看看碧儿的神情,摸摸鼻子,也悄然走向后堂。
君问天默默地坐到碧儿的面前,冰冷的面容稍稍开颜,“是在气我刚才没顾上你吗?”
碧儿抬眼,对着他扁下嘴,“我们有那种交情吗?君堡主。”他又不是韩江流,看着他,越发体会到韩江流的好,心中不由地一阵酸涩,眼眶突地一红。
“我不是娇气的小姐,扔在哪里都不会丢掉。君堡主,请问你对我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呃?”君问天讶异地一挑眉。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自已?真的替你感到悲哀。好了,君问天,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好奇了。反正以后的一两年,你我和平相处,井水别犯河水。关于那个名义上的堡主夫人,我明里暗里都不会给你丢脸,你不要花心思再找人试探我了。那种事,实在是对我的侮辱,让我觉得恶心。飞天堡我参观过了,现在,我要回去了。不要找人送我,我自己走。”她一口气说完,腾地站起身,就往厅外走去。
“碧儿!”君问天冷凝地伸手抓住她,“你到底在讲什么?我确实有急事要处理,不是故意丢下你的,更不是试探。”
“不要解释,我不想知道。”她挣扎地想抽回手,他紧紧地抓住。“赵管家已经吩咐厨房为你蒸了熊掌,煮了鹿肉,还煎了猴脑,至少也得用完午膳再走。”
“飞天堡有多富有,你无需特别说明。不过,我要提醒你,那种国家珍稀动物,别顾着吃得痛快,当心蹲大狱。”
“什么珍稀动物?”君问天一张俊脸冷得慑人。
碧儿眨巴眨巴眼,抿紧唇,小脸拉得长长的。她又忘了身在何处,一种挫败感就象狂袭的巨潮把她整个人都吞没了。“君问天,如果可以,真的好想悔婚。”她嗫嚅低语。
“是吗?”君问天冷冷一笑,“我记性不算太好,可还是记得当初这婚约可是你主动提的。”
“所以才说如果可以,因为这是不可以的。”她沮丧地抬起头,肩耷拉着,黯然打量着窗外一幢幢楼阁,一簇簇树木丛林,这里每个人都好象不太正常,富丽背后都象隐藏着诡异,传说那么多,人与人之间很复杂,她真的要在这里度过两年吗?
如果对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当去旅游。她就把这二年,当成去了海外战场,做了回战地记者吧!做堡主夫人一定不会比做战地记者艰辛。想到这里,她又自信满满。
“君堡主,以后请多关照了!在婚礼之前,我们就别挑战世俗,不要见面为好!洞房花烛夜见了。”她扫了他僵硬的俊容,闭了闭眼,算是招呼过了,纤细的身子一转,抬脚出了大厅,象放飞的鸟儿,欢快地跑出他的视野。
君问天追逐着她的身影到厅外,伫立,呆愕。
他觉得某种情形超脱了他的掌控,他很想扔开,却又有些无能为力。
紧闭的心扉象被谁砸开了一条缝,往里嘶嘶吹着风,他不禁轻抽了一口凉气。
一匹高大的红马突然出现在车道上,越来越近,马上一位俊雅的披着灰狐斗蓬的公子笑吟吟地跳下马,“君兄,你我莫非有灵犀,知道我今日要来,特地在这里等候吗?”
“江流!”君问天一喜,慌忙迎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