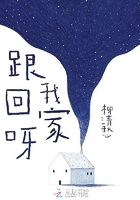(因本章字数过多,遂分两次更新,以下内容为《39上》的下半部分。)
父子两正商议着明日庆生的事儿,忽地仔仔手机响了。
“我奶奶的视频电话!”仔仔对爸爸轻声说。
“喂,奶奶!”接通电话以后,仔仔兴高采烈地回房去和奶奶单聊。
手机里的老太太用一口纯正的湖南话问孙子:“仔儿!你最近补课补得怎样呢?”
“就天天上课呗!一周六天,晚上休息。”仔仔躺在床上笑嘻嘻的。
“是不是又要过生日了?”仔仔奶奶瞅准时机打来电话。
“嗯……”少年挠头憨笑。
……
祖孙两个在屋子里聊得喜庆,客厅里翁婿两却冰冷无话。致远摸不懂便去忙家务了——擦洗餐桌上的茶渍饭粒、粘沙发上的头发、哄漾漾睡觉、烧热水存热水……老马瞄他来来去去的身影,心中渐起了一团湿火。
仔仔和奶奶聊完后,老太太给孙子发了个大红包作生日礼物。仔仔收了红包嘚瑟得如两脚踩在弹簧上一般,跟在爸爸身后大呼小叫地聊着奶奶。父子两又坐下来等她妈回来一块商议明天过生日的事儿,谁想过了十点桂英还没回来。仔仔见妈妈一直没回,扫兴地回房了,致远于是又在干家务。
老马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忍不住地瞅了几眼,瞥见女婿两脚飞快地在家里穿来穿去。先是晾晒洗衣机里洗好的衣服,后来整理客厅的书架和门口的鞋架,接着匆忙地收拾漾漾撂在客厅里的玩具……老马心中叵烦,巴不得自己此刻在马家屯里——耳根清净、两眼不烦。
致远大汗淋漓地在客厅里扫地拖地的时候,桂英回来了。老马一看手表,已经十点半了。城里的工作不是靠脑子靠嘴巴吗?怎么靠脑子靠嘴巴的工作还要忙活到大晚上十一点——老马纳闷。
“哎呀,亲爱的,累死我了!我回来开车一路地打哈欠!”桂英一回来直奔何致远,而后在客厅里大大方方地从背后搂着何致远的肚子。
老马一肚子火气碰上了冰块,老农民羞得赶紧别过头去不敢看了。
“爸在那呢!”致远小声提醒,然后挣脱了桂英的怀抱。
“你媳妇抱你——怕啥呀?”桂英说完瞅了眼老头,大步朝客厅走来,而后咣当一声倒在沙发上——横瘫着。
“哎呀累死我了!今天白天跑了两家客户,到手一家,但是规模很小,订的展位也很少!晚上一个业务员要离职,跟他聊了很久,然后请他和几个业务员一块吃了个散伙饭,路上累得我都不想回来了,我想着直接在车里睡一晚明天肯定有精神!”桂英横在沙发上,两脚高高翘起来。
“妈,你明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呀?”仔仔听声知妈妈回来了,出了屋也来到客厅里。
“明天……我不知道呀!最近走了好多客户,又烦又忙……日子不好过呀!今年后半年的提成估计要歇菜了!”桂英浑身无力地说。
致远放好拖把换了双干的拖鞋也过来了,他坐在了桂英头枕的沙发扶手上。
“没事,你忙吧,我和我爸定好了明天的饭菜,明天说不定晓星姨姨也过来!”仔仔坐在爷爷身边安慰妈妈。
“哎……”桂英长叹一口气,回头看着致远说:“亲,帮我按按脖子,我肩膀、脖子僵了一天,又酸又胀!最近耸肩都耸不了——这块全是硬的!”桂英指着地方,致远伸出两手来给老婆按肩膀。
老马默默地白了一眼,憋着气不说话。
“哎对了,冰箱坏了,应该是调控的问题!我爸不会弄,晚上我打客户电话人家下班了,妈你待会看一下,明天蛋糕来早了可能得放进冰箱里。”仔仔一边看手机一边对桂英说。
“你妈都累成这样了还修什么冰箱!”老马咧了咧嘴说。
“呃……我现在去修!”桂英鼓了一口气硬是起了身,父子两跟在其后,走到冰箱那儿,桂英按照以前说明书里的方法在尝试。
不工作不赚钱也就算了,水管不会修、灯泡不会换,现在冰箱坏了也指望婆娘回来弄!老马沉了一口气,心里暗忖:赶紧走赶紧走!再待在这儿指不定气出啥毛病来!
几分钟后,桂英调好了冰箱温度,三口子又一伙过来了,原样坐在沙发上,致远继续给桂英按肩膀、揉脖子。致远和仔仔许是未察觉到老头的脸色,桂英扫了一眼早知他不高兴了,她也不问,自个跟老公孩子聊自个的,懒得理会老头那摊怨事。
十一点半,仔仔回房睡觉,致远收拾屋子整理床铺,桂英躺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你累了回房睡去!明天还要上班呢!”老马对桂英说。
“嗯。”桂英半睡半醒里轻哼一声。
老马见她没睡着也能听见,于是正经威色地开口说:“你一个女人家天天在外面跑,他个大男人天天关在屋里不见人!这叫什么事儿!一个男人不踏入社会怎么混?哎我都担心他时间越长越难融进社会。我待了两月就没见他跟什么人说过话——他的社交圈还没有漾漾大!他不能永远不见人对不对?有老婆孩子就得养家不是?不能总让一个女人养着呀!养了四五年了还要养多久?难不成让你一个婆娘家养他一辈子!你乐意我可不乐意!”
反正自己要走了,不说白不说,也不挑挑拣拣了,老马直说他最想说的话。
桂英蓬头散发地艰难地坐了起来,两手抱胸,凝视老头,怕致远听见她刻意压低嗓子说:“我说了一百遍了,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你以为他乐意辞掉工作吗?他现在在写小说,在努力,在调整,你没听过中年危机这个词吗?”桂英说得激动,左手握拳不住地捶沙发。
老马合住扇子,坐直身子道:“狗屁个中年危机!矫情!明明是性格问题、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扯什么中年危机!哪有中年人四十来岁在家里带娃一带带了好几年的?我是替你着想,你还替他说话!你一天到头能陪漾漾多久?娃儿天天晚上巴巴地等着你,有几回是她没睡你回来了?你算算你一周能陪她几天?他现在四十五了不工作几岁工作?五十岁还是六十岁?我一说他你就急一说他你就急,四十岁人了分不清好歹!”
父女两压低声音在客厅里吵嘴,致远早觉察到了,虽听不清在说什么,但猜测肯定是与自己相关。
“我家里的日子我乐意这样过,行不行?你要走了还说这个干什么?”桂英瞪着老头问。
“哼,你乐意我不乐意!只要我在,我就要矫枉过正,把这个掰过来!哼!”老马双手抱胸看着左脚。
“下周你就不在这啦,说这个有意思吗?”桂英说完抱着胸气呼呼地回屋里了。
“哼!”老马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口,他在客厅坐了许久,待微微平静了才回房睡觉。
桂英晚上睡下后,本是一碰枕头立马睡着,被老头这么一说,怎么也睡不着了。不知道是自己习惯了又忙又累、早出晚归还是真觉得女主外男主内的结构无所谓,亦或是她潜意识里早已把养家糊口当成了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业务好也就罢了,只是近来退展的太多了,公司上下人人自危,个个传言下半年的展会要大亏损。若真是亏损了,她这个业务经理必然是首当其冲。怎么办呢?桂英唉声叹气地无法入睡,工作上的事情致远又丝毫帮不了她,只能靠自己。可她工作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衰败、锐减的经济逆势。
午夜过后,黑夜之中,中年女人想起了另一个人——王福逸。他从安科展之初便跟着老钱总,见过公司的大起大落,也经过行业的大起大落,他多少是见过大世面、经过大场面的人——他肯定有法子。一想到王福逸,桂英如找到救星一般,一颗心不再绷着了,缓缓松弛下来,方才入睡。
第二天到办公室以后,桂英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王福逸的电话。那边早到自己工厂里的王福逸看到是桂英打来的,十分欣喜,赶紧接通电话,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与她通话。这边马经理讲明情况以后,那头的王福逸有条不紊地安抚、分析、指点,最后给出了好些珍贵的建议。马经理举着电话嘴角弯弯,一边听一边手里赶忙记着,唯恐错过了一条。两人如此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一个多钟头才挂掉电话。
桂英俯视纸上慌乱的笔记,频频点头。福逸说得对,大势如此,接受现状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的确得需要召开个专门的业务会议聊一聊这件事,越是避而不谈,业务员们心中越是惶恐不安。倘若业务员一个个先走了,那流失的中小客户更多。打预防针、服安慰剂,然后逆势而生,争取流失的客户最少,保底求稳——这才是今年安科展业务方面的终极目标。倘若再贪图增长,以为一年总比一年好、今年赚得永远比往年多,那业务员们本有的自信也会被极大打击。
职场女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福逸的智慧,马经理整理好思绪,通知行政的同事安排下午的会议室,一场保底求稳、稳定军心的会议迫在眉睫。
最近桂英忙于自己的业务,的确疏忽对业务部的管理,这才导致好几个业务员离职、业务员各自业务纷纷流失的事实。在这个档口,的确应以大局为重,放下小我的利益。桂英举着那张纸,心中开朗了许多,对王福逸更是暗暗钦佩。
早上九点多,何一鸣正在听化学课,突然桌子上传来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如是写道:“何一鸣,不好意思,我爸爸下午不让我去参加你的生日,所以……对不起啦!”一鸣举着纸条看完以后,知那是顾舒语的笔迹,他转头望向顾舒语,只见顾舒语撅着小嘴耸了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没事没事!”何一鸣故作无事且大笑着对顾舒语悄悄做了个口型,而后转过头继续仰望黑板,心中却冰凉冰凉的。
为了盼着顾舒语能来,他从前几天晚上就开始布置自己的小房间,想着她再来时能耳目一新、破颜一笑甚至称赞几句;为了让她对自己另眼相看,他提前半个月便在揣摩生日这天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饰品;昨天晚上和爸爸确定菜单时,其中他执意要点的五样菜全是顾舒语爱吃的;甚至,为了感谢她的计算机,何一鸣连回谢的小礼物也买好了,只巴巴地等着她来……
“何一鸣,不好意思,我爸爸下午不让我去参加你的生日,所以……对不起啦!”
“何一鸣,不好意思……”
“何一鸣……”
少年郎抬着头,余光却不住地垂下来扫视书上放着的那张纸条。那文字如此清秀,那言语很有礼貌,写出来的“何一鸣”三个字真的很好看……豆蔻少年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默重复,在失落中挑拣安慰,在沮丧中幻想希望。
又不是她自己不想来,是她爸爸不让她来,女孩子应该管得严一些,他能理解的,他能理解的——何一鸣如是安慰自己。
上午十点,老马看电视看累了,关了电视,放下遥控器重新拿起手机。时兴的老头到深圳才一个多月已习惯了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等当下通用的软件。老马无意中点到了微信朋友圈,在圈子里翻看着图片。
正看着电话响了,是老二兴盛打来的。
“喂?大!”兴盛如孩子一般喊着父亲。
“哎!咋了?”老马问。
“么事!明个中元节,我给我妈和我婆早上扫墓的时候,碰到了我建民叔。我打眼一看,他瘦了一大圈!”
提到马建民,老马攥了攥手里的龙头拐杖——那正是建民送给他的。建民是老马的堂弟——家里二叔的儿子,比他三弟马建济大几个月,如今也是六十岁的老头了。人老了都会瘦,老马不知兴盛说的“瘦了一圈”到底是有多瘦。
“哦……你建民叔从县里回来给他大他妈上坟吗?”老马问。
“嗯!我从我妈坟上回来的时候碰上他了,就跟他一道又去我三爷的坟上。我两把那几个坟全清理了一遍,拔了草、围上土,然后我两一道回来了!”
“他身体咋样?”
“没啥大问题,但我看明显没上次好!”兴盛蹲在院子里回忆。
“家里有啥大事不?”老马坐在摇椅上好奇打听,不防备身边来了个走猫步的小人儿。
“前段时间咱屋的母猪生了猪娃——十二个,死了一个!现在十八天了,这段时间好几个人来我这问价!其中一个人出到了四百块一条!”兴盛伸出四指,一脸的不可思议。
“猪生娃儿——这么大事你咋没给我提前说?”老马不高兴。
“忙!这么多活我哪有时间打电话呢!我那晚上八点多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它已经生了七个了!一晚上忙活,第二天早上喂完母猪赶紧又去果园!太忙咧!”
“哦!我听致远说猪肉涨价了,没想到这么贵!现在这些人一天天胡整哩——可憎得很!最近深圳一斤猪肉三十多!屋里唻?”
“也是三十多!前天我问是三十八一斤!咱村里牛肉才四十二一斤!你说说这事儿!”兴盛不解又窃喜。
“咿呀!啧啧!管他呢!反正咱赶上了!这段时间你把猪娃看好,等几天出月了赶紧卖了,千万甭拖!赶紧卖!”老马脸上的表情一会天堂一会地狱。
“嗯!这一窝猪娃能卖上些钱!哦还有,前几天兴兴家青辣子卖上价了——一斤一块七!那天我跟兴成、行波三个人开车给她家摘辣子,她还雇了她村两人一块摘,那一天三亩多辣子一齐卖了九万多!啧啧!美太太!”兴盛啧啧点头,心里激动无比。
“咿呀!撩咋咧!兴兴今年赶上了!种了好几年没赶上,今年逮住了!撩得很!你跟兴兴提醒提醒,要是她妹子兴华朝她借钱——千万甭给!给兴华她婆婆都行千万甭给兴华两口!那两口子浮得很!”老马说完那嘴咧得有一丈长。
“嗯!”兴盛连连点头,在心里默记着这件事。
兴盛忽想起另一桩事,吞吞吐吐:“呃……我哥……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他问了问屋里情况,说他回陕西了,待了几天可走了,没回咱屋里!我想见他……可么见上……哎!”兴盛眉目里十分失落。
“啧!甭管他!甭管他!好好弄你的事儿!果园闲得没活儿吗?还有心操心他!没事赶紧到地里忙活去!”老马气不打一处来,话语立刻变了味儿。在旁玩耍的漾漾听得不对劲,吓得扭头瞪着小眼瞅着爷爷。
“知道了知道了!”兴盛怯怯地说。
“行了,么啥事儿我挂了!”
“嗯!”
老马挂了电话,长叹一口气。时常想起老大马兴邦,每每无不叹气。最烦他到处胡跑,他愣是到处胡跑——一跑跑了二十多年,啥名堂也没跑出来,白白耽搁了半生光阴。要搁在村里,他还仗着自己村长的身份给他寻个好亲事,现在几年几年地不见人——不回村也不回省,电话也不乐意打……每回每回,一想起这个儿子,老马心中顿涌出无限的愁绪来,呼吸不经意间变得沉重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