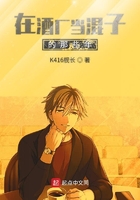第二天醒来时头疼欲裂,转头看见范三还在打呼噜。房间里没有蔡亮的影子,上厕所时又看到隔壁小李的女人在洗衣服了——她似乎有永远洗不完的衣服——蔡亮不在厕所,难道他去摆摊了吗?我回到房间推醒范三问他蔡亮去哪里,范三迷迷糊糊地说昨晚蔡亮送郑萍回去了,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响:难道昨晚蔡亮在郑萍那里过夜了吗?竟敢对我的女人下手了,亮鳖简直是禽兽!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怒火。
坐在床沿想着怎么揍蔡亮,我打算他一进门的时候就一个飞脚将他踹回出去,或者拿起床底下那个被小D搞破的热水瓶朝他砸去,或者冲过去盖他一巴掌……等了很久也不见他回来,我就去厕所洗了把脸,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郑萍并不是我的女人——微风吹过我被水浸湿的脸时,我这么想着,我们从来没有确立关系过,我也没和蔡亮说起过。不能就这么毁了十几年的兄弟情谊。可是,郑萍其实是喜欢我的——她居然舍不得吃我给她的花生,可见她多么爱我。蔡亮怎么可以趁她酒醉就下手……太过分了,想来想去我心里依然有一股怒火,最终还是打算把蔡亮揍一顿,可是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回来。我肚子有点饿了就打算去楼下吃碗面。
吃完面以后我决定亲自到郑萍那里走一趟,今天正好是周六,她不用上班,说不定正和蔡亮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呢。一想到这里,我不由怒火中烧,加快了脚步,到了郑萍楼下后正要放声叫嚣,突然听见楼梯响起了熟悉的啪嗒啪嗒声,是拖鞋打在瓷砖上的声音,郑萍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此急迫地往楼下跑来,她仿佛被追杀一样撞开铁门,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的,手里拿着个手机,她见我站在那里急忙大声叫道:“华辉,快,蔡亮住院了……”
我一听脑子又嗡的一声响,急忙问:“蔡亮不是和你在一起?他怎么会在医院里?”
郑萍把手机递给我说:“他昨晚送我回来后就回去了呀,刚才有个自称警察的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蔡亮的朋友,让我去一趟医院。我想打电话给你们,你们都停机了。”
太蹊跷了,蔡亮居然和警察扯上了关系,我连忙打电话过去,那人说蔡亮在医院躺着,让我们赶紧过去,我追问蔡亮做了什么事,他不耐烦地把电话挂了。
往医院赶去。见到蔡亮时差点没把我们吓死,只见他鼻青脸肿,像个猪头一样。郑萍立刻哭了下来。蔡亮知道我们来了,浮肿的嘴巴微微一斜,表示微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说不上话。
来了一个护士问哪个是家属,我说我们都是家属,她说你们出来一下,跟着护士出门时,我心想:难道蔡亮……心里一阵害怕,到了门口才知道护士是叫我们交钱去的,我一看要五千多元立刻大叫起来。
现在连五十块都没有。
范三仰起头看着收银的人说:“钱一分也没有,要命有一条。”这话仿佛对强盗说一样,郑萍忍不住扑哧笑出来。护士一声冷笑:“你们当这里是慈善机构啊,没钱就停药。”我们一听要停药,再想到蔡亮奄奄一息的样子,立刻急了,我赶忙说:“我们去找,你们再给我们几天时间。”
又去看了蔡亮,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出了医院。
五千元啊,苍天。
不知道该死的蔡亮到底去干什么了,会被打成这样。早知如此,还不如在郑萍那里过夜呢,让别人打不如让兄弟我打。
我在医院门口看了一眼郑萍,说:“郑萍,昨晚他喝醉了你怎么不留他在你哪里休息?”郑萍愕然地看着我说:“我……”她娇羞地低下头。
我居然问出这种鬼话,真该给自己一个巴掌。
抬头想到要去找五千多元医药费,我就咬牙切齿,等蔡亮好了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本来生活就够艰苦了,他还整出这种灾难来。
回到小阁楼后,我和范三躺在床上商量对策。一个多小时后有了初步的计划:先把旧房客的书卖了。当时他委托我们把这些书转交给另外的三千位壮士,既然找不到那三千壮士,就转交给收破烂的壮士吧。在卖书之前我和范三把书一本一本地翻了一次,范三说书里有可能夹着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结果我们大失所望,这个不知道是诗人还是疯子的旧房客一分钱都没往书里夹。不过我再次看到了他的诗歌,是打印稿的,我这才知道其实他那天念的并不是“祖先失笑”,而是“祖先失效”。我把那张打印稿放在床上,然后就叫了收破烂的人来,那些书我们一共卖了一百五十三元,而这些书的原价大概要一万多,这种落差让人不胜唏嘘。
由于找到的钱只是杯水车薪,还不够医院塞牙缝,我们破罐子破摔,当晚拿着这些钱又去喝了一次酒,范三的意思是想借酒找点灵感,这样才能尽快找到另外的四千九百元。坐在昏暗的小饭馆里,点了几个带有辣椒的菜,范三特意点了两盘青菜,很久没有吃绿色植物了。
喝了几杯酒后,范三的脸上涌起两股红晕,他的视线透过厚厚的镜片落在脏脏的地板上,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四千九百元……干,医院赚得也太爽歪歪了吧?”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认真地问道:“辉鳖,你活了二十四年,有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四千九百元?”
我想了想,确实从来没摸过这么多的钱。不过我记得当年给祖先扫墓的时候,我曾经摸过上万的冥币。
“冥币肯定不算啦,你又不是死人。”范三说。
“那就没摸过了,不过蔡亮如果需要的是冥币我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了——你摸过这么多钱吗,三鳖?”我反问范三。
“没有。”他抬手推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这些年读书都是贷款读的,他妈的,我还欠国家一大笔钱。”
“国家的钱慢慢还吧。拖它几年,等人民币贬值了再还。”我说。
闲扯了一阵,谁也没把话题引到怎么找钱的事情上来。酒足饭饱后打算去医院看看蔡亮——坦白说,我觉得那个人已经不再是蔡亮了。
我在去医院的公交车上问范三:“三鳖,你觉得蔡亮被打成这样了他还是蔡亮吗?”
范三的头靠在幽暗的车窗上,“应该还是吧,虽然电视里经常把被打成这样的人成为猪头,但在本质上他依然还是蔡亮。”
当时公交车正好驶过一个文明小区的门口,人行道上有很多名人的头像雕塑,我于是说:“如果一个人被砍头了,他其实已经不是他本人了,他变成了一具尸体。蔡亮被打成这样了,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吧?”
“太麻烦了,一个新的名称够麻烦的。生活允许误差。而且严格意义上讲,蔡亮被打成这样,顶多叫他‘坏掉的蔡亮’”,范三说。
其实在漫长的、颠簸的路上我们应该谈谈蔡亮为什么会被抓、又为什么会被打,可是这个话题谈了几次都猜不到答案。眼下的这个问题却很好消遣:坏掉的蔡亮——这让我突然想起了被小D搞破的蔡亮的热水瓶,坏掉的热水瓶,我们再也不会称它为热水瓶了,有些人会称之为垃圾,有些人会称之为废品,当然,蔡亮完全是会康复的,这是他和热水瓶的显著区别。
这段他卧床不起的日子,我们要不要用新称呼?文明小区的最后一段路种着许多竹子,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三鳖,你知道竹子小时候的昵称是什么吗?”
范三想了想:“还是叫竹子啊……不对,竹子小时候应该是叫‘笋’”。
“嗯,那青蛙的小时候呢?”
“青蛙小时候叫蝌蚪。”
“它们很幸福,小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为了让蔡亮以后不至于太不幸,我们决定给蔡亮重新取个名字,可是车行驶几个站了我们还是没想出来。
到了医院门口时,范三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紧锁眉头,然后开心地说道:“辉鳖,另外的四千九百块我有办法啦,你刚才说青蛙小时候的事情,蝌蚪启发了我,精子不是被称为小蝌蚪吗?我们去卖精子怎么样?这样来钱肯定快。”
我一听顿时要晕过去,“三鳖,你疯了吗?精子不就是儿子!我们为了蔡亮难道把儿子都卖了吗?我不赞成这个办法。”
范三说:“精子如果没有卵子根本成不了儿子的,卖精不算卖儿子,法律是明令禁止贩卖妇女儿童的,但却提倡卖精子。”
“卖精子是怎么算价钱的?”我问范三说。
范三也不知道,往蔡亮的病床走去时我们打算去问问这座医院的人。
“这个医院这么黑,我们在这里卖可能会被坑了。”我说。
“嗯,这相当于他们从我们这里进货,就像当时我们找钱老板批发瓜子时,一直在压他的价,要是真在这里卖精子我们千万别被他们黑了。”范三说。
我心里其实很不愿意卖精子的。走进了蔡亮的病房,他正睁着小小的眼睛看着天花板。我对范三说:“三鳖,我们让蔡亮去自己卖怎么样?这样更公平。”范三听完哈哈大笑,我突然想起这些天来蔡亮的异常举动,他很久没有射了,女子十二乐坊根本不听他的。
坐在床边看着鼻青脸肿的蔡亮,他依然无法清晰地开口说话。
护士进来给蔡亮换药时范三问她说:“护士姐姐,你们这里收精子吗?是怎么算价钱的?”
范三后来说那小护士脸皮很厚,说到精子也不脸红,果然是多见不怪。她让我们自己去问接待员。
这时,门口突然走来一位警察,我们都立刻站起来,他朝我们点点头,走到蔡亮身边凑到蔡亮耳边说了几句话,很快蔡亮就从被窝里伸出手把一个东西交给了警察,警察拍拍他头顶,笑着转过身对小护士说:“小妹妹,好好照顾这个小伙子,他是个英雄,帮我打坏人才受伤的。”说完笑着走了。
这个警察的举动让人觉得十分蹊跷,只是蔡亮已经闭眼准备休息了。
午夜前,约摸最后一班车要开走时离开了医院。坐在公家车里飞速穿梭在大街上,终点站下车后在站台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贴小广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牛皮癣广告”,很好奇就走过去看,那上面写着:诚聘专职公关,要求身体好,有事业激情,月薪两万不是梦。
“这是招鸭的广告。”范三说。
“去试一试吧,你不是很想去干那些有钱的女人吗?我觉得这样比卖精子好多了。”我说。
找那个小孩子要了一张广告,我们在浓黑的夜色里往几百米外的莲花小区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