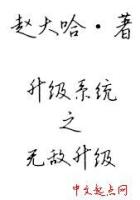背叛,是地球人的一種行為。
背叛這種行為,是表現地球人性格的典型。
背叛,在其他地球生物的行為中找不到。
背叛是不是在外星生物的行為中也有?不得而知。
背叛是一種極壞、極賤、極卑鄙、極下流、極可恥、極無情、極殘酷、極可怕的行為。
必須說明的是:背叛,絕不等於叛變。
背叛是背叛,叛變是叛變。
叛變在明中進行,背叛在暗中進行。
叛變可以光明正大,背叛必然黑暗陰森。
問題不在那個“叛”字,是在於那個“背”字。
人人有權和任何人由合而分,而由一致而對立——這種過程是叛。但如果叛的一方,在進行這一切的時候,被叛的一方全不知情,叛的一方,還竭力在瞞騙欺哄被叛的一方,那就是背叛。
被背叛,是極令人痛心的事,其令人痛心的程度,大抵是人類所能感到的痛心之最。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背叛是什麼呢?《創世紀》上這樣記載着:“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是從女人先開始,受不了引誘,背叛了上帝。
(背叛行為之中,必須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引誘在。)
(被背叛了的上帝,表現了人所無法表現的偉大心胸,人類自此墮入罪惡深淵,可是上帝還是盡一切力量在拯救世人,甚至派出唯一的兒子,用寶血來洗世人的罪。)
故事其實不是從說教開始,而是從一場戰爭開始的。
戰爭也是人類行為之一,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在人類居住的這顆小行星上,沒有一天停止過,一直不斷地有各種各樣的戰爭。大而古老到了軒轅黃帝和蚩尤在中國北方平原上的大戰,驚天地泣鬼神。小而接近的到屋外空地上,兩批孩子忽然不知為了爭奪什麼而打了起來。
(在戰爭行為之中,必然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爭奪的目標在。)
不必問時間地點交戰雙方等等細節,總之,那是一場戰爭。
整個作戰的方案,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來,師長和副師長、師參謀部的大小參謀,都反覆經過詳細的研究,也通過了種種方法得來的情報,對敵人方面的兵力有着確實的了解,敵方將領用兵的方式,也了然於胸,這一仗,一定可以打贏,而且可以贏得極其漂亮,大獲全勝。
這一個師的兵力足,武器好,師長和副師長之間,親若兄弟,副師長經常笑着對人說:“我是師長從垃圾堆裏撿出來的。”
而師長一聽得副師長那樣說的時候,總也笑着:“胡說八道什麼。”
副師長的神情,會變得認真“本來就是,九年前,我——”
這一番對話,認識師長和副師長的人,都聽過三遍以上,可知九年來,他們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樣的對話。內容完全一樣,當然,當師長還是旅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的時候,對話中的“師長”,要換上師長在那時候的職位。
所以,故事也不是從戰爭開始,而是從師長和副師長的相遇那件事開始的。
師長姓甘,大名鐵生,像是生來就該當將軍的,可是他的外形,和他的名字、軍職,絕不相稱。要是他不穿軍服,穿上一襲長衫,再拿一柄摺扇的話,那根本就是一個文弱的白面書生——事實上,甘鐵生投筆從戎,的確文武雙全。
帶兵,並不好帶,並不是所有的軍隊都有良好的紀律,有的老兵,十年八年兵當下來,在戰場上經歷得多,把生死得失全看得淡了,長官的命令,要是不合意,照樣當耳邊風。
可是甘鐵生帶的兵,一直都被稱為“鐵軍”,那自然是由於他治軍有方,韜略出眾,而且在衝鋒陷陣之際,勇猛無比——他纖細高瘦的身形,本來應該在幾千個彪形大漢之中,成為笑柄,可是誰也不敢小看他,因為他打仗勇猛。所以,他十八歲當排長,二十七歲就當了師長。
副師長姓方,大名也叫鐵生——那是一個很普通的中國男性的名字,連同名同姓,也大有可能,單是名字一樣,不算太巧。
副師長的外形,和師長剛好相反,他們兩人名字相同,可是外形截然相反,方鐵生是真正的彪形大漢,身形魁梧雄壯之極,手伸出來,大如蒲扇,捏成了拳頭,就和醋罎一般。曾有幾個老兵打賭,說他的手,能握住拉了引線的手榴彈,就讓手榴彈在他的掌中爆炸,而他可以無損分毫。
那場打賭,自然沒有結果,因為勇猛如方鐵生,也不敢真的那麼做來證實一下。
他身高接近兩公尺,全身肌肉盤結,每一塊突出的肌肉,都硬得像鋼塊,他力大無窮,一個人可以負起一門大炮,他滿臉虬髯——關於他的鬍子,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勤務兵替他刮鬍子,刮了左半臉,再刮右半邊,刮完了右半邊,左半邊的鬍子又已冒了出來,摸上去會扎手。
所以,方鐵生想保持頭臉之上,淨光滑溜;是沒有可能的事,他也乾脆把虬髯留了起來,每十天半月,修剪一次,他的虬髯一圈圈,又密又黑又硬,更替他這個凜凜大漢,增添了十二分的剛猛威武。不論是誰看了,都會聯珠般喝采:“好一條漢子。”
又有傳說,說他在戰場上,故意揀高地,往上一站,天神一般威風,敵軍一起舉手投降,寧願成為他的部下,往往可以不戰而勝。
這個傳說雖然誇張了一些,但是有一次,軍中官兵同樂,演《風塵三俠》,方鐵生扮虬髯客,一出場,采聲雷動,倒的確沒有人不叫好的。
方鐵生方臉濃髯,身形又高大之至,但是他為人卻十分隨和,對部下從來不疾言厲色,只罪打仗時不拚命的人,其他一切錯誤,他都一概不理,只當看不見,有事求他,只要他能答應,無有不應允的。
要不是他性格隨和,雖然說“英雄莫論出處”,但也總不能把“我是師長從垃圾堆裏撿出來的”這樣的話,一直掛在口邊。
對了,這樣神威凜凜的一員猛將,怎麼會是“從垃圾堆裏撿出來”的呢?
要把時間向前推九年。
那年,甘鐵生十八歲,軍職是排長,方鐵生十二歲,在垃圾堆中。
垃圾堆,是真正的垃圾堆。那樣的垃圾堆,普天之下,不知凡幾,垃圾堆上,照例有漫天飛舞的各類蒼蠅、老鼠、野貓、野狗和無家可歸的流浪少年,各盡所能,希望能在垃圾堆中,發現一點可以靠它維持生命的東西。
那個垃圾堆,位於一個小火車站的旁邊,車站小得只有半邊鐵皮屋(另外一半不知什麼時候叫人拆走了,或是銹壞了。)
這種小地方,平時人迹稀少,一天也未必有一班火車經過,而甘鐵生恰好就在這時經過。
運兵的列車不在正常的班次之內,又不是有軍情,只是普通的調防,並不趕時間,所以載甘鐵生排長所在的那個團的運兵車,就開開停停,停停開開,在什麼地方停,完全沒有規律,只是臨時決定。
人的命運,真是天下最奇怪的事,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一個機緣,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而一個人的一生,又可以影響許多人的一生,許多人的一生糾纏聯結起來,就是整個人類的命運。而一切,絕對可以只開始於偶然的偶然。
像那時,運兵車如果不是在那個小站中停了下來,就不會有以後的事發生了——自然,還是會有事發生,但必然完全不一樣。
一個因素還不夠,要是方鐵生那時不在垃圾堆中又扒又撥,也就不會有以後的一切發生了。
兩個因素也還不夠,還要加上甘鐵生正在車廂門口,無聊地站着,運兵車全是貨廂,俗稱“悶罐車”,車停了,打開車廂的門,呼吸新鮮空氣,他在身後的車廂裏,有他率領的一排士兵,在他前面,是廣袤無垠的平原,直到天腳下,才影影綽綽,有點山的影子。甘鐵生已經打過幾仗,年紀雖然輕,可是志向很遠大,望着一直向前伸延開去的大地,他正在假設自己不是一個小小的排長,而是一個將軍。
要在這一片平坦的大地上,和敵軍決一死戰,應該如何進攻,才能取勝。
所以,那時候,方鐵生離他雖然只有十來公尺,他根本沒有注意到。
又一個改變命運的因素來了,那個小火車站,居然還有一個站長,就在那時候,這個老站長從那半間鐵皮屋中,探出頭來,大叫了一聲:“鐵生。”
使方鐵生和甘鐵生兩個本來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忽然之間,變成了並肩作戰,生死與共,浴血拚命,情同手足的各種原因,到這時大致齊備了。
老站長一叫,甘鐵生排長就先吃了一驚,自然而然,把在原野上馳騁,指揮着他想像中千軍萬馬的視線,收了回來,望向那一下叫聲傳出之處——這是任何人忽然聽到了有人叫自己名字的必然反應。
於是,他看到了老站長,老站長卻並不是面向他,而是面向着一堆垃圾,還伸手向前指着,甘鐵生的視線,也自然而然循他所指看去,理所當然,他看到了方鐵生,只不過那時,方鐵生背對着他,正俯着身,用雙手在扒撥着垃圾,方鐵生看到甘鐵生,要遲上幾秒鐘。
老站長又叫了一聲:“鐵生。”
甘鐵生這時知道了,老站長叫的不是自己,是那個在掏垃圾的人。
老站長繼續叫:“別掏摸了,能有什麼吃的,也全叫野狗叼走了,能有什麼剩下的?反倒弄得蒼蠅亂飛,臭氣衝天。”
甘鐵生這時,也感到自垃圾堆中,有攻鼻的臭氣冒出來,他不禁皺了皺眉,雖然他已有相當的軍人經歷,可是在這樣的垃圾堆中,就算有什麼殘剩的食物,又怎麼能入口?看起來,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不設法找別的方法去填飽肚子?他的心中,對那個人,既有同情,但也有幾分輕視。
老站長話還沒有說完,方鐵生就站直身子,轉過身來,他一轉身,並不先看老站長,想來老站長的這種話,他聽過很多遍了,或者他根本不願意望向老站長,只是隨便把視線移向一處,恰好,和甘鐵生對望了一眼,甘鐵生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下低呼。
並不是方鐵生有什麼令人吃驚的怪容貌,那時,他才十二歲,自然也沒有一臉的鬍子,令得甘鐵生發出低呼聲的原因是,方鐵生一站起來,個子極高,骨架極大,可是瘦得真不像話,露出破衣服(如果那還能算衣服的話)外的兩條手臂,簡直就是兩根又大又粗的骨頭。他的臉上,除了那一雙眼睛之外,也找不到別的什麼。
而且,一和他照面,任何人可以看出,他只是一個孩子,臉上污穢得難以形容,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孩子,至多,說他是一個少年。
可是他個子卻已經那麼高大,看起來不相稱之至。
甘鐵生在發出了一下低呼聲之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那個子高大的,名字可能也叫做鐵生的少年,一看到他之後,目光就沒有移動過。
甘鐵生完全可以接觸他那毫無掩飾的眼光中所表達的人類感情。
說來很奇怪,當時,只在那一剎那,甘鐵生就完全知道了這個奇怪的少年通過他的眼神,在訴說些什麼。他是在訴說他的不幸,訴說他生活的困苦,可是也告訴人,不論多麼困苦,他要生活下去,他可以接受人家的同情,但決不接受賜捨,他不是乞丐,他寧願在垃圾堆裏找又腐又臭的食物(還不一定找得到,這時,他瘦骨鱗峋的大手上,就只是提着一隻死老鼠),也不願意去乞討。他的眼神之中,有着倔強,也有着人的自尊,甚至於還包含了要求人家對他的尊重。
那種眼神,簡直勇敢之極,甚至十分高貴,又有幾分稚氣的驚喜,和他這時的外形,極不相稱,但是卻恰如其分地顯示了他的內心世界。
兩個人視線接觸的第一次,時間相當長——通常,陌生人很少有三十秒以上互相對視的時間。甘鐵生的心中,起了一種十分異樣的感覺,感到這樣骨格壯大的流浪少年,會在自己生命中起極其重大的影響,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於是,他幾乎沒有考慮,就向方鐵生招了招手,同時叫他:“小兄弟,你過來。”
若干時日之後,方鐵生回憶那一剎那的偶遇,他有他的說法。
方鐵生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父母是什麼時候去世的,他年齡太小,完全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長大的——中國北方的民風,比較淳厚,雖然不能長期照顧,但是收留一兩天,給幾件破衣服,給點殘菜冷飯,總還做得到。
方鐵生就在這種情形之下長大,和野狗為伍,練成了什麼都能放進嘴裏、吞下去、塞進肚子的本領。也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這個原因,他竟長得出奇地高大,八九歲的時候,站起來就像大人一樣高,一過了十歲,更是又高又瘦,食量也大得驚人,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覺,幾乎都在為找吃的動腦筋。他找食物的辦法也真多,大多極其原始——夏天爬樹抓蟬,一抓幾百個,可以吃頓飽的,冬天挖田鼠洞,挖到了一個,不但田鼠不論大小,都進了他的肚子,洞裏田鼠儲存的食物,他自然也絕不客氣,一律接受。
諸凡青蛙、四腳蛇、野狗、野貓,一切地上爬的,天上飛的,田裏長的,樹上結的種種東西,一到他的手裏,都能化為食物。
鄉間的野狗多兇,見人就吠,揀好欺的會咬,啃吃過死屍的野狗眼睛還會發紅,可是由於方鐵生殺野狗,吃野狗實在太多,所有野狗,老遠看到他的影子,挾着尾巴就逃。
聽說,常要在鄉間趕路的婦道人家,在方鐵生的破衣服上,撕下一小塊布來,掛在身上,由於那上面有方鐵生的氣味,野狗聞到了,也會遠遠避開,以保行路人的安全。
在這種情形下長大的一個孩子,不折不扣,實實在在,是一個野孩子。
可是他自小就性子十分隨和,只有人家欺負他,他從來不去欺負人,當然,被人欺負、輕視,不加反抗是一回事,心裏絕不會喜歡被欺負輕視,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當他那一天,一轉過身來,看到甘鐵生的時候,最初的一剎那,本能是抗拒的。
他在若干時日之後這樣說:“鐵路上來來去去的運兵車很多,也有散兵游勇,也有整隊開拔的,見得多了,總覺得軍官也好,小兵也好,好像都是另外一種……東西……另外一種動物,和普通人不同,當兵的呼喝,打人、踢人,誰也不敢反抗。
“可是他不同,我一看到他,車廂門口,瘦瘦削削,整整齊齊,可是又那麼有自信地站着,他只是隨隨便便地站着,就好像他就是一切的主宰。
“他的眼神,開始時十分猶豫,可是一下子就變得極其……嗯……極其溫柔,從來也沒有人用這樣子的眼神望過我,在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會關懷我,幫助我,那正是我從來也沒有過的……人類感情,我和他對望着,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心跳加快,身子發熱,恨不得衝過去,緊緊地抱一抱他,或者是讓他緊緊地抱一抱我。
“我一直盯着他看,他也一直看着我,我全身都在發抖,當然,那種從心處發出的顫抖,人家是看不出來的,正在這時候,他開口了,他開口了……”
儘管事情已經過去好多年了,方鐵生每次,一講到這裏,還是會聲音嘶啞,顫動,情緒激動,可知他當時的情緒,不知激動到了什麼程度。
他會深深吸一口氣,然後再道:“他開口了,他叫我“小兄弟”,小兄弟,從來沒有人這樣叫過我的,真沒出息,我心裏不知多高興,可是鼻子一酸,卻眼淚滾滾,我從來也沒有哭過,難過得就算要死,揪心揪肺,我也沒流過眼淚,那是我第一次哭。”
甘鐵生一叫,方鐵生立即就向他奔了過來,甘鐵生也早已看到,這流浪少年滿臉淚痕,淚水還在不斷地湧出來,他臉上本來髒得污垢只怕有好幾重厚,給淚水一衝,有的化了開來,有的衝掉了,有的還留着,成了一塊奇特無比的大花臉。
照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甘鐵生至少要問上一句:“你怎麼哭了?”可是他沒有問,因為他一眼就看出來,這個野少年並不是哭,只是在不可抑制地流淚,所有的地球生物之中,只有人才會用眼淚來表示情緒。
淚腺和腦部某些區域,有緊密的聯繫,情緒自腦中產生,或悲或喜或感動或激昂,都會刺激淚腺,湧出眼淚。
甘鐵生在這少年瞪大了的眼睛中,看到了激動的光芒,他知道他為什麼會流淚,自然不必再問。
方鐵生不想流淚,可是那不受控制——人的身體中,有着太多的完全不受腦部控制的部分,他也不去抹淚,只是當甘鐵生伸出手來的時候,自然而然,把他的手交到了甘鐵生的手裏。
方鐵生的手,其實比甘鐵生的還要大,幾乎全是骨頭,又粗又硬,兩雙手,立即緊緊相握在一起。
這兩雙手,在後來的歲月中,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可是這時候,一雙手屬於一個年輕有為的軍官,一雙卻屬於一個無父無母的流浪野少年,相去不知多遠。
可是任何那時看到這兩雙手互握的人,都不會懷疑他們的感情,都會相信在這兩雙手之間,絕不能再插進一些別的什麼。
甘鐵生先開口:“你的名字叫鐵生?鋼鐵的鐵,生命的生?”
方鐵生想回答,可是喉間不知叫什麼東西便住了,只能發出一些奇怪的、沒有意義的聲音,他立即用力點着頭,表示肯定的答覆。
甘鐵生笑了起來,也用力點頭:“我也叫鐵生,和你的名字一樣。”
方鐵生的眼中,射出極明亮的光芒。
甘鐵生又道:“我姓甘,你呢?”
方鐵生直到這時,才迸出了一個字來:“方。”
甘鐵生自己也不知道為了什麼,心中只覺得無限高興,他望着這少年,用力搖着他的手,再問:“你多大了?有沒有十五歲?”
方鐵生吸了一口氣:“十二。”
白素突然問我:“怎麼樣?”
我回答:“很好,很吸引人,不過,有許多地方,太囉嗦,太……細膩了,或許,女作家的緣故?”
在我和白素這樣對話的時候,正一起在看一篇小說,小說的題目是《背叛》,和我的這個故事一樣——事實上,要是沒有這篇題為《背叛》的小說,就絕不會有我這個題為《背叛》的故事,這一點必須說明,但是我又絕不是抄襲,只不過是小說的故事,都環繞着背叛這種人類的行為而發生。
背叛這種行為,除了人類之外,大抵在別的生物中都不存在,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人類行為,因為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關係的人之間,都不斷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