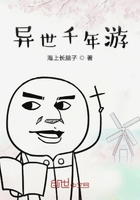要在七億印度人中找一個不知姓名的印度人,那幾乎不可能!
但如今,我卻聽到了他的聲音!
我陡地震了一震之後,立時轉過身來。在我轉過身來之際,那客人也恰好轉過身來,我們兩人打了一個照面。
在那一剎那間,我們兩人的神情,都像是受了雷殛!那印度人,雖然這時,他看來儀容出眾,衣飾華麗,鬍子經過小心的梳理,緊貼著頰旁,看起來威嚴莊重。但是我仍然可以毫不猶豫肯定,他就是那個在酒吧中對我說話的那個看來像是流浪者一樣的印度人!
我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神秘的印度人,竟有著甚麼王子的銜頭。而這時,看他這身打扮和氣派,他那王子的銜頭,不是假的!
我想,對方一定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突然見到我,他的震驚可能還在我之上!
那專家也發現了我們之間對視著的情形,他大步向我走來,十分不客氣地來推我,想將我推出門去,以免得罪他的貴客。
別說我突然見到了那印度人,絕不會放過他,單是專家這種不客氣的態度,也足以令我冒火的了。所以我毫不客氣,用力向外一推。那一推,令得專家跌出了好幾步去。
而我一推開了專家,立時向那印度人走去:“想不到,真想不到!”
那印度人──耶里王子──的面肉抽動了幾下,也道:“是的,真想不到!”
我興奮得不由自主搓著手,因為找到了這個印度人,我心中的許多疑問,都可以得到解決了!
我一面搓著手,一面向著他走過去,直來到他的面前,才站定身子,不理會專家發出憤怒的吼叫聲,正在向我衝過來,我道:“原來你還是一個甚麼王子?我想,我們應該好好地談一談!”
我的話才說完,對方還沒有反應間,專家已來到我的身邊,又用力來推我,可是我已經先行出手,這一次,我將他推得跌出更遠。
耶里王子面肉又抽動了一下:“其實,也沒有甚麼好談的!”
我冷笑起來:“日本警方對你很有興趣!”
耶里也冷笑道:“這裏是印度!”
我有點冒火,但仍保持鎮定:“刑事案,可以通過國際警方來處理!”
耶里牽了牽口角,發出了一個相當陰森的笑容:“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我再踏前一步,用手指戳向前,抵住了耶里的胸口。這時,專家已經又掙扎著走了過來,但是他在吃了兩次虧之後,他顯然已不敢再亂來了,只是兇狠地瞪著我,沒有再動手,我也不去理他,一面用手指抵住了耶里,一面道:“你對武夫還有印象吧!”
耶里陡地震動了一下,我又道:“他曾幫你將磚頭灰漿運上去,我相信,這是那個大廈管理員致死的原因,是不是?”
耶里的神情更陰森,但是他顯然已經恢復了鎮定:“你是甚麼人?”他又望向專家:“我一定要和這樣的一個瘋子交談麼?”
專家怒吼了起來:“出去!滾出去!再不走,我要召警察來了!”
他說著,已來到電話旁邊,拿起了電話來。
我考慮了一下當時的情形,如果我不走,唯一的結果,就是給印度警察押走,我可不想被拘禁在印度的監獄之中。而且,我要找的人,既然是“王子”,那一定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要找一個普通的印度人難,要找一個有名有姓的王子,總不會是甚麼難事!
我後退了一步,高舉雙手:“好,我走!”
我一面說,一面向後退去,雙眼仍然盯著耶里。當我退到門口的時候,我道:“奇渥達卡還好麼?”我指著專家,“你來找他,其實並沒有甚麼用處,他知道得不多,我知道的,可能比他更多!你來找我談,比和他談更好!”
耶里只是冷冷地望著我,我又向他說出了我所住宿的酒店的名稱和房間號碼,然後,輕輕地轉過身,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在我向外走去之際,我聽得專家連忙在向耶里道歉,耶里卻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的心情極其輕鬆,因為我竟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要找的人!
在印度找一個印度人,健一認為那沒有可能,可是我卻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到了酒店,和那蒂星通了一個電話,表示我會和他再聯絡。然後,我將整件事,又從頭到尾,想了一遍。我已找到了那印度人,這是一大進展。而且我有信心,耶里一定會來找我!
耶里的身份特殊,而他卻在日本進行那樣神秘的活動,不管他活動的目的是甚麼,他一定不想人知道和深究下去!
他一定會來找我,不管他來找我的目的,是對我有利還是有害,他一定會來找我!
沒有人會喜歡自己神秘的活動給人知道,耶里不會例外。
我在床上躺了下來,連日來我都相當疲倦,我雖然考慮到耶里會對我不利,但是我總不能不休息,在保持高度的警覺下,我才要矇矓入睡,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
我一躍而起,抓起了電話聽筒,聽到了那蒂星的聲音:“日本有一個長途電話來找你,我已叫他打到你酒店來!”
日本來的長途電話,那當然是健一打來的了,我感到十分興奮,因為我已找到了那個印度人,這是健一再也意料不到的事情。
那蒂星並沒有耽擱我多少時間,我放下了電話,又通知了一下酒店的接線生,如果有來自日本的長途電話,立刻接到我房間裏來。
我在等著,等了三十分鐘,電話才又響起。
我一伸手,抓起電話來,在知道了的確是來自日本的長途電話之後,我已經準備立刻向健一大聲宣佈我的重大發現了。
所以,當我一聽到對方用日語在叫著“喂喂”之際,我立時道:“你再也想不到,我找到了那個印度人!那印度人可能是一個沒落王朝的後代,人家叫他王子!”
我講得十分快,電話那邊卻靜了下來,沒有了聲音,我又連喂了幾聲,才聽得一個人道:“對不起,你是衛斯理君?我不明白你講些甚麼。”
我也呆了一呆,那不是健一的聲音,雖然長途電話中的聲音不是很清晰,但是那絕不是健一,可以肯定。我略為猶豫了一下:“對不起,你是──”
那邊道:“我是奈可!你還記得我麼?我是奈可,雲子的好朋友!”
我呆了一呆,奈可!這個過夜生活的小人物,他打長途電話到印度來找我幹甚麼?而他是先打電話到那蒂星家裏去的,那當然是健一告訴他和我聯絡的方法,因為我只將這個方法告訴過健一,那麼,健一為甚麼自己不打電話給我呢?
我已經意識到有甚麼不平常的事發生了!
我忙道:“是的,我記得,奈可先生!”我唯恐他囉唆下去,因為在我的印象之中,他不是一個說話爽氣的人,所以我立即道:“有甚麼事,請快點說!”
奈可還是停了片刻,在那極短的時間中,他雖然沒有說話,可是我卻可以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可知道事情真的有點不尋常。
正當我又要催促他之際,他開口了:“衛君,健一君,他……他……”
奈可在口吃著,講不出來,雖然遠隔重洋,但是我彷彿可以看到他那尖削的三角臉,面上肌肉在不住抽搐的那種氣急敗壞的樣子。
我大聲道:“健一怎麼了?”
奈可終於講了出來:“健一突然辭職,離開了東京,他只留下了一張字條給我──”
我聽到這裏,不禁暗罵奈可這傢伙,小題大做,大驚小怪!我還以為健一發生了甚麼不得了的大事!
雖然健一突然辭職,這件事也可稱突兀,但無論如何不值得立刻向我報告!
我埋怨道:“就是健一君辭職的事?”
奈可急匆匆地道:“是的,不過,他留了一張字條給我,叫我立刻告訴你,還留下了和你聯絡的方法!他還要我將字條在電話裏唸給你聽!”
我有點忍無可忍之感,大聲吼叫道:“那麼,請你快一點唸!”
奈可給我一喝,接連說了七八下“是”,才將健一留給我的字條唸了出來。不過,在唸之前,他還是抽空加了一句他自己的話:“健一君留給你的字條,究竟是甚麼意思,我一點也不懂!”
健一交給奈可,耍他在長途電話中留給我的字條,如下:“衛君,我看到了自己,在你看到自己的地方,我看到了自己。在我看到了自己之後,我明白這些年來,我自己根本不是我自己,我不想再繼續扮演不是我自己這個角色,所以我走了,我要使我自己是真正的自己,我回到我應該回去的地方,來不及和你說再見。還有,不論事情多麼神秘,我看你也不必再追尋下去了,你不必去找那個印度人,快快找回你自己,那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聽我的勸告,老朋友。”
奈可一個字一個字,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健一留給我的便條,唸了一遍。他總算是盡了責。唸完之後,他又補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不過,他真的辭了職,而且,立刻離開了東京,走了。”
我呆了半晌。
健一的話,我也不是全部明白,可是我至少懂得甚麼叫作“我看到了自己”。也明白健一看到自己的地方,就是板垣和雲子幽會場所的那個怪房間之中。
健一在那怪房間裏看到了自己!
我腦中一片混亂,急於想知道事情的詳細經過,因為健一既然將便條交給奈可,在這之前,他一定曾和奈可聯絡過,我要知道詳細的情形。
我忙道:“奈可,你別急,你要將情形詳細告訴我,愈詳細愈好!”
奈可的聲音聽來很苦澀:“我……可以告訴你,但是我沒有長途電話費,我……我……”
我立時道:“你掛斷,再打給我,由我這裏繳費。”
奈可高興了起來,大聲答應著。
我和健一離開雲子的病房之後,由於健一的安排,而且在瘋子之中,雲子是十分文靜的那一類,醫生斷定她不會對人有傷害,所以允許奈可可以選擇任何時間,陪伴著雲子。
奈可這傢伙,對雲子真有一份異乎尋常的深厚感情,他所選擇的時間,是全部時間。也就是說,他一直在陪伴著雲子。
醫院方面事後說,雲子有了奈可的陪伴,精神好了許多,如果不是她仍然一直在翻來覆去說著那幾句話,從外表看來,簡直和常人無異。
奈可卻很傷心,因為雲子成了瘋子。他一直在對著雲子喃喃自語,叫著雲子的名字,不斷要雲子說出她的心事來,他一定替雲子分擔,哪怕事情再困難,他也願意負責。
由於奈可不斷對雲子在自言自語,看起來又傷心又失常,以致一個不明情由的實習醫生,有一次,反倒認為奈可是病人,而雲子是來探病的!
雲子對於奈可的話,一點反應也沒有。當晚,奈可向醫院要了一張帆布床,就睡在雲子的病床之旁。這本來是不許可的。
但是醫院得到了好幾方面的通知,雲子這個女病人,和極重大的案件有關,要盡一切方法,使她能恢復記憶。奈可的作伴,也是方法之一,所以醫院方面只好答應。
睡到半夜──這是奈可的敘述──奈可突然被一陣啜泣聲所吵醒。
奈可本來不願意醒過來,因為他實在太疲倦。可是據他說,這一陣哭泣聲極傷心,聽了之後,令人心酸之極,覺得就算發出這種哭泣聲的,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也應該立即放棄仇恨,轉而去幫助這個在絕望中哭泣的人。
所以,奈可揉著眼,坐了起來,當他坐起身之後,他看到雲子就坐在床沿,哭著。那種傷心欲絕,使人一聽,心就向無底絕壑沉下去的啜泣聲,就是雲子所發!
奈可怔怔地望著雲子,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雲子在以前,不是沒有對奈可哭過,有好幾次,雲子曾伏在奈可的肩上流淚。
奈可自然知道雲子在大都市中掙扎,日子並不如意,心情的開朗是表面化的,所以每當雲子哭的時候,他總是盡量輕鬆地道:“怎麼啦?陽光那麼好,又不愁吃,又不愁穿,應該快樂才是,為甚麼要傷心?”
雲子是一個性格堅強的女子,每當奈可這樣說的時候,她便會立時昂起頭來,將頭髮掠向後,同時也抹去眼淚,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來:“誰說我傷心了?我根本很快樂!”
在這樣的時刻,奈可便只有暗暗嘆氣。他當然知道雲子的話,不是她的心底話,但是奈可自己既然沒有力量可以使雲子的生活真正幸福快樂,除了順著雲子的話打幾個哈哈之外,他也不能做些甚麼。
自從雲子的聲帶出了毛病,不能再歌唱之後,雲子有更多次對著奈可流淚的經歷,但是每一次,也都能及時地表現自己“並不傷心”。
在奈可認識雲子以來,從來也未曾見過雲子這樣哭過,雲子哭得這樣傷心,奈可張大了口,想安慰她幾句,但是喉嚨發乾,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他只是怔怔地看著雲子哭,過了好一會,他只覺得自己也想哭,但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哭,總不是很體面的事,所以他竭力忍著,聲音乾澀:“雲子,別哭了好不好?每一個人的生活都不如意,哭並不能改善生活的環境,別哭了好不好?”
雲子仍然哭著。
奈可又喃喃地說了很多安慰話,雲子仍在哭。
奈可一賭氣:“好,哭吧,看哭對你有甚麼用,有甚麼好處!”
奈可在這樣說的時候,根本沒有期望雲子會回答自己甚麼話。可是雲子卻突然開了口,她仍然在一面啜泣著,一面說話,她的聲音,也是同樣傷心欲絕,聽來令人心碎。她道:“至少我哭過,你連哭也不能隨心所欲,你也想哭,可是你不敢哭!”
雲子這幾句話,說得極其清醒,令得奈可一時之間、忘記了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不會講出那樣清醒的話來。在那一剎那間,他只是被雲子的話怔住了,想到了他自己。
無論在生活中多麼不如意,無論受了多少屈辱,無論為了活下去,做過多少自己不願做的事,無論在大都市的夜生活中打滾,多麼令人覺得自己的卑賤,可是正如雲子所說那樣,他連哭都不敢哭!
一想到這一點,奈可幾乎忍不住要放聲大哭起來。
可是也就在這一剎那間,他還未曾哭出聲,就陡地省起,雲子一定已經清醒了,不然不會講出這樣的話來!
剎那之間,他大喜過望,忍不住高聲呼叫起來:“雲子,你醒了!”
雲子說道:“我根本沒睡著過!”
奈可更加高興,跳下地,站著,揮著手:“我不是這意思,我是說,你從神智不清中醒過來了!”
雲子略為止住啜泣:“神智不清?我甚麼時候神智不清?我……倒寧願神智不清,可是我……我清清楚楚感到絕望,我不知道如何活下去,我覺得困倦,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樣…我……”
雲子還斷續講了不少話,但是奈可說,他沒有再聽下去,他只是向雲子作了一個手勢,示意雲子留在房間裏,他自己則打開病房的門,奔了出去,在走廊的轉角處,找到了電話。
健一是在半夜被奈可的電話吵醒的。他一聽到了奈可的聲音,便忍不住要破口大罵,但是他因為才打了一個呵欠,沒有來得及立刻罵出口,就已聽到奈可在叫道:“健一先生,雲子清醒了!雲子清醒了!”
健一陡地將罵人的話縮了回去,疾聲道:“甚麼?請你再說一遍!”
他居然在對奈可的對話中,用上了一個“請”字。
奈可又叫道:“雲子清醒了!”
健一躍起,將電話聽筒夾在頸際,一面已拉過褂子來穿上:“你在哪裏打電話的?快回去看著她,別讓她亂走,我立刻就來!”
健一放下電話,一面披著上衣,一面已出了房門,在門口胡亂穿上了鞋子。
“健一先生來得真快,他穿的鞋子,一隻是黃色,一隻是黑色的。”奈可敘述說:“那時,我在病房門口,等著他。”
奈可放下電話,回到病房,雲子仍然哭著,奈可道:“等一會,有一位健一先生要來,他是警方人員,不過人倒是──挺好的。他說你和一件重要的案子有關,嗯,好像是板垣先生的死──”
奈可說到這裏,偷偷向雲子看了一眼,想看看雲子的反應如何,因為他一直不相信板垣的死和雲子有關,板垣是雲子生活的保障,雲子不能失去板垣!
可是雲子一點反應也沒有,自顧自哭著。
奈可繼續道:“他來了之後,你只要照實說就是了,不會有事的,請相信我!”
雲子幽幽地道:“會有甚麼事?”
會有甚麼事呢?奈可也說不上來。
雲子不等奈可回答,又幽幽地道:“甚麼事,我都不在乎了!”她說著,抬頭望向窗子。窗上裝著鐵枝,月色很好。月色映得雲子的臉看來極蒼白,淚痕在閃著光。
雲子喃喃地道:“我還在乎甚麼事?還有甚麼事可以令我更痛苦、傷心?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活著幹甚麼,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
奈可聽得雲子這樣說,有點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才好,他想要安慰雲子幾句,可是卻又不知說甚麼才好,雲子向他望來,用的是一種相當同情的眼色,雲子這時的聲音,聽來反倒十分平靜:“奈可,你也該好好為你自己著想一下!”
奈可剛才曾被雲子勾起極度的悲哀來,因為驚異於雲子的清醒,所以才急急地通知了健一。這時,雲子的話,又令得奈可茫然,他除了嘆息之外,實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
為自己打算,奈可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小人物,實在沒有甚麼好為自己打算的地方。幸運不會突然降臨在他的身上,他所能為自己打算的一切,在大人物眼中看來,簡直可笑,那程度就像是人看到螞蟻在為一粒餅屑而出力一樣可笑!
奈可沒有說甚麼,只是伸手在臉上重重撫摸了一下,雲子忽然道:“你說的那個叫健一的警務人員,甚麼時候會來?”
奈可答道:“應該很快就到了!”
雲子道:“你到門口去等他,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奈可望了雲子片刻,伸手在雲子的頭髮上,輕撫了一下,這是奈可對雲子的一種親熱的表示,奈可知道自己是小人物,但同時,他也覺得自己比雲子堅強,所以常以長者的動作來表示他對雲子的感情。
雲子像經常一樣,略側著頭,奈可又嘆了一聲,雲子側頭的那種神情很美麗,她應該可以成為一個知名度較高的歌星,奈可想。或許,在經過了這件事之後,全日本都知道有大良雲子這個人,她如果再登上歌壇,可能會成為紅歌星!那麼,他──奈可──就可以成為一個紅歌星的經理人了!
當奈可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情相當振奮,順從地走出了病房,當雲子要他關上病房的門之際,他也將病房的門關上,就站在病房的門口。
當奈可站在病房門口的時候,病房的門關著。雲子在病房中做些甚麼,奈可無法知道。
據奈可的敘述是,雲子在那短短的一段時間中,十分平靜,因為他沒有聽到病房之中有甚麼聲音傳出來。
而那時候,正是午夜,即使在一個瘋人院中,午夜也是極其寂靜的,所以如果雲子在那時候,有甚麼聲音發出來的話,奈可一定可以聽得到。
奈可在病房門口並沒有站了多久,健一就來了!
健一來得極匆忙,兩隻腳上所穿的鞋子,都不同顏色,他在走廊中急步奔過來時的腳步聲,打破了寂靜。當他看到奈可在門口之際,他立即問:“雲子呢?”
奈可向病房指了一指,健一立時握住了門柄,在他推門進去之前,他回頭,問奈可:“你說她已經完全清醒了?”
奈可點著頭:“是的,全清醒了!”
接著,奈可猶豫了一下:“太清醒了,她甚至勸我為自己打算,以前,她從來也未曾對我說過這樣清醒的話。”
奈可最後那一兩句話,聲音很低,他不敢肯定健一是不是聽見,健一推開門,奈可想跟進去,可是健一卻立時用身體阻住了奈可的去路,冷冷地道:“對不起,我和雲子小姐要秘密談話,你在外面等著!”
“我可以堅持我也要進去的,”奈可在長途電話中的聲音,仍不免悻然:“但是,我也有自尊心,我忍受不了人家對我的輕視,不讓我進去,我就不進去好了,所以我立時退開,門在我的面前關上,健一君進了病房。不過,我實在應該進去,因為我如果跟進去了,至少可以知道在病房之中發生了一些甚麼事,而不是只聽到病房中傳出來的聲音。”
由於奈可被拒在門外,所以,健一進了病房之後,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奈可不知道。奈可只能聽到自病房中傳出來的聲音。根據傳出來的聲音,雖然可以判斷發生一些甚麼事,但卻無法肯定。尤其是,奈可聽到的聲音,包括一些對話,簡直不可解釋。
病房的門才一關上,健一的話語就傳了出來,健一的語聲是充滿了驚詫的:“天,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
健一的話說了一半,就陡地停了下來,接著,便是“砰”地一聲響。
據奈可說,“砰”地一聲響,他知道那是病房中唯一的一張椅子翻倒的聲音,可能是健一走得太急,絆倒了椅子。
接著,又是健一的語聲:“你們……你們是怎麼一回事?你們──”
據奈可說,他當時奇怪之極,因為健一傳出來的話中,從開始起,到這時為止,總共才不過講了兩句話,而在這兩句話之中,他一共用了四次“你們”。
“你們”本來是很普通的詞,每一個人在對著超過一個人說話的時候,都可能重複地使用很多次。但是奈可卻清楚地知道,病房中,健一所面對的,只是大良雲子一個人,不可能再有別人。
對著一個人講話,就應該使用“你”,而不是“你們”。可是健一卻說“你們”!
如果不是剛才健一的語氣態度,對奈可的自尊心造成了太大的打擊的話,奈可一定會推開門去,看個究竟。不過這時,奈可卻並沒有這樣做,只是發出了一下低微的悶哼聲。
接著,奈可就聽到了雲子的聲音。
雲子的聲音很平靜,也很低,如果不是奈可平時聽慣了雲子的話,他可能聽不清那句話。但由於他和雲子太熟的緣故,所以他可以分得清雲子在說甚麼,雲子道:“你來了?你別急,我可以使你知道你要知道的一切。”
健一的聲音仍然很急:“那個職業殺手,是誰和他接觸的,你們──”
健一在這裏,又用了一個“你們”,不過這一句話也被打斷了話頭,接著,便是一連串的低語聲。
奈可可以肯定,那持續了足有十分鐘之久的低語聲,是雲子所發。不過由於語音實在太低,以致即使奈可和雲子如此熟稔,也不知道雲子究竟講了些甚麼。
這時,奈可的好奇心愈來愈強烈,他已經要不顧一切推開門衝進去了,可是也就在這時,他卻聽到,健一發出了一下如同被人痛擊之後呻吟一樣的聲音。
奈可陡地一怔,可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而在他還未曾定過神來之際,門打開,健一己走了出來。
健一出來,關上了門,在他關上門之後,雲子的一下叫聲,還自內傳了出來,那是雲子提高了聲音叫出來的,奈可完全聽得清楚。
雲子在叫:“你如果不信,可以去看一看!”
奈可向健一望去,一時之間,嚇得講不出話來。
“我對健一君,實在沒有甚麼好感,”奈可說:“我對一切警務人員,都沒有甚麼好感。所以,在我的一生之中,曾經起過不知多少古怪的念頭,然而決未曾起過一個念頭,想去同情一個警務人員。可是這時,我真的同情健一君,因為他的神情實在太可怕了!”
健一當時的神情,一定是真的可怕,在奈可的聲音中,猶有餘悸。他續道:“健一君的臉色,比醫院的白牆更白,他雙眼發直,身子在簌簌發著抖,當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臂的時候,即使隔著衣服,我也可以感到他手心中透出來的那股涼意。他平時呼來喝去,何等威風八面,可是這時,真比一頭待宰的羔羊還要可憐!”
奈可形容得很好,這就是健一當時的情形。
奈可被健一的神情嚇呆了,但他呆了並沒有多久,立時叫了起來:“健一君,你──”
健一失魂落魄:“她……她對我講了……講了……”他又望向奈可,忽然問道:“她也對你講過?她……她……對你講過?”
奈可全然莫名其妙:“講過甚麼?”
健一將奈可的手臂抓得更緊,以致奈可竟不由自主叫了起來,可是健一仍然不放手,不住地道:“她對我說了,還叫我去看看,她叫我去看看!”
由於健一在講這句話的時候,是直視著奈可的,所以奈可只好問道:“她……她叫你去看甚麼?”
健一道:“他叫我去看看自己!”
奈可不明白健一這樣說是甚麼意思。事實上,不會有人明白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我可以明白健一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看看自己”,意思其實極簡單,就是去看看自己,沒有別的解釋。
因為,我曾看到過自己,所以我明白。
奈可當時不知再說甚麼好,健一則突然之間,顯得十分激動,不但握著奈可的手臂,而且搖著,說道:“我一定要去看看自己!”
奈可實在給健一握得太痛,只好道:“好,那你就去吧,快去看看你自己!”
健一鬆開了奈可的手臂,急急向前走了兩步,然後又轉過身來:“奈可,你去不去?去看看自己!人不是有很多的機會看到自己!”
奈可悶哼了一聲,口中雖然沒有說甚麼,但是心中卻在暗駕:瘋人院應該多收留一個病人才對!當然,奈可在這樣想的時候,臉上的神情,對健一也不會太親切友善。健一倒沒有生氣,只是嘆了一聲,搖了搖頭,神情像是相當可惜。
接著,健一就走了。
健一還沒有走出走廊的盡頭,奈可便轉身推開了門,想去問問雲子,她究竟對健一說了些甚麼。當奈可推開門之際,看到雲子坐在床沿,神情十分古怪。
奈可說道:“健一問了你甚麼?”
雲子不答。
奈可又問道:“他對我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不知是甚麼意思,你叫他去看甚麼?”
雲子仍然不答,但忽然笑了起來,一面笑,一面道:“那不是我,是她!是另外一個女人,那不是我!”
雲子不斷說著,直到奈可抓住了她的手臂,用力搖撼著她的身子,她還是笑著,重複著那兩句話。
情形和以前完全一樣,不過加上雲子不斷的笑聲,根據神經病專家的意見,一個不斷癡笑的瘋子,比單是喃喃自語的瘋子,更加沒有希望。
健一在離開了奈可之後,做了些甚麼,奈可並不知道,但是健一的行蹤,有人知道。
有關健一離開了奈可之後的情形,當然不是奈可在長途電話中告訴我,是日後我一點點調查出來的結果。我知道這些經過的時間上雖然有差距,但這些事,在事實上接連發生,所以我加在一起敘述。然後,再接上奈可再遇上健一的情形,以使整件事,有連貫,不致中斷,便於理解。
健一出現在那幢大廈的入口處,注意到他的,是一個探員。自從鐵輪出現,死於亂槍之下之後,仍然有探員駐守在那大廈中。
那探員看到健一,迎了上去,招呼了健一一聲,健一的腳步很匆亂──照那探員的說法──匆亂的意思就是,不但走得急,而且不是依直線行進的,那情形,就像是喝了酒,不勝酒力一樣。
探員想去扶他,但卻被他推開了,健一直走向升降機,走進去。
“我這時才注意到,他──健一君的鞋子,一隻黃色,一隻黑色,而他又走得那樣匆亂。是不是健一君有甚麼意外呢?我自己想,”探員追憶當時的情形:“我想追上去看看,但是想到健一君是那樣有經驗的警官,不必多擔心,所以,我就沒有上去。”
探員雖然沒有跟上去,但是對於健一的行動,多少有點懷疑,所以他一直在注意,看健一是不是會有意外。半小時之後,健一還沒有下來,探員覺得事情有點不正常,他剛想進升降機時,升降機向上升去,到了十一樓,停止了片刻,又開始下落。
等到升降機到了大堂之後,門打開,健一走了出來。
探員追憶道:“健一君緊鎖雙眉,在自言自語,像是心事重重,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些甚麼。我又叫了他一聲,他像是完全沒有聽到,他逕自向外走去,步履比進來時穩定很多,可是也沉重得多,我看著他走出了大門,就沒有再注意他。”
這是健一在離開了奈可之後,逕自來到板垣、雲子幽會場所的情形,從時間上來說,健一是在離開了奈可之後,立即來到這幢大廈的。
健一在離開了大廈之後,又到甚麼地方去了?沒有人知道。但是估計,他可能回家,在家裏耽了一會,因為事後,在健一的住所中,有過匆忙收拾行李的跡象。這一段時間,約莫是一小時,因為在一小時之後,健一又出現在他的辦公室中。
當時天色還未亮,辦公室中,只有一個值日警官在,值日警官是健一的朋友,一看到健一,就道:“早!為甚麼那麼早?可是案子有甚麼新的進展?”
健一沒有回答,逕自向前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很匆忙,甚至沒有關門,所以值日警官轉過頭去,可以從打開的門,看到健一在辦公室中做些甚麼。
健一一進辦公室,就坐了下來,寫著信。
據那個值日警官說,健一一共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一揮而就,寫了之後,就放在桌上。第二封信,寫了三次才成功。寫好之後,摺起來,放進衣袋之中,然後,拿起第一封信,走出辦公室,交給了值日警官:“處長一來,就請交給他!”
值日警官說:“他不等我說話,就走了出去,等他走出去之後,我才看到信上寫著‘辭職書’,我吃了一驚,想叫健一回來,但是健一君已走遠了。”
健一離開了辦公室之後,又到醫院去見奈可。
他在辦公室寫的第二封信,就是寫給我的。也就是奈可在第一次長途電話中讀給我聽的那一封。
健一和奈可再度見面,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據奈可說,健一表現得十分快樂、輕鬆。奈可特別強調“輕鬆”,因為健一平時由於工作上需要他不斷思索,所以他的眉心,經常打結,但這時,完全沒有這樣的情形。
健一吩咐奈可,一定要盡快找到我,將這封信讀給我聽,他留下了一點錢給奈可作打電話之用。然後,他輕鬆地拍著奈可的肩,又打開病房的門來,將頭向內,看了一看。奈可也趁機跟著看了一看,雲子只是在傻笑,重複著那兩句話。
奈可最後道:“我看了健一君留給你的信,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所以根本不想打電話給你,想把健一給我的錢──留著做別的用途。可是第二天,就有兩個探員來問我關於他的事。原來他不單辭職,而且人也離開了東京,在車站,有一個他的同事遇見他,健一只說了一句他到他應該去的地方去,沒有別的交代。”
發生在健一身上的事,由奈可在長途電話之中,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
我在放下了電話之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呆了多久。我只是坐著發怔,思緒一片混亂。過了好久,我才將經過的情形,約莫理出了一個頭緒來,而值得注意的事,有以下幾點:
雲子曾忽然清醒,講了不少平時她不講的話,這些話,聽來很傷感(她對奈可講的)。至於她對健一講了些甚麼,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她曾叫健一去“看看自己”。
健一真的聽了雲子的話,我也相信健一“看到了自己”,健一看到了自己的結果是,留下了一封辭職信。
健一留下了一封給我的信,勸我別再理會這件怪事,就此不辭而別,到他“應該去的地方”去了。健一“應該去的地方”是甚麼地方,我一點概念也沒有。
事情的經過,就是那麼簡單,但也是那麼不可思議。
其中還有一點是相當難明白的,那就是健一在進了病房之後,曾不斷說“你們”。
而事實上,當時在病房內,健一面對著的,應該只有雲子一個人。
當我整理出這些來之後,我在想:我是不是應該回日本去找一找健一呢?找到了健一,當然可以在他口中明白很多事情,可是我只知道健一離開了東京,他到甚麼地方去了,全然不知。要在日本找一個日本人,不會比在印度找一個印度人容易多少,而我要找的印度人,我已經知道了他的身份,和他交談過,我更可以肯定,這個印度人一定會主動來和我接觸,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實在沒有理由離開印度到日本去!所以,在和奈可通了幾乎將近一小時的長途電話之後,我決定不到日本去,至少暫時不去。
我的睡意全消,在房中來回踱步,天色將明。我心中在想,在經過了專家那裏的交談之後,如果那位耶里王子,居然可以忍到天亮之前,不主動來找我,那麼,他可算是一個忍耐力極強的人了。
因為他在從事的勾當,是如此之神秘,這種神秘的勾當,通常是絕不想給外人知道的,而我明顯地已經知道了很多,他怎麼可能不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