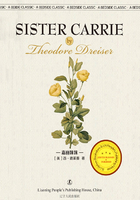良辰美景聽得我故意拿費力的名字開玩笑,覺得十分有趣,哈哈笑著,互望了一眼,從她們的神情上,看出她們立刻有了一個頑皮主意,可是她們並沒有說出來,只向我和白素一拱手,身形倏退,已到了門前,齊聲道:“一有結果,立刻來報。”
我忙道:“且慢。”
對付她們,有時,言語所用的詞彙太現代化了,未必有用,這“且慢”兩字,恰好用上,她們已打開了門,身形飄向外,又立時反閃了進來。兩雙大眼睛望定了我。一去一回,身形快絕,我看到她們的耳垂上,一左一右,各自掛著一雙式樣相當別緻的耳環,正在亂晃。
我道:“費力的研究課題一定十分專門,你們看不懂,自然也記不住,要帶些工具去,我有——”
不等我講完,兩人已搶著頭:“比起戈壁沙漠那裡來,衛叔叔,你那些所謂工具,都像是石器時代的東西。”
我怒瞪著她們,兩人故意作出害怕之狀,可是絕不準備改口。
我悶哼一聲:“好,有微型攝影機可以將文件攝下來嗎?微小到什麼程度?”
兩人嘆了一聲,叫起來:“天,還用攝影機。”
我惱怒:“哪用什麼?”
良辰道:“總有先進一點的吧,譬如說,圖文傳真。”
我更怒:“你怎知費力的地方一定有圖文傳真機可以供你使用?”
美景道:“我們可以隨身攜帶。微型,無線電直接傳送,掃描端子一掃而過,在戈壁沙漠處的接收機中,文件就清清楚楚出來了。”
我向白素望去,心中在想,在她們口中,那叫作戈壁沙漠的兩個人的能耐,可能是被誇大了的。
這種微型的無線電圖文件傳真機應該還只是實驗室中的東西,所以我要在白素處求證一下。
白素向我微笑,同時點了點頭,肯定了戈壁沙漠確有其能,我也不禁大是感嘆,因為要得到白素的肯定,並不是太容易的事:“當是天下之大,能人輩出,什麼時候,倒要結識一下這兩個人。”
良辰美景一聽,雀躍向前:“好極了,他們不知多想認識你,提了好多次,我們都怕挨你罵,連搭腔都不敢。”
我苦笑:“我哪有那麼兇。”
良辰指著美景,美景指著良辰,指的都是耳環:“這是他們設計製造的精密通訊儀,有著多種功能,譬如說,剛才白姐姐利用電話打了一個號碼,號碼是把訊號輸入他們住所的電腦,再自動傳向發射台,我們這裡,就收到了訊號。”
我吸了一口氣:“每一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通訊方式,例如溫寶裕是——”
兩人搶著回答:“三長兩短。”
“三長兩短”的訊號的一種方式,也是中國話中的一句俗語,不是很懷好意,她們當然是故意選定了這樣的訊號給溫寶裕用的,所以,一說了出來,就笑個不停。
我盯著她們耳下不斷搖晃的耳環看,六角形,不會比指甲更大,也很薄,微型電子儀器的體積可以小到這種程度,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兩人又道:“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好,你就由我們介紹給他們認識。”
我又好氣又好笑:“我成了獎品了。”
良辰美景一起叫:“誰叫你“隔著牆吹喇叭”——聲名在外,我們這就去進行。”
我那時,如果知道她們“這就去進行”是什麼意思的話,一定會提議她們明天早上再開始也不遲。
那只能算是一個小插曲,我也是直到若干時日之後,才知道當晚她們離開之後,做了些什麼。
那是後來,有一次,已成為世界著名私家偵探的小郭,忽然向我提起,說的時候,猶有餘悸:“真駭人,這世上奇才異能之士真多,若干天之前,半夜三更,我的一個職員在事務所當值,進來了兩個穿紅衣服的少女,行動快得和鬼魅一樣,立逼著要找一個——醫生的一切資料,那職員——一直以為遇到了鬼,嚇得發了三天燒,再也不敢當夜班了。”
我聽了自然只好苦笑,還不能表示什麼,只好道:“你那職員,也未免膽子太小了。”
小郭的神情十分嚴肅:“不是他膽小,我的事務所中,到處都有閉路電視,也一直不斷進行錄影。事後,錄影帶放出來一看,那兩個少女站著不動的時候,明麗可人,兩個人一模一樣,可是一動時——絕無可能有人可以移動得如此之快的,她們是——”
我笑了笑,知道他接著想說什麼:“不,她們不是外星人,有機會,會介紹給你認識。”
小郭望了我半晌,才道:“你認識的怪人真多。”
我立時回答:“包括閣下在內。”
良辰美景在離開之後,就在小郭的偵探事務所中,取得了費力醫生的一切資料。
費力醫生的研究所,由一個世界性的研究基金作資金支持。這一類的基金,對於有資格的研究者,十分寬容,付出大量的金錢供研究,三年五載,沒有結果,絕不會有半分怨言,而且也絕少過問研究者如何花費金錢。
費力的研究所,甚至連建築物,都是基金支出建成,在一個海灣的邊上,十分優美清靜。
這些,都是我在事後才知道的,具體一點說,是在那晚分手之後的第三天晚上。
那一天,從下午起,就顯得十分不正常。本來,秋高氣爽,氣候宜人,可是那天卻熱得反常,而且十分濕悶,所以,當下午三時左右,門鈴聲響,我聽到老蔡蒼老的聲音,在叱責來人時,心中在想:是老蔡愈老火氣愈大了呢?還是這樣的天氣,令人脾氣暴躁?
隨著老蔡的呵責聲,是一個聽來有氣無力的聲音在哀求:“老蔡,看看清楚,是我,我不是陌生人,我是衛斯理的老朋友了。”
老蔡的聲音更大,可以想像,他在大聲叫嚷時候,一定雙眼向上翻,不會仔細看看來人是誰的:“誰都說是熟人,我怎麼沒有見過你?”
我也在迅速想:“聲音很熟,可是一定曾經過了什麼非常的打擊,所以聲音變了,那會是誰?難道是陳長青學道不成回來了?不,那不會是陳長青。”
我不想老蔡繼續得罪人,所以打開書房門,走向樓梯口,向下望去,首先看到的,是叫汗濕透了襯衣,貼在來人的背上,而就在那一剎那間,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而且也感到意外至極。
我先喝止了老蔡:“老蔡,你怎麼連這位先生也不認識了?快請他進來。”
老蔡聽我一喝,才認真端詳了來人一下,也不能怪他老眼昏花,這時,來人抬頭向我望來,在大約不到十公尺的距離,打了一個照面。我和他極熟,可是要不是剛才聽到了他的聲音,也不容易一下子認出他來——如果那是他刻意化裝的結果,自然不足為奇;這人的化裝術極精,有一次,在中國西北,秦始皇墓地之旁,他化裝成了當地的一個牧羊人,就幾乎把我瞞了過去。
而如今,他絕不是化裝,而是由於不知道遭到了什麼事,以致連他的外形,也起了變化,他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這時滿是驚怕和疑惑,像是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一樣,而在我的想像之中,就算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了,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應該這樣驚慌失措的。
這時,他看來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他的襯衣被汗濕透,看來也不單是由於天氣悶熱,而是由於內心的極度恐懼和虛怯,所以才會那樣冒汗。
而且,他那種大量出汗的情形,可能已經持續了相當久,因為他的皮膚,尤其是臉上,呈現著嚴重缺水的情形,皺紋滿面膚色灰敗。
這時,他抬頭向我望來,眼神無助之至。他伸手想推開老蔡向前起來。可是非但未把年老力衰的老蔡推開,他自己反倒一個踉蹌,幾乎跌倒,老蔡忙伸手將他扶住,他就大口喘氣來。
這種情形,我看在眼中,大是吃驚,連忙飛奔上前,一面叫:“齊白,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齊白,就是那個獨一無二的盜墓專家齊白,在我記述的故事中,出現過許多次的齊白。
相信在看了我對來人的描述之後,再聽我叫出了齊白這個名字來,各位也一定大吃一驚了。要使齊白那樣堅強、勇敢、心底縝密、堅韌、具有高度科學現代知識的人,變成眼前這種樣子,一定有特殊至極的原因。
齊白最近一次在我故事中出現,是《密碼》這個故事,所以我立即想到,是不是那個故事中,那怪不可言的似人非人,似蛹非蛹的東西,已經發育成熟,變成了一個可怖莫名的妖孽怪物?
如果是,也的確可以把他嚇成那樣子的。
可是,和這怪物有關的班登醫生,帶著那怪物到勒曼醫院去觀察它的成長了,如果有了變化,我們曾約定,最快告訴我,而我沒有接到班登醫生的任何通知。
我一面飛快地想著,也來到了他的身邊,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背,他手心冒著汗,可是卻冰冷——可知他的情形,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他張大了口,聲音嘶啞,可是出聲不成語句。我把他拉到沙發前,推他坐下,他竟然一直抓著我的手背不肯放,我只好叫老蔡快點拿酒來,偏偏老蔡行動又慢,我真擔心齊白會在那一段時間中,昏死過去,再也醒不過來。
齊白這樣闖進來的情形,以前也發生過,可是他本身的狀況如此之差,我卻是見所未見,就算是當年,他被一個大國的太空總署追殺,像土撥鼠一樣,躲在地洞中的時候,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好不容易我從老蔡手裡,接過酒瓶,用牙咬開瓶塞(我的右手臂,一直被他緊緊抓著),把酒瓶湊向他的口,他總算知道張開口,可是當他喝酒時,酒卻一直流到了口外。
幾口酒下去,他整個人,算是有了一絲生氣,居然知道翻著眼向我望來,聲音一樣嘶啞,但總算可以說話了,他道:“我——見鬼了。”
我呆了一呆。
齊白是一個盜墓賊,根據“上得山多遇著虎”的原則,見鬼機會最多的,自然應該是盜墓人。
事實上,齊白經常在一些寬敞宏偉的古墓之中,流連忘返,不知道外面是什麼世界。
以他這樣身份的人,見鬼了,似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本來我著實被他的樣子嚇了一跳,但這時知道他不過是見鬼而已,雖然看得出那個鬼(一個或是一群),令他並不好過,但也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有點嫌他大驚小怪,所以用力摔開了被他抓住的手臂,同時,語音之中,也不免大有譏諷之意:“哦,是什麼鬼?大頭鬼?水鬼、長腳鬼?青面獠牙的男鬼,還是百般嬌媚的女鬼?”
齊白用那嘶啞的聲音叫:“我見鬼了,你知道嗎?我見鬼了。”
他並沒有怪我在諷刺他,只是又抓住了我的手臂,搖著,力量不大,十分虛弱,重複著他的遭遇,充滿了求助的眼神。我不忍心再去諷他,嘆了一聲:“看來,你遇到的鬼,沒給你什麼傷害。你現在的情形這樣差,多半是你心理作用。”
這兩句話,倒對他起了一定的鎮定安慰作用。他接過酒瓶,又喝了幾口酒;才大大吁了一口氣,雙手捧住了頭,過了一會,才道:“我本來一直不相信有鬼,可是這次——唉,這次——我真的見鬼了。”
我等他再說下去。
他再深吸了一口氣:“我不但見到了鬼,而且,還和鬼一起生活了三天。”
我皺起了眉:“請你再說一遍。”
齊白虛弱地重複:“我和鬼一起生活了三天。”
我大搖其頭:“鬼有什麼生活?人死了才變鬼,既不生,也不活。”
要是換了平時,齊白一定會因為我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在咬文嚼字而生氣,可是這時,他看來連生氣的精神都沒有。他只是改口:“好,就算是我和鬼——一起存在了三天。”
我心中仍充滿了疑惑:“照你現在的情形來看,你見到的鬼——應該你一見就逃才是,如何和他一起存在了三天之久?難道鬼有什麼力量,使你無法避開?”
齊白雙眼張得很大,眼神迷惘,像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且頻頻舔著唇。
我拿了一大杯水給他,他端起來。咯咯地喝著,又再喝了幾口酒作為補充,這才用比較正常的聲音問:“能聽我從頭說?”
我拍著他的肩頭:“當然,老朋友。當然。如果有什麼鬼,能把你嚇成那樣,我自然有興趣聽。”
齊白更正我的話:“我不是害怕,只是——感到無比的詭異。人對死亡那麼陌生,而鬼魂一直又是——虛無縹緲的,忽然有——一個鬼,結結實實出現在你的面前,那感覺——怪到了不可思議——”
我早就承認靈魂的存在,也進行過不少工作,去搜尋和靈魂接觸的方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但確如齊白所說,研究、探索靈魂、是一回事,一個“結結實實”的鬼在面前,又是另一回事。
(“結結實實”,他用了多麼奇怪的形容詞。)
我也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寒意,齊白望著我,一副“現在你知道了吧”的神情。
我向他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說得具體一些。
齊白喘了幾口氣,才道:“是一個老鬼——我的意思的,一個古老的——死了很多年——卻又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他的遭遇一定令得他震驚萬分,因為直到這時,他說話仍然斷斷續續,難以連貫,也使得聽來格外有一種怪異之感。
我也受了一定程度的感染,向他作了一個手勢:“慢慢說,從頭說起。”
齊白望著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接著又大口喝酒,又抿了嘴好一會,才道:“最近,我發現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古墓——”
一個故事,如果用這樣一句話來開始的話,應該是相當吸引人的,可是齊白如果要說一個故事,而用這樣一句話作開始,那卻一點吸引力也沒有。因為作一個盜墓狂,要是每隔三五天,他不能進入一座新的墳墓,只怕比常人三五天不吃東西還嚴重——他會因此死亡。
所以,發現了一座古墓,對他來說,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不過,也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說“十分奇特的古墓”。齊白“閱墓多矣”,能讓他稱為“奇特”,當然不簡單。
所以,我並沒有表示意見,而且我也想到,他將要作出的敘述,一定驚人至極,因為他曾如此震慄。
他停了一停:“這古墓,顯然是墓主人生前就經營的,在經過了傳統的墓道、墓室之後,是相當寬敞的地下建築,幾乎完全比照地上的一幢宅子建成,連內中的陳設,也和一幢舒適住宅所有的無異。當我進入的時候,一切都保存得極好,完全可以使用——”
他講得漸漸流利了起來,本來應該讓他說下去,不該打斷他的話頭,可是我卻無法忍得住最基本的疑問,所以我一揮手:“等一等,你說的那個古墓,是中是西在什麼地方?哪一個省?”
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可是齊白聽了,卻翻著眼:“那有什麼重要?”
我有點生氣:“當然重要,你說那座古墓十分奇特,有著地下住宅一切完善的陳設,那是現代北歐家俱,還是古羅馬的大理石浴池。可以是日本式,也可以是中國式。”
齊白抿著嘴,看來在考慮是不是該回答這個問題。
這令我更生氣,他帶著一條命,十成之中去了七八成的樣子來看我,宣稱他和一個鬼在一起過了三天,當然是要向我求助,可是這時,卻又吞吞吐吐,這的確叫人無可忍受。
我冷笑一聲,說話也就不客氣起來:“我知道,盜墓賊大都鬼頭鬼腦,自己找到了一座古墓,就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會湧進那古墓去,所以一定要嚴守秘密,睡覺也最好把嘴縫起來,以免說夢話。”
齊白漲紅了臉:“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
我冷笑:“怎麼不可以?我知道,那墓,離這裡多半不會太遠,不然,以你的精神狀態來看,你也根本支持不到我這裡,早已倒斃街頭了。”
齊白苦笑:“幹嘛生那麼大的氣?不是我支吾,是他不讓我說。”
我大聲問:“誰?”
齊白道:“他——那個——鬼。”
我更大聲道:“任何鬼,都曾經是人,任何人,都有名字,就稱他的名字好了,那個鬼的名字是什麼?”
齊白張大了口望著我,樣子像是白癡。他的這種反應,當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他的這種神情,竟然維持了一分鐘之久,這真正在考驗我的忍耐程度——近年來,我涵養好了不知多少,要是換了以前,早就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橫拖倒拽出去了。
過了一分鐘,他才搖了搖頭:“不能說,我答應了他不說的。”
我怒極反笑:“他是一個鬼,照你說則是一個老鬼,死了好多年了,是不是?多少年?”
齊白喃喃地道:“五百多年了。”
我一聲斷喝。“一個人死了五百多年,又變成了鬼,還有什麼可保守秘密的?他為什麼不讓你說出他的名字來,他還有什麼可怕的?你說這種鬼話來搪塞我,是想和那老鬼去永遠作伴?”
齊白臉漲得血紅,可知他的心中也十分憤怒,不到半小時之前,他連站也站不穩,此時居然霍然起立,氣咻咻道:“衛斯理,你這人,你這人——就是不講理,什麼都自以為是,我為什麼要騙你,是他不讓我說,我指天發誓,是他不讓我說,而當時,他要我保守秘密,我也曾發誓答應他。”他那樣聲嘶力竭,一副此情唯天可表的樣子,自然不會打動我,我“嘿嘿”冷笑:“像你這種人,發誓的時候臉不應該對天,應該對地。所有的古墓全在地下,你整天向地下掘,小心有一天,掘到了地獄去。”
齊白用可怕的神情盯著我,我則冷冷地望著他。過了好一會,才看出他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你不想聽我和那鬼在一起的經過了?”
我立即回答:“想,非但想,而且想得很。”
他忙道:“那就——”
我一聲大喝,打斷了他的話頭:“我要聽一個完整的故事,有確切的人名、地點、發生故事的一切詳細背景,而不要聽你在某時某地某古墓之中遇見了某個鬼。”
我一口氣說下來,齊白臉上紅了青,青了紅,好半晌講不出話來。
我又道:“看你剛才來的情形,你極需我的幫助,你要人幫助,就必須把一切都告訴別人,而不作保留。”
齊白嘆了一聲,坐下來,雙手托住了頭,一會,才道:“你錯了,我的情形不好是由於遇到的事太詭異,我說過了,我不是害怕,我也不要你什麼幫助,事實上也幫不了什麼。”
我給他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那你來找我幹什麼?”
齊白一字一頓:“想來和人分享——奇異的遭遇,或許,如果他願意,你也可以有機會——和他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