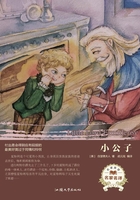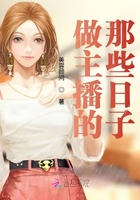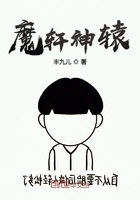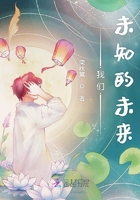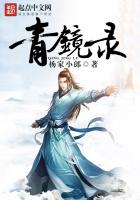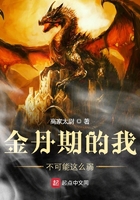若冷热两层空气之间的界限参差不齐,折射像往往会变形。美国探险家安德鲁斯曾一度看到形如巨大天鹅的异兽在戈壁沙漠的湖中涉水。从几百码以外遥望,它们宛如来自另一世界的庞然巨怪在来回走动,细长的腿几乎有15英尺长。安德鲁斯立刻叫探险队的画家,把这些不寻常的野兽画下来。他自己则蹑足向湖边走去。他走得越近,湖的面积缩得越小,野兽也变了形。肥硕的大天鹅变成了苗条的羚羊,安详地在沙漠上找草吃。热空气曾产生了水的幻影,由于热空气层高低不平,致使动物的形状变得稀奇古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交战时,海市蜃楼使英军炮兵不能开炮。炮兵眼前出现虚幻景物,把敌军阵地遮盖起来。英军司令部在报告炮轰时说:“由于海市蜃楼作祟,战事不得不暂时停止。”
1798年,拿破仑的部队在埃及也碰到过海市蜃楼。据说他的部队看见景物倒悬、湖泊失踪、平地变成棕榈树丛,纷纷跪在地上祷告,求上苍使他们免受世界末日的浩劫。远征军里至少有一个人——法国数学家孟日,还能保持清醒,提出了科学上的解释,他们才明白其中奥妙。
南北极的海市蜃楼不同,靠近地面的空气十分寒冷,而上面却有一层较暖的空气时,蜃景便会出现。那时会看到遥远物体的形象移到天上。这些海市蜃楼往往有双重映像。例如,船只或冰山在风平浪静的海面漂浮,水中会有它们的倒影。在远处的人既能看到物体的形象,也能看到上方较暖空气层折射回来的倒影。这样的“双重曝光”式映像,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1912年在南极探险时已有正式记录。队员在南极内陆长途跋涉后回到岸边,看见补给船“新地”
号的双重映像挂在空中,上面是正像,下面是倒像,船上的炊烟正向相反方向飘出。虽然船本身遮在大山的后面,可是在蜃景里却可以看到船上一切很正常。
偶尔空气还要开些有趣的玩笑。巴黎上空有时会出现原物倒像的蜃景,那时埃菲尔铁塔便会在头上顶着它自己的一个倒像,给巴黎市添个奇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德国潜艇艇长在北美海岸附近,从潜望镜看到纽约的摩天大楼倒悬在他头顶上的天空,整个城市好像就要掉到海里的样子。据说那个困惑的艇长看到这种情景,下令仓皇逃向远处海中。
海市蜃楼不一定都是物体的真实形状。可能是放大的像,可能是缩小的像,也可能是变形的像,就如在哈哈镜前看到的歪曲形状,变形的程度随光线折射的空气层之位置和成分而异。蜃景中,北极海的一块浮冰会看似一座危险的冰山,一株棕榈树会缩成一片草叶,渔舍也会变为巍峨的宫殿。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拐角那边物体的蜃景。譬如说,若在覆冰峭壁之类的直立平面上出现寒冷的空气层而使光线折射,光线便会因折射而绕过峭壁。一个在北美珞矶山脉中行走的人说,因为自己遇到这样折射的蜃景,所以预先知道有一头熊藏在转过山脚的小路上。
“复杂蜃景”大概是世界最有趣的蜃景了,在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间的麦西那海峡以及日本富山湾上,偶尔可以看到。这种蜃景的名字出自意大利有关仙女摩根拿的海底魔宫的寓言。后来一般都用摩根拿这个名字代表各种各样的海市蜃楼。
复杂蜃景的出现,海水必须相当温暖,使接触海面那层空气的温度升高,更高处必须另有一层暖空气,于是形成两层暖空气夹着一层冷空气。这样一来,中间那层冷空气不但会产生双重蜃景,还能发生柱面透镜的作用,把物体的高度放大。
复杂蜃景出现时,各种各样的蜃景,正的、倒的、放大的、缩小的、变形的复像等,全都混杂在一起。复杂蜃景并不突然出现,出现之前,空中会先出现一片诡谲的云。如果麦西那海峡上空的空气很热,海上风平浪静,这片怪云里便会有一个美丽的海港市镇的像闪烁动。然后会有第二个市镇出现在第一个之上,还会有第三个,每个市镇里都有闪闪发光的高楼和宫殿。有时看来房舍似乎是在水面之下,据说那就是仙女摩根拿居住的地方。似乎还能看见街上有行人,穿着宽大的白色衣服。
在麦西那海峡出现的复杂蜃景,究竟是什么市镇的折射像,直到今天还争论不绝。有人说那是西西里岛麦西那港口,有人相信那是一处海岸,岸上树木山石因放大和变了形而看似宫殿和高阁。更有人说那是意大利一个偏僻渔村的影子,通过海市蜃楼的魔力,变成一个美丽的市镇了。
不论那是什么地方,复杂蜃景始终是美丽无比的空中景象。尽管比别的海市蜃楼更多姿多彩,复杂蜃景也像别的海市蜃楼一样,是因光波穿过空气时所遵守的自然法则而造成的结果。
地球生命起源
从古至今,人类有许多未解之谜,人们对此也极为关注,生命的起源便是其中之一。
早在19世纪末,当人们通过反复实验,证明在正常条件下生命不可能从无生命物质转化而来,即证明生命自然发生说是谬论时,就有人把视线转向了宇宙空间。1907年,瑞典着名的化学家阿列纽斯(1859-1927)发表了《宇宙的形成》一书。他主张,宇宙中一直就有生命。“生命穿过宇宙空间游动,不断在新的行星上定居下来。生命是以孢子的形式游动的,孢子由于无规则运动而逸出一个行星大气,然后靠太阳光的压力被推向宇宙空间里。”与此同时,其他科学家也证明了这种压力的存在。因为在宇宙中类似太阳这样的恒星数不胜数,故类似太阳的恒星光是处处存在的。根据以上表述,我们可以说产生生命推动孢子运动的光压力在宇宙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极其普遍。阿列纽斯认为:孢子在星际空间里被光辐射推着往前走,直到它掉到或落到某个行星上,由此便可产生活泼的生命。如果那个行星上已有生命,它就和它们展开强劲的竞争;如果还没有生命,并且条件具备,它就会在那里定居下来,于是便使这个行星有了生命。
据他估算,孢子从火星飞向地球仅需84天,只需14个月就可轻松地飞出太阳系,若要飞到距地球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的比邻星(距地球4.3光年)也不过9000年。显然这些数字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阿列纽斯还认为,孢子有着厚重的外衣保护,生命力极其旺盛,足以忍受住遥远的、寒冷的、没有水分和营养的艰苦的星际旅途,而不丧失其复苏的能力。一旦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这些宇宙间的“流浪汉”来到了一个适宜生长的优质环境中,便开始了征服这个星球的过程。
许多学者支持阿列纽斯的这一理论。但是,由于他主张生命在宇宙中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抹杀了生命有过起源的问题,把生命起源的探索推向了不可追溯、不可认识的唯心领域,甚至为神创论者所利用。
近年来的一系列发现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生命天外来源说的极大关注与热情。首先人们注意到,地球上的生命虽种类庞杂,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具有相似的细胞结构,都由同样的核糖核酸组成遗传物质,由蛋白质构成活体。这就使人们产生了疑惑,如果生命果真是在地球上由无机物进化而来,为什么不会产生多种生命模式?其次,还有人特别注意到,稀有金属钼在地球生命的生理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钼在地壳上的含量却很低,仅为0.0002%。这使人不禁又要问,为什么一个如此稀少的元素会对生命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地球上的生命会不会本是起源于富含钼元素的其他天体呢?第三,人们还不断地从天外坠落的陨石中发现有起源于星际空间的有机物,其中包括构成地球生命的全部基本要素。人们还发现在宇宙的许多地方存在着有机分子云。生命绝不仅仅只存在于地球上,人们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再者,一些人还注意到,地球上有些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常周期性地在全球蔓延,而其蔓延周期竟与某些彗星的回归周期相吻合。于是人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有些传染病病毒来自彗星。如果这真有可能的话,那么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其他的生命孢子传入的可能。
近代对生命天外起源说的最重要支持,来自下述两个实验。
早在19世纪末,人们就发现,来自宇宙的星光,在到达地球的途中,由于被星际物质所吸收,而造成了星光的减弱。
然而,究竟是什么物质造成了这种星际消光现象呢?
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准确满意答复。近代利用人造卫星进行研究,把来自宇宙的星光展成光谱,发现在红外区域的3.1微米、9.7微米、6~6.7微米和紫外区域的0.22微米波长处均有强烈的吸收带。
这使我们有可能在实验
室里进行实物模拟,以此来确认究竟是什么导致的消光现象。
人们曾一度认为,造成星际消光的物质是石墨构成的宇宙尘,也有人认为是硅酸盐尘,还有的人说是带有苯核的有机物,但实际模拟的结果却将这些假说一一否定了。
不久前,英国加迪夫大学教授霍伊尔对此重新进行了一次细致入微的研究,他大胆地假定,宇宙中充满了微生物,正是这些微生物造成了星际消光。
根据这一新奇大胆地设想,他用大肠杆菌进行了模拟试验,结果不出所料,在紫外0.22微米的波长范围里,他找到了与星光相吻合的吸收带。
在霍伊尔实验的启迪下,日本京都大学的薮下信助教授等人对大肠杆菌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结果在红外区域的3.1微米、9.7微米和6~8微米均找到了相似的吸收带。
但在紫外区域减光曲线则与霍伊尔的结果稍有偏差,减光曲线的峰值不是在0.22微米,而是在0.9微米。薮下等人认为,一个原因可能是大肠杆菌在宇宙中也许会有一些不同于地球的特征,从而造成了这种细微的差别;另一个原因能是空气中的氧气也会吸收紫外线,也许是氧气造成的干扰。
因此他们开始着手准备到“空间实验室”中去进行这一实验。
1985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彼得·威伯等的实验结果。他们把枯草杆菌置于模拟的宇宙环境中,即在气压低至七亿分之一个大气压的高真空条件,温度为10K时,进行紫外线照射。
结果发现枯草杆菌具有非常强的耐受能力(比在高温条件更能经受得住紫外线的照射),其中有10%可存活几百年的时间。如果枯草杆菌不是置于高真空条件下,而是置于含有水、二氧化碳等的分子云内,则其存活时间可达几百万到几千万年,因此他指出:这种“云”足以在明显短于枯草杆菌平均存活时间的范围内,从这个星球移向另一星球,从而把生命的种子撒向四方。
经过一次又一次细致的调查研究,生命起源学说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科学家们正在进一步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相信终有一天会解开这个谜。
地球物种起源
那时是1835年的3月,生物学家达尔文第一次率队勘察崎岖的秘鲁群峰。
在登上安第斯山脉西面险峻的山坡道路,进入一条狭窄弯曲的小径时,骡队停下来休息。达尔文眺望动人的景色,嵯峨的顶峰,深邃的涧谷,在晴空中盘旋的巨型秃鹰。突然间,附近一面岩壁上的小发光物体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走近细看,原来是一枚海贝。接着又看到无数贝壳,从同一条石灰石夹层凸出来。
达尔文迅速下了骡子,着手撷采贝壳。他忘记了那里海拔一万三千英尺左右。骡夫一直在抱怨天气寒冷,他也因空气稀薄而喘气。这位生物学家若能在那里停留几天,一定会有极大收获。
可惜当时是南半球的夏末,如果开始降雪,这个在安第斯高山的恶劣环境下备尝艰苦的勘察队,就会被困。
达尔文采集贝壳化石时,发现其中有些与以前在太平洋海滩上采集的相似。在过去某个时期内,这些贝壳大概都沉在海洋底下。由于某种不详的隆起过程,从前是低洼的洋底,竟然升到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处。当时的地质学家一直以为,安第斯山脉是由火山喷出的熔岩造成的。达尔文推断,并不是全部如此。今天,我们晓得达尔文的说法很正确。慢慢漂移的地壳板块互相摩擦,在许多地域弄皱了洋底,还把洋底向上推,沿着几个大陆的边缘挤出了几条大山脉。
达尔文在这座高山采集的化石,促使他改变对地球年龄的看法,最后也改变了世人对地球年龄的看法。达尔文知道,带有贝壳的沉积物,从海底升到山巅,必须历经亿万年时间。达尔文也知道,安第斯山脉的贝壳绝非特殊例子。
在阿尔卑斯山脉和其他山脉,以前也发现过类似的化石。
在某种意义上,藏在岩石里的化石,可视作过去年代的地质岩,记录着地球历史的年代递变,每一代各具其特有的生物体型。只要没有剧烈扰动,带有最老年贝壳的最老年沉积岩层,就会被压在任何沉积层系的底部。带有较幼年化石的较幼年海洋沉积物,必会沉积在洋底较老年岩层的上端。如果这些地层未曾变动,其年代顺序就如书中的页数那样排列分明。
化石除说明过去的地质变化过程外,还是地球上绝种生物的实证。自古以来,无数生物的遗体沉积在海洋底下,虽然多半会腐坏,但许多有坚硬肢体,它们嵌入洋底的砂砾、沉积物和粉沙内,得以保存下来,还深埋在不断沉积海底的其他有机体残骸下面。在陆地上,生物化石保存在原油坑、藓沼、沼泽、洞穴、河床、冰原等地。
达尔文在安第斯山脉有所发现前的时期,许多人早在地球各处发现过贝壳和骨骼。古希腊人曾在离海滩极远的内陆捡到海贝,因而推论海洋过去必曾一度涌至那片陆地。有时候可能发现类似庞大野兽骨骼的大碎块,希腊人却只认为那是神话中的怪物。
此后若干世纪内,人类在干燥的陆地上,陆续发现海洋生物的化石遗迹。
但是很少人晓得希腊人对过去海平面改变的解说,更少人同意希腊人的说法。
有些博学之士相信,化石是外来异物,从其他星球降落地球的种子长成;另一些学者坚持说,化石必是偶然在地里形成的生命拟态;还有些思想家推论,化石是魔鬼的杰作,埋在地里以愚弄好奇的人类。
在17世纪的欧洲,化石遗迹引起的谜团,有一种新的意义。教会学者看到圣经出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译解,甚感震惊。当时维系社会与宗教所凭借的,是长期公认的圣经威权。宗教领袖为了维护这种威权,便着手以当代的科学方法证明神迹,特别要证明创世的记载确有其事。拿科学的事物来支持圣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