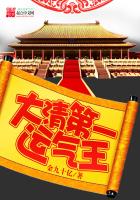临离别时,萝拉又跟我蹭蹭鼻子,轻声对我说:“我以前去过印度,那儿真的很美。我希望你能到达印度!”
“那你为什么没留在印度?”我困惑地追问,不理解她怎么能离开这样一个天堂。
“如果你自己的内心不美,不论你在哪儿,都不会觉得那里美好。”萝拉回答着,眼睛里涌起了泪水。她在哭之前就转回身,向森林走去,并对小动物们喊:“我们现在唱‘今天没有牛奶[19]’!”
等到森林里响起动物乐手们的欢呼声,我们也踏上了穿过田地的道路。我们全沉浸在新发现的真相带来的震撼中:我们竟然没有扑通一声掉进无尽的牛奶里。我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默默无语地走了几分钟,然后踏上了一条横在我们面前的路。这条路的路面坚硬得极不自然,它的灰色看起来也不自然。太阳高高悬在空中。在阳光的照射下,路面在我的蹄下散发着舒适的温暖。如果我当时就知道,我所站立的地方,被人类冠以如此不诗意的名字——“公路”,我肯定就不会感到如此惬意了。
“那么,”苏西慢腾腾地问,“去印度应该往哪边走呢?向左还是向右?”
我向贾科莫投去求助的眼光。他沿着灰色地面跳到一个黄牌子前,牌子离我们有几头牛身长总和那么远,上面画着我们看不懂的人类符号。公猫对着牌子观察了片刻——他看起来好像真能破解那些奇怪的符号似的,然后跑回来向我们解释:“我们还要再走十五千米,一直到一个名字叫库克斯港[20]的地方。在那儿我们等待开往印度的船。然后我想办法把你们偷渡到船上……唉,我说得越多,越觉得这个计划太疯狂……”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我们关于这个疯狂计划的问题说出来,比如“什么是船?”“什么是偷渡?”或“什么是库克斯港?”就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这和拖拉机的音律不一样,”小红萝卜说,“这个东西发出的音律是‘呼姆——呼姆——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姆’,强有力多了,也快多了。”
“Attenzione[21]!”贾科莫喊。
我们没任何反应。
轰隆声更响了。
“Attenzione!”公猫又喊了一遍。
我们依然没反应。
“我喊了‘Attenzione’,你们没有听到吗,你们这些愚蠢的母牛?”
“是,听到了……”小红萝卜首先开口说。
“……可是,我们不知道‘Attenzione’是什么意思。”希尔德把小红萝卜的话补充完整。
“另外,”苏西解释道,她因越来越响的噪音而有些气恼,“我们不是愚蠢的母牛,至少我不是……她们几个有一点……尤其是萝乐……”
“汽车!”贾科莫喊。
在我们前方,我们看到一个与拖拉机有几分相似的东西正向我们冲过来,速度快到不可思议。那里面坐着一个女人,她看到我们露出恐惧的表情,至少和我们的恐惧一样多。
“去那里面!”贾科莫大喊一声,一头冲跳进路边的一道沟里。
这个汽车看起来非常强壮结实,因此,我认为这一跳着实是个好主意。
希尔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比我快一蹄子,已经跳进了沟里。
贾科莫哭号起来:“你砸到我身上了……你的屁股就坐在我脸上!”
希尔德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小红萝卜也紧跟着跳了出去。现在是希尔德开始大叫:“嗷,现在我也被砸到了!”
贾科莫呻吟:“我还埋在你身下呢。再跳上来一头母牛,我就要像我的老朋友莫斯小姐一样扁平平了!”
本来我也想直接冲出去,跳到我两位朋友身上的,但是苏西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马路上,惊恐地盯着疾驰而来的汽车。
“苏西!”我冲她喊。
这头蠢牛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出于深深的恐惧,她像被死死冻在路面上一样。那个东西马上就要撞到她了,而她肯定没有命大到能在这样的碰撞中活下来。
我低下头,冲过去,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角抵进她屁股里。
“啊!”她大叫一声,直接蹿进那条沟里,正压在希尔德上面的小红萝卜身上,而贾科莫还被压在最下面。他现在哀呼着:“嗷呜,简直太完美了。”
最终我也赶紧跳了进去,“砰”的一声砸到苏西身上。苏西大叫起来,她身下的小红萝卜痛苦呻吟着,小红萝卜身下的希尔德也唉声叹气着,最下面的贾科莫痛骂:“下次我只跟兔子一起旅行!”
汽车从我刚刚跳离的地方呼啸而过,这时我们这堆砸在一起的牛也摔落散开了。我挣扎着爬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头从沟道里探出来张望。另外几头牛也学着我的样子观察着外面。这条路上飞驰着很多这样的汽车,一部分比刚刚第一辆大一些,甚至有几个后面还拖着小房子。
“那些是荷兰人。”贾科莫说,但是仅仅靠着这么一句解释,这一切并没有变得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
那些汽车显然让小红萝卜和苏西感到极其恐惧,每一辆汽车疾驰而过时,她们两个都吓得浑身发抖。勇敢的希尔德对这些快速的东西也感到厌恶:“跟这些东西发出的臭气相比,屁叔叔散发的简直是野玫瑰的香甜。”
因为我也有点害怕,所以我问:“谁赞成我们再找一条别的路呢?”
整个旅途中,所有的牛第一次意见一致。
可是,贾科莫反对:“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路穿过文明,非常抱歉。”
“这让我感到很难过。”小红萝卜叹息道。
“我也是。”苏西气呼呼地说。
“不管‘文明’是什么,”希尔德苦闷地说,“我现在就已经恨它了!”
这是我们几头母牛在这次旅行中第二次意见完全统一。
我们不情愿地踏上走进“愚蠢的文明”的大路。当然,我们并不是走在贾科莫称为“公路”的地面上,而是走在它旁边的草地上。我们左边是马路,右边是田地,夹在它们之间的狭窄草带,窄到我们只能一个跟着一个,纵队前行。苏西对此并不十分满意:“好,真棒,现在我可以好长时间一直盯着萝乐的肥屁股啦!”
我还从来没有过像这一刻如此地希望我肠胃胀气。
为了不让我们队伍的气氛变得更糟,我决定不理睬苏西的放肆。然而在队伍最后面,紧跟着小红萝卜的希尔德却帮我反击了:“我愿意看你的屁股,苏西。”
“啊,是吗?”苏西惊奇地问。
“当它陷进荨麻堆里的时候!”希尔德嬉笑着说。
“我愿意看你掉进马蜂窝里的屁股。”苏西回击道。
“我想看你陷进蜂蜜里的……”
“这并不糟糕啊。”苏西不解地问。
“……一群蚂蚁堆上!”希尔德把她的句子补充完整。
她们俩像山羊一样相互挑衅着(山羊对待彼此真的很恶毒,他们一天天咩咩着相互辱骂,我们牛真觉得这不可想象),我观察着汽车里的人们,他们全都吃惊地盯着我们。因为看到我们而感到高兴的人,只有几个,就是那些小小的“人犊子”。他们挥舞着小胳膊,手指着我们,开心地笑着。看着这些小家伙,我根本不能想象,他们会吃掉我们。他们看起来也似乎丝毫无意这样做。这些年幼的人类不可能是吃牛的怪物,不是吗?
“他们根本不想吃掉我们。”我对坐在我头上两角之间的贾科莫说。他的腿几乎已经痊愈了,但是他还不想走路。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好像挺享受被我驮着走路的。
“大多数人不会自己去杀牛。他们从来没见过死牛。他们只吃你们身体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不会想到,自己正大快朵颐的食物,曾经也是一个生命。”
这种行为听起来不仅荒诞,而且变态。
“我想,如果看到你们是怎样被宰杀的,大多数人应该也不会吃你们了。”
这就使得人类的行为变得善良一些吗?大概没有吧!人类教育他们的后代去食用其他的生灵,这简直不可理喻。如果我有一头小牛犊,我一定会教他尊重每一个生命——除了苏西。
“你们牛只需要对一小部分人感到害怕,”贾科莫解释道,“农民、屠夫、Sodomisti……”
“Sodomisti?”
“嗯,就是那些与动物欢爱的人……”
“我根本就没问!”我打断他,同时也一点都不奇怪,这个概念里含着“Mist”(粪堆、垃圾)这个词。
在我看来,人类一分钟比一分钟更阴森恐怖。关于他们,还有多少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我还不知道,并必须去了解的呢?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呢?光是在这些汽车里,就已经难以想象了。
我正苦思冥想时,身后的苏西问:“我们快到了吗?”
“不呢。”贾科莫回答。
过了一会儿,苏西又问:“我们快到了吗?”
“不呢。”公猫说,这次有些被触怒了。
还没一分钟,苏西又问:“现在呢?”
“不!”
“但是我们马上就到了?”
“如果你再这样问下去,你永远都不会到了!”
“你怎么弄死一头母牛呢,小猫仔儿?”苏西挑衅地问。
贾科莫从我头上爬下来,走到我臀部——我转过头去,为了能看到他要做什么——他在苏西的鼻子跟前“唰”一下伸出爪子:“就用它。”
苏西战栗了一下,努力保持镇定:“好,好,我可不想在眼睛上受这么一下。”
贾科莫冷笑:“不,小姐,你肯定不想。”
他转回身来,又微笑着在我背上保持着平衡走回到我头部,坐在我的两角之间。他的冷笑让我感到一阵寒战。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他是一只温顺可爱的公猫,但是现在我感到,他也可以变得很危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是一位毫不犹豫就会去伤害其他动物的主儿。刚想到这儿,我就不禁想到了老狗和我的噩梦:如果连一只有着这样利爪的公猫都差点被老狗杀死,我又能靠什么来抵御他呢?虽然那只是个梦,老狗只是在梦里想杀死我,但是如果这个梦里藏着对未来的真实预言呢?如果我确实将再次遇到这头怪物般的猛犬呢?这个可怕的想象让我在盆腔处感到一阵抽痛,有一点像来例假时的疼痛,但是又很不同。
苏西的声音让我从沉思中醒来:“公猫,我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吧。”
“哎呀,你又要问,我们是不是快到了?”贾科莫戏谑道。
“不。”
“好,那你想问什么?”
“还很远吗?”
贾科莫大声长叹一口气,然后在我的两角之间蜷缩成一团,悲哀地说:“到印度时我一定成酒鬼了。”
一个“人犊子”从一辆汽车里使劲扔出来一个苹果核,砸到我背上——看来那些小家伙也不都是可爱的。我目送着那辆汽车,不禁自问,如果那些人不得不使用汽车来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双腿,那世界到底得有多大呢?地球想必比我曾经设想的大多了,只是,到底有多大呢?忽然,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可怕的怀疑,我怀疑,直到我们“到了”,还需要很久。
“你说,”我轻声问公猫,为了不让其他几头牛听到,“是不是我们走三天也到不了印度?”
“教皇是天主教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
“当然啦,印度还远着呢。”
“四天?”我追问,希望这个“远着呢”并不遥远太多。
“还要远。”
我咽下一口唾液,这样一个行程我们母牛能坚持几天呢?八天?九天?最多十天?
“比十天还多?”我谨慎地问。
“我估计,还要多一些。”
“‘一些’是多少?”我小心地继续追问。
“哦,可能三个满月吧。”
“三个满月?!”我惊慌地叫。
另外几头牛一起诧异地看着我。
“什么三个满月?”希尔德问。
“呃,”我赶紧胡编乱造,“贾科莫说,在印度能看到三顶圆月。”虽然这个托词很笨,但是我一时也想不到其他的借口。我不能对她们说,到印度还要走那么久。如果我说了,她们全会丧失希望,就像我刚刚一样。
“三顶圆月?”希尔德追问,“这怎么可能呢?”
“奈雅在那里往天空上多甩了些她的奶酪。”我继续撒着谎,把母牛女神也扯了进来,尽管我已经完全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存在了。
小红萝卜天真地认可道:“她乳房的生产力可真强。”
不管怎么说,她们暂时接受了我的信口开河。但是苏西还是过一会儿就絮絮叨叨地问:“还有多远?”“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或者:“蹄子都冒烟了,可怎么办呢?”我不禁自问,这三个满月我们几头牛该怎么相处呢?更不要说在到处是人类的世界上生存下来了?在希望要彻底消失殆尽时,我的盆腔区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抽痛。这大概不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抽痛,估计也不是我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抽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