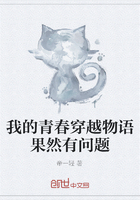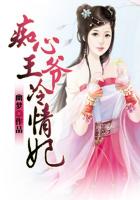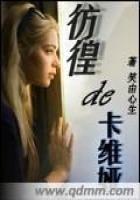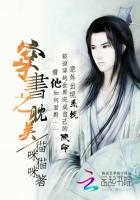三、与绝望做斗争
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有一篇短篇小说《墙》,它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描写“我和另一个麻风病人”在黑夜里爬行于黑沉沉的大地上。突然,一堵顶天立地的墙出现在面前,把天空和大地一截两半。他们“拼命用自己的胸膛去冲撞这堵墙,伤口滴出的鲜血把这堵墙染得通红,但墙却依然静静地耸立着,岿然不动”。于是,人与墙的搏斗开始了,这个“我和另一个麻风病人”夜以继日地“以头撞墙”,只有黑沉沉的夜,“把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傲慢地岿然不动的墙以及一小撮战战栗栗的可怜人照得通亮”。有的人“把墙视作朋友,紧紧地贴到它身上,把它当作靠山,求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墙却一直是我们的仇敌”。在与墙搏斗时,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的不幸,有哭泣、有鲜血、有愤怒、有诅咒,也有欢乐和爱情。然而,我们与墙的搏斗注定是无望的,这个“我”只能说:“我们人很多,我们的生活都不堪忍受。就让我们用尸体铺满大地吧。”他们同其他的搏斗者一起,每隔一定时间就用前额撞一次墙,他们感到,自己虽然在搏斗中渐渐死去,但自己“是永生的,恰如上帝一样”[1]。
安德烈耶夫笔下的墙,象征意义很丰富,我们可以作出无穷遐想。但真正提出“以头撞墙”和“绝望哲学”的却是另一个俄罗斯犹太大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在20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作为一位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非常令人瞩目。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理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的苦难与绝望,其一系列思想对我们颇具启发性。
舍斯托夫非常关爱俄罗斯作家,尤其推崇契诃夫。舍斯托夫指出,尽管有人指责契诃夫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倒在地板上,哭喊着,并以头撞墙”,但面临绝望的尴尬境地正是人类真正的处境。真正的哲学不是源于惊奇,而是源自绝望,人只有面临绝望的深渊,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据说,舍斯托夫大约在12岁时,曾被一伙人绑架为人质,以向其父勒索巨款。然其父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没有答应绑匪的条件,以致舍斯托夫被绑架半年之后才被释放,但是这半年中的生死考验,无疑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打下终生难忘的烙印,成为他产生“绝望哲学”的潜在动因。再加上他身为犹太人,从小身处异族文化圈的“边缘人”处境。对于俄国人,他是犹太人;对于法国人,他是犹太人。终生的无家可归和漂泊流亡,使他深悟生命的况味。在舍斯托夫看来,现代人从来没有如此软弱无力和疲惫不堪。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害怕孤独与黑暗,畏惧死亡与深渊,人类的苦难比海洋中的沙子更沉重,人的生命仍比所有的客观规律价更高。他关注着个体的人,关注着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绝望与呼告,孤注一掷地走向《圣经》,并向先知和上帝发出呼告,希望通过信仰来战胜绝望和宿命。正如他在《论绝望与可能》中所言:“不要讥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如果谁有即便是芥粒大小的信仰,那么他就能移山填海。只有纯粹的人类勇敢精神,才能因为荒谬而控制一切有限。这就是信仰的勇敢精神……信仰并且只有信仰,才能摆脱人的罪孽;只有信仰,才能使人从必然性真理的支配之中脱离出来,而必然性真理掌握了人的知识是在他尝了禁树之果以后;只有信仰才能赋予人以勇敢无畏和力量,去正视死亡和疯狂,而不是优柔寡断地向它们顶礼膜拜。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敞开了拯救之路……归根到底只剩下一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这时才敞开了信仰之路。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上帝。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2]
德国犹太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生前默默无闻,但自杀后由于其友人舍勒姆、阿多诺[3]和阿伦特[4]等人的大力宣扬,逐渐声名鹊起。他是一个生长在德国、用德语阅读和思考的犹太人。卡夫卡[5]将这种土生土长的德国犹太人心理描述为,后腿依然站在父辈的犹太教上,但前腿却找不到新的立足点。不理解这种处境和心态,就无法理解本雅明、卡夫卡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无法用德语表达出这种在德国文化环境中所感到的孤立、排斥与他乡之感,但除了德语,他们又无以选择。因此,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可能不写作”,因为只有通过写作才不会泯灭他们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认为他们使用德语是“公开地和隐蔽地甚至可能是忐忑不安地侵犯别人的财产。这不是正当获得的,而是偷来的,顺手捡来的。即使不会被挑出任何语言错误,而它依然是别人的财产”;“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写作”,因为没有其他可供使用的语言。甚至“还可以补充上第四种可能,即不可能写作,因为这种绝望不是可以通过写作来减轻的”[6]。犹太人问题在他们这代人身上看起来似乎不可解决,因为他们不想也无法“回归”犹太人的行列或者犹太教,因为他们对一切传统、文化和一切“归属”都表示怀疑。所以,可供选择的反叛方式只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种绝望。因为,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常常陷入一种困境,而且两者之间常常很对立[7]。
本雅明的身上有多重思想面孔:他学识渊博,却不是学者;研究语言理论,却不是语言学家;批判哲学传统,却不是哲学家;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的作品,却不是翻译家;他研读犹太教经典,却不是神学家。但反过来说,他又兼有所有这些身份。此外,他还有多种角色:“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甚至没有职业……”[8]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本雅明被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分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否定神学或文学解构主义的权威学者,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政治、宗教或学术的家园。”[9]而本雅明自己则认为,他身上具有人性与犹太性的双重性:“我是一个犹太人,并且,如果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而活着的话,我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犹太人而活着。”他认为,“犹太人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对我来说犹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思想的高贵承担者和代表者”。“当代思想文学的犹太人”,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犹太人”。[10]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战争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作西方文化的崩溃和技术与文明的胜利,本雅明则把它看作一场大火,以破坏性价值的名义威胁着吞灭所有资本主义文化。本雅明在战争期间发展的语言弥赛亚理论,和同时期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的神学弥赛亚无政府主义,都是在犹太文化哲学的潜在灭绝面前的表达。“这个时代没有一种形式允许我们沉默的表达。但是我们感到自己被无言所捕获。我们鄙夷文字表达的轻松不负责任。”[11]1916年,他在一封信中绝望地写道:“我们处在暗夜之中……战争威胁着从我们手中夺走一切,艺术、真理、正义。”“我曾经试图用言词和它(暗夜)搏斗,……但我随后知道了无论是谁,与黑夜搏斗就必须要抽走最深的黑暗,以便产生出光,在这一巨大的努力中,言词只是其中一站。”[12]1919年三四月间,本雅明和布洛赫相遇了,此时两人都开始把隐微的智识主义的语言作为世俗—神学的弥赛亚主义的表达。但是两人在政治领域有冲突,即内在于弥赛亚观念之中的伦理两难。虽然同是犹太人,但布洛赫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本雅明始终对政治抱有拒斥的态度,他的语言哲学是反政治的,他通过语言救赎反对马丁·布伯[13]的个人犹太教的思路关闭了通往行动的道路。同时,他还拒斥布洛赫的此世末世论和乐观的乌托邦主义,认为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一书存在着一种基督教与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混合。他拥护更加悲观的结论:“由于自然与孩子的缺席,人类注定要抵达灾难性的自我毁灭。”[14]但是,无论是本雅明还是布洛赫,都具有利奥·拜克所说的“弥赛亚式的反讽”:对救赎的确信和凄凉的悲观主义,因为这种确信要求“只有那些被这种悲观、这种嘲笑、这种抗议和这种反讽所感染的人,才是真正的坚守未来,并引导世界朝向未来更迈进一步的伟大的乐观主义者”。[15]语言是救赎的中介,但历史是灾难的剧场。
为了在“熟睡的忘却”之中不再感到痛苦,本雅明终于在德国民谣中找到一个“驼背小人”,他的深刻意图是将它作为一种传统,“既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16]也就是说,将在尘世中因等不到弥赛亚救赎而痛苦扭曲的人,变成快乐的驼背小人,因为“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就会消失(一位伟大的拉比曾说),弥赛亚并不希望通过暴力改变世界,而仅仅希望在其中做一点点调节”。[17]
之所以本雅明把这个“驼背小人”当作德国传统和犹太传统的交融,是因为他生存于此世,并不等待和盼望着另一个世界的到来。所以,他对生活在幻想中的人报以大声的嘲笑:
当我进入我的房间,
去铺我的小床,
一个驼背小人在那里,
笑得浑身打颤。
这笑声来自尘世之自然与无辜的生命对一切超验幻想的回答,所以,这个传统是德国式的笨重;但另一方面,嘲笑过后,他“并不希望通过暴力改变世界,而仅仅希望在其中做一点点调节”,所以,
当我跪在我的垫凳之上,
我想要祈祷,
一个驼背小人就在房间里。
他开始说:我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
也为驼背小人而祈祷。
“祈祷”不是企求拯救,而是祝福,完全尘世式的祝福,虽然保留了希望,但不再具有超验色彩,是完全没有神存在的人的世界的希望,表明了一种绝望,很难等到“弥赛亚”的拯救。后来,本雅明又讲了一则犹太人的故事:
据说,有一个信哈西德教派的村子,一个安息日的傍晚,犹太人坐在一家破旧的小酒馆里。他们都是村民,只有一个人谁也不认识,他看起来很可怜,衣衫褴褛,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有人提议,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愿望。头一个想有钱,第二个人想有个女婿,第三个人想有个木工刨台。就这样轮着说。每个人都说了,只剩下阴暗角落里的那个乞丐。在大家的追问下,他终于不大情愿,犹犹豫豫地回答道:“我希望,我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统治着辽阔的疆域,深夜躺下了,我睡在我的宫殿里,敌人从边界进犯,天还没亮,就已攻到了我的城堡前,城堡里毫无抵抗,我从睡梦中惊醒,连外衣都来不及穿,穿着衬衣就踏上了逃亡之路。我走过高山深谷,越过森林丘陵,一刻也不停歇,昼夜奔跑,直到我到了这儿,蹲在你们角落的这条凳子上,得救了。这就是我的愿望。”其他人都迷惑不解地互相看看。——“那你从这个愿望得到了什么?”有人问。——“一件衬衣”,这就是回答[18]。
这个故事令人称奇之处,不在于他的愿望是一件衬衣,而是他为了得到一件衬衣,所愿意付出的漫长而艰辛的过去,人只有在过去中才能把握自己,哪怕是彻底失败的过去,哪怕这个过去已经彻底成为过去,而不再可能重新获得,这个过去也不应该丢弃。这就是现代人对于传统的态度,或者说应该具有的态度。在这个时候,本雅明早年的弥赛亚已消失,物质满足已成了他心中的救赎之道。看来他是彻底绝望了。
1939年秋,虚张声势的战争[19]开始,本雅明被作为敌国公民拘留在一个法国营地。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拒绝了前妻邀他一起去英国的恳求,千方百计地寻求前往美国的签证。1940年5月,德军进攻法国,6月本雅明开始四处逃亡,起初去劳德,后来又到了马赛。8月份他终于在霍克海默的帮助下获得了签证,但是却找不到船只离境。接近9月底的时候,他试图与一群难民一道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却在波港遭到了西班牙边境士兵的阻挡。当天夜里,本雅明服食了过量的吗啡而身亡。第二天,同行的其他人安全地通过了边境[20]。
法国思想启蒙家、哲学家伏尔泰说过:“当一切希望都失去了,死亡成了一项责任。”对犹太人不应该是这样,当一切希望都失去时,他们又找到新的希望。即使在绝望中,他们也尝试为希望辩护,本雅明只不过是一个心急的犹太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是犹太人离开西班牙进入放逐的同一年,因为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犹太同胞寻找新的避难所[21]。哈西德教派是犹太人的一个主要教派,一天,一位伟大的拉比到乌克兰的一个村庄看望受迫害的教众。许多人向他谈起被屠杀的家庭、被活埋的孩子和被亵渎的葬礼。大师听着,摇摇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我知道,你们想要我痛苦地喊叫,绝望地哭泣,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不会,你们听我的,我不会。”接着,在一段久久的沉默之后,他还是开始喊叫了,并且越叫越响:“Gewalt, Yiden, zeit zich nit meyaesh!犹太人,为了上帝,不要绝望……犹太人,不要绝望!”在华沙的贱民区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然而哈西德教派的教众被催促——实际上是被命令——不要绝望!因为犹太人三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绝望是一场渎神——一个亵渎。
有一首名为“他们杀了他们的上帝”的诗非常有名,它描述了耶稣在东欧某村庄的出现。他在寻找他的兄弟——他在寻找他的人民。当他找不到他们时,他询问一位过路人,“犹太人在什么地方?”——“被杀了”,过路人说。“全部吗?”——“全部。”——“他们的家呢?”——“被毁了。”——“他们的教堂呢?”——“被烧了。”——“他们的智者呢?”——“死了。”——“他们的弟子呢?”——“也死了。”——“还有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也死了吗?”——“所有的人,他们都死了。”耶稣开始哭泣他的人民遭受的屠杀。他哭得那么痛心以至许多人都转身看他,突然一个农民喊道:“嗨,看他,这儿又有一个犹太人,他怎么还活着?”于是农民们扑向耶稣也把他杀了,杀死他们的上帝,以为他们正在杀死的不过是又一个犹太人。大屠杀的印记深深留在了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让他们开始绝望,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却喊出这样的声音:
当敌人疯狂时,他毁灭;当杀人者疯狂时,他杀人;当我们疯狂时,我们歌唱。[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