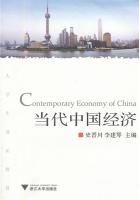如果脖子上的刺痛不是从“极度不舒服”转变成“真是要痛死人了”的话,我大概还会对“女人”这种用词更加惊讶一点。
“唉哟喂!”我大喊了一声,努力睁开眼睛想弄清楚这种痛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我看见了某种闪亮的金属。是不锈钢?或者是银器?而这块金属上正倒映着我疼得变了形的脸庞。
“回答我,不然我就扎穿你的脖子!”这个低沉的声音威胁说。同时,那块金属片扎得更深了一点儿。疼痛中的我稍稍闭了闭眼,咬紧牙关重新把眼睛张开,想看一看是谁在对我说话。我抬眼向上瞄去,而面前站着的是……班迪克斯?他身上竟然还穿着我为白马王子雷特罗画的衣裳,没有了胡子,但手上却拎着一把剑,抵在我脖子上的正是那把剑!
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反应大概和任何处于相同情况的人都一样,我问:“唉,你是不是脑子进了水啊?”
“这话是什么意思,女人?”班迪克斯反问。
不过,他倒是把剑从我的脖子上挪开了。疼痛感消退了下去,我可以顺畅地吸两口气了。
“说吧,女人,‘脑子进了水’是什么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你没脑残吧?”
“脑残?”
“你家踩轮子的仓鼠都还在吧?”
“仓鼠?”
“不然就是它们去你脑袋里放屁了,是吧?”我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谁?仓鼠吗?”
“爱谁谁啊!”
“为什么仓鼠会做这种事情?”
“不知道啊,”我回答,“也许因为你在它们面前也像现在一样神神道道的啊!”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仓鼠了。上一次见到还是在南部堡垒被围困时,我们在困境中以它们为食。”从班迪克斯脸上的表情来看,就好像曾经他的确被围困并陷入饥荒的境地。他表现得真实可信,不仅如此,他说话的语调也至少比平时低了八度。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他竟然在演戏方面有这么高的天赋。我的老天,这家伙昨天在他未婚妻面前想假装胃胀气时还露了馅呢,可现在却能让人以为他真的有着伤痛的过往。
班迪克斯把痛苦从眼中驱散,解释说:“而且,仓鼠也不可能在人的脑子里放屁。”
“呃……你说什么?”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杀掉我,接着,用斧头把我的脑袋劈开,然后仓鼠还得爬进去并且……”
“说得也太细节化了。”我打断了他。
“细节化?这又是什么意思?”
“你就别再装疯卖傻了!”我怒发冲冠。
“你胆敢对雷特罗·冯·阿曼坡用语不敬?”班迪克斯威吓地用剑指向我。
“如果你不把剑挪开的话,我还会用脚不敬呢。我会踹得你下半身需要开发援助。”
“你胆敢威胁雷特罗·冯·阿曼坡,女人?”他的剑举得更吓人了。
“洞察力不错啊!”
“没人可以威胁雷特罗·冯·阿曼坡!”班迪克斯的眼睛眯了起来,闪烁出冷酷的怒意。哪怕我的脑袋对我说“这一切不过是场游戏而已”,可我还是被吓了一跳,于是我缓和了语气,以免继续激怒他:“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但如果你能放下这把傻里傻气的剑,我会相当高兴的。”
“这是‘狼刃’,是永恒之王的最后一把剑。”他说得激昂高亢。
我着实吃了一惊。班迪克斯是从哪里知道我给这把剑取了这个名字的?既然说到这个问题,那么他又是从哪里知道我把王子命名为雷特罗·冯·阿曼坡的?解释只有一个:班迪克斯一定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偷偷看过我的小册子。出于某种原因(但愿我马上就能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他决定把自己打扮成雷特罗的样子,并为此刮掉了胡子。但是,他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套服装的?雷特罗的造型可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想要现做的话,光是按照我的模板去裁剪就得花一番工夫。而这样的服务项目只需要一个晚上就能办到吗?又或者,我以为这套造型是自己研究开发的,但实际上却是无意识地把《魔戒》《权力的游戏》,或者是某部与卡美洛相关的影片中的戏服画到了纸上。而班迪克斯在认出来之后,很快就找到了租借戏服的地方,同时还弄到了一把真剑以及可以塞到戏服下边的塑胶垫衬——因为那惊人的肌肉是不可能借助一大杯超剂量的蛋白粉混合饮料在一夜之间长出来的。可是,哪家戏服出租店大半夜里还开着门呢?不过,现在的首要问题并不在于戏服店的营业时间,而是——这见鬼的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对于这个问题,我充满希冀的拳拳之心怯怯地对我的理智说出了一个答案:也许……也许他做这一切是为了重新赢回我。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至少可以算是一次相当有原创性的尝试嘛。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解释吗?比如,雷特罗从我的画册子里活了过来……
那是当然啦,而且外面正漫天飘飞着粉红色的大象在欢唱《玛卡莲娜之歌》呢。
只有看多了漫画和奇幻小说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念头。那位从未真实存在过、因而也就永生不死的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如果把不可能的事情排除掉,那么剩下的就是真相了,不管它显得有多么难以置信。而在此情此景之下,显得相当难以置信的现实就是:班迪克斯想要让我回到他身边!
我的理智让我觉得这种推测很有道理。这真让人高兴得想先来一个前空翻,再来一个后空翻啊,而且是空中转体两次的那种。我的理智警醒地喊道:“亲爱的心,每当你快乐得做起体操的时候,总是会摔成重伤的呀。”而这时,班迪克斯的低沉声音打断了我的意识激流:“如果你现在再不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就用狼刃刺穿你。”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新造型很适合他。他的脸显得更加棱角分明,并且也比从前更有男子气概。刮掉胡子明显使容貌有了极大改善。每一个潮男都应该这么做,这样一来,世界也将更具美感。这一头长发(他是去做了接发吗)不仅很酷,而且颇具野性。简而言之,班迪克斯比以往要更加帅气了!
我决定加入他的这场“我要赢回娜莉”的游戏,于是说:“把你的剑放下,我就会告诉你这是哪里。”
班迪克斯犹豫了一会儿,把剑插回了剑鞘,要求我:“现在快说!”
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向班迪克斯,捧起了他的脸。
“你……你到底在干什么?”他惊讶地问。
“看上去像是在干什么?”我反问他,而我的嘴唇靠得越来越近。
“看上去,你像是要给我一个吻?”班迪克斯回答道,出人意料地显得有点胆怯。几乎让人觉得,他还从来没有被女人吻过。
“不是随便的一个吻,而是一个生命之吻。”我说。如果是普通的谈情说爱,这话就说得有点矫揉造作了,但我觉得,这非常适合班迪克斯定下的这种调调。当我的嘴唇就要印在他的唇上时,他惊恐地大叫起来:“放开我,女人!”然后一把推开了我。我吓得往后踉跄了几步、倒退时被绊倒在纸板唐老鸭的身上。在划拉着双手企图保持平衡却徒劳无功之后,我和纸板唐老鸭一起轰然倒地。
“你疯了吗?”我咒骂着。
“如果这里有谁疯了的话,那就是你!”班迪克斯震怒,重新拔出了剑,这回可不是游戏了。现在我真真切切地开始害怕他会伤到我,于是瞟向门口方向,想估算一下是否有可能逃出书店、跑到大街上去。这时,我的目光扫过了那本小册子,它和唐老鸭并排躺在漫画书店的破旧地毯上,翻开的正好是我画了雷特罗的那一页。
我急忙捡起这本老旧的皮质书册想好好瞧一瞧。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页曾被人调换过。没有任何精心剪裁过的痕迹,也没有新刷上去的胶水。这肯定、确定并且一定是原本的那一页。只不过,页面现在干干净净、空空如也,雷特罗仿佛真的是从纸页上一溜烟跑掉了似的。我忍不住看向窗外,可外边并没有粉红色的大象一边飞一边唱《玛卡莲娜》,也没有长着紫色斑点的大象,即便是普通的灰象也不见一只。只有一名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从门前走过,她看上去仿佛刚刚参加了美国政府承办的一场睡眠剥夺实验。
可是,这样的日常景象以及粉红大象的缺席没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因为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仍然在愤怒地质问:“你在干什么,女人?”
我抬头看向他。也许这并不是班迪克斯在用一把借来的剑指着我,也许这位就是雷特罗·冯·阿曼坡本人。
不,这不可能!这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王子!我真是昏了头。对于这空出来的页面以及我面前的这位斗士,并没有好的解释。也许我在浴缸里把自己弄得缺了氧,以至于伤到了大脑。没错,正是这个原因,绝对是我产生了幻觉!
不过,我一直都以为幻觉这东西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应该更有跳跃性,色彩更浓烈一些,更扑朔迷离一点。如果是电影里的人物开始幻想,那么镜头至少会摇摇晃晃,画面通常也会闪闪烁烁,色彩会显得更加失真走样。而正在幻想的人会觉得自己陷入了高烧的迷梦之中。他们大多会遇见一位过世的人,或者至少会碰到一名预言者为某个谜题给出暗示,又或者——在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会得到一个阴森的预言,不过其中词句总是表达得神神秘秘的,因为预言师总会禁止大家把话说得清楚明白。
可是,我这里的一切显得那么真实。我并不觉得自己高烧发热,也没有发现周围有任何变化。这间漫画书店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店外的大街也一样,没有任何摇摇晃晃或者闪闪烁烁的感觉。整体色彩和平日里一样丰富多样,既有漫画书店的五颜六色,也有柏林市区普遍一致的灰不溜丢。现在的情况也和谜题或者阴森的预言一点都不相干,眼前提着剑的这位斗士只是想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思来想去,这场景都不像是幻觉。
如果排除了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剩下的就是真相了,不管它有多么难以置信——福尔摩斯虽然这么说过,但这位聪明人可从来没碰到过我这种状况啊,他顶多就是和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及莱辛巴赫瀑布做一些斗争而已。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剩下的就是真相了,即使它非常不可能。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我面前站着的正是雷特罗·冯·阿曼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