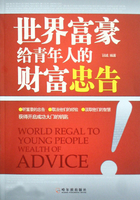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领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1944年6月6日而非两周后发起诺曼底登陆。做这个决定有很大风险,因为有件事会导致这个决定失败,而且发生的概率非常大,那就是如果6月7日的天气状况使支援部队无法登陆,那么前一天登陆的军队就可能不得不退到海上。但是决定延迟登陆也有另一种风险,那就是德国人会发现盟军计划登陆的位置。因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权衡所有风险,在其中做出选择。仔细考量后,他得以理清思路,判断出哪种选择能够让行动的成功率最大,这才做出最后的抉择。
领导者常常难以理清思路。近忧往往会影响一个人所做的决定,甚至不会让人去考虑长远的打算。一些决定本质上就有极大的复杂性,大量变数必须以某种方式呈现,这样领导者才能成功。如今,人类工程学家称之为信息超载的现象让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通过电子邮件、会议和电话,海量信息蜂拥而至、泛滥成灾,只会让领导者分心,令他思维混乱。或者,领导者接收到的信息七零八碎,于是就可能用假设填补空白,这就会导致有时候没有真正的理解。领导者的重大决定,从本质上来说,通常不是非黑即白的。相反,做决定的过程包括“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然后基于某种标准明确起主导作用的利益。如此思考的结果是个人的一种判断,带有主观色彩,就好比说贝多芬作曲比勃拉姆斯好”。
独处有助于理清思路。领导者只有通过努力分析想通复杂问题——就像艾森豪威尔在登陆日之前所做的那样——才能明确解决问题所需的必要条件;只有平息周遭喧闹并滤去内心嘈杂,才能听到直觉微弱的声音,而直觉的潜意识思维可能已经发现了意识思维尚未发现的关联;只有清楚自身劣势,才能扬长避短。
独处也带来别的益处,是一种更加务虚的收益,但重要性同样不打折扣。最好的工作是受灵感启发的工作。善于反思的领导者不仅会问自己应该做什么决定,而且会问自己的行动是否能够促进某种更大目标的实现。登山者不仅是为了爬山而爬山。教师能教给学生的不仅只有课堂上的内容。特殊需求儿童的父母或许能从孩子和自己努力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深刻的意义。最能鼓舞士气的领导者是那些发现了超越手头任务的清晰意义的人。而这种意义就来源于深思熟虑。
清晰的逻辑分析和清晰的直觉判断两者的基础都是清楚的头脑。比尔·乔治(Bill George)介绍了一种让头脑清楚的方法。乔治是美敦力公司(Medtronic Inc.)一位非常成功的CEO,也担任过其他高管职务。他现于哈佛商学院任教,著有畅销书《真北》(True North),书里他建议领导者认真思考自己的核心价值,以此来给自己指明方向。
“有效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元素不是优先做紧迫的事然后再做重要的事。”乔治说,“今天人们过于强调紧迫的事了。这对领导者来说一直十分不利。”乔治强调,深思不只针对内向者而言。“我非常活跃、外向,很有干劲。”他说,“三十几岁的时候,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有了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但这段时间他每天回到家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每晚都加班到七八点,回到家后吃晚餐、看杂志,然后就头昏脑涨地睡着了。”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起,乔治开始每天冥想,尤其是超觉冥想(禅修的一种手段)。他说:“我不知道超觉冥想为什么会有用,但确实有用。冥想的时候你会慢下来,静静深思。这其实是一种内省的过程,这是令一个人放松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超觉冥想的过程很简单。修行者(即冥想的人)最好每天冥想两次,每次20分钟,一次是一天的工作开始前,另一次是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即使每天做一次也比不做要好得多。每次冥想的时候,修行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祷语”上,并在脑海中一遍遍重复。祷语通常是一个字,没有硬辅音,对修行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含义(比如“Ayam”)。
然而修行者在实践过程中通常发现注意力会经常偏离祷语,转向貌似自己蹦出来的各种思绪。这些思绪通常关乎最近能引发修行者情绪波动的事情,比如让修行者感到满足、骄傲、快乐的事情,但更多的是一些令人感到焦虑、担心或害怕的事情。
当注意力转向消极思绪的时候,修行者的心率就会加快,而且可能真的会觉得紧张感贯穿全身。但集中精力想着祷语,同时任由注意力转向郁结于心的紧张情绪产生的思绪,这一过程不失为一种纾解消极思绪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情绪的方法。这个过程被修行者称为“净化”。
在冥想中消耗的时间多少要看修行者开始冥想时情绪有多激动。乔治说他的“思绪通常在10到12分钟后就稳定下来”。净化过程结束后,修行者感到平和、镇定。独处的过程中产生了洞见,也就是直觉,有时候往往冥想还没结束就已经在脑海里清楚地显现了。
之后修行者就能把精力集中到他想关注的事情上了,此时他心中一片清净。冥想增强了领导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完成冥想后,事情似乎明朗了。”乔治这样评价自己的冥想过程,“然后我随手拿了一张纸,把我的想法写下来”。
彼得·克劳福德(Peter Crawford)是个博学多才的隐者,他通过很多方式进行独处。彼得是土生土长的加州北部人,从耶鲁和斯坦福商学院获得了学位,曾在麦肯锡公司任职,目前在嘉信(Schwab)理财公司担任高管。“对我来说,独处带来很多好处。”他说,“有认知上的,情感上的,精神上的,以及身体上的。”成长过程中,他在几个“关键时刻”都寻求过独自思考。“一天晚上在高中学校里,我被申请大学的事搞得筋疲力尽。所以我骑上自行车来到要塞公园(Presidio)。我在黑暗中骑了一小时。我只想离开。”到了耶鲁大学,大四前的那个暑假,彼得的同学都在贝恩(Bain)和高盛(Goldman Sachs)实习,而他却在华盛顿州偏远地区当护林员。“我在理清思绪,想清楚我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我需要清晰的思路。”
在嘉信当高管的时候,彼得每天都会习惯性地独处——虽然他说“你不说我其实都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每天早上彼得在5点醒来,锻炼身体,然后早早去上班。“每天第一个小时最适合思考。”他说,“在晨光中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就好像把电脑上所有访问记录都清除了一样。清空后,我的大脑就能更好地运转。”
彼得在家附近夜跑的时候也能理清思路。他这种做法类似于佛教的“行禅”,修行者不用凝神想某个祷语,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行走这项运动上——抬起一只脚,再抬起另一只脚。彼得跑步的时候头上戴了照明灯,以便于看清前面的路。“没有音乐,没有耳机。”他说,“我把自己放空,把头脑中的东西清空,只想着自己的步伐。”
莉莎·霍华德(Liza Howard)也是通过长跑来厘清思绪的——她每次都跑很远很远。莉莎是全球顶尖的超长距离马拉松赛跑运动员,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并多次获得100英里跑冠军。(她个人最高纪录是跑100英里用了15小时7分钟,每英里花9分钟。)她一般会穿越得克萨斯州西南部的丘陵,道路崎岖,沿途可看到橡树和刺柏,或仙人掌和龙舌兰。
莉莎所说的跑步的作用恰恰正是比尔·乔治所说的冥想的作用。“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她说,“剥离掉日常生活的琐碎,留下重要的东西。”不过跑步的过程不同于冥想:“大部分注意力都消耗在运动上,剩下的注意力就容易聚焦到所想的事情上。”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运动与思考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他说,“把紧张情绪化解到体育活动中,能使思维清晰。”
独处能使思维更有条理,而这反过来可以促进逻辑分析的能力。彼得·克劳福德用给自己写备忘录的方式来理清思路。“我的备忘录通常是不给别人看的。我只是有条理地收集自己的想法而已。”他在麦肯锡的时候就这么做了。“那里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思路是否清晰。”他写备忘录的时候会沿着一条主线:“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我们将会遇到的挑战——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彼得用来分析情况、困难和解决方案的逻辑模式。
在家中,彼得是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也用同样的方式理清思路。“我写育儿日记。”他说,“刚开始只想记录美妙和感动的瞬间,方便日后回忆。但我渐渐意识到可以通过记日记的方式收集自己在育儿方面的想法,比如我们遇到的麻烦、面临的艰难抉择等。带孩子的时候,我们有过喜悦,也有过苦恼和怀疑,还会自我反思。”彼得往往在夜里写日记。“有时候我忙完就感觉累瘫了。但我会整理思绪,这样就有了新的见解,精力也恢复了。”
和彼得·克劳福德一样,萨拉·迪拉德(Sarah Dillard)也喜欢在独处的时候整理思路,让思维更有条理。萨拉是教育领域的创业者,曾在联邦教育部担任高级官员。她还牵头促成了孟菲斯市(Memphis)两大校区的合并,一个校区里大多是黑人学生,另一个大多为白人。时至今日,这场校区合并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不久前,她曾任四方教育(Quad Learning)高管,这是一家帮助社区大学提高毕业率的咨询公司。如今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SPD教育咨询公司(SPD Advisory)。
“对我来说,独处有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独处,一种是在大自然中独处。”她说。每天,她都步行15分钟去位于华盛顿的公司上班。“每天在上班路上,我都会对未来进行展望,而不是反思过去。我定下一天的计划,明确自己需要做哪些工作、完成什么事。”在工作中,她电脑上一直有个打开的文档,里面记录了一件件会导致情绪波动的事。“我把每个事项都用彩色标注。”她说,“绿色的是我感觉良好的,红色的是我感觉不好的,而紫色的则意味着我会以不同方式处理。”
每周三早上,萨拉会在家工作几小时,一个人静静回顾那些事项。“我把记下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反思我们团队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做成了?哪些没做成?我在了解团队的表现。”
在评价手下每个人的表现时,萨拉也遵循同样的方法——收集数据,然后反思。“我和每个同事一对一谈话。每次谈话之后,我就在谷歌便签里记录下我们谈了什么。每个季度我都回顾自己和每个人的谈话记录。在回顾的过程中,我会意识到一些自己之前没发现的事情,有时会注意到哪些方面做得好,有时也会意识到哪些方面做错了,需要道歉。”
萨拉还认为全公司都应当进行反思。“我无法想象一些创业者竟然不反思自身。”她说,“在初创公司里,你必须快速学习,否则是不行的。而反思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你第一次做的事情,处理方式有很多。但如果你只是耽于现状,不反思,你就永远都不知道其他的可能性,就无法了解到哪种方式是最佳的。”她也说:“在初创公司里,你会遇到很多‘未知的未知’,所以你要研究这些未知,从中学习,否则你永远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内特·菲克(Nate Fick)是畅销回忆录《一颗子弹的距离》(One Bullet Away)的作者。他在独处的时候既进行逻辑分析又用直觉思考。“在独处的时候才能理清思绪。”菲克说,“除非你只是回应别人的想法,而不是自己引领方向。”
菲克曾任海军陆战队侦察官,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服过役,后来在华盛顿一家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当过主席。他现在是网络安全公司安德伽玛(Endgame)的CEO。“我告诉助理,我每天需要90分钟时间关起门来独自思考。”他说。对手下员工也有同样的要求:“我告诉我的员工,每个月要有两天完全没有任何会议的时间,否则每天太过忙乱,就没有时间消化或思考。唯一的解决方法,除了像梭罗那样与世隔绝,就是创造独处的空间。”
菲克有办法打破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常规。“某种程度上,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会打扰我们。”他说,“我家书房里以前有个电话,上面有个闪烁灯。每次来电,灯就闪啊闪的,我觉得很崩溃。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话扔了出去,买了个20世纪70年代的旋转号盘电话机,于是再也不会被语音信息和闪烁灯打扰了。真是个极大的改善。”在户外,他也寻求独处的机会。“我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航行。”他说。他的帆船适合全家出游,又适合独自使用。“如果我不能单独出海,那要这条船干吗?”
菲克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直觉。“那些渗透进潜意识的东西变得具体,逐渐成形了。”这一过程通常在跑步时发生,菲克可以连续跑90分钟或更久。“我常常边跑边想,‘这就是我要搞清楚的事情’。于是我开始思考,虽然没两分钟我的思绪就飘到别的事情上。但几乎我每次跑完以后,我已经将注意力绕回到那件事上,并完成了思考。整个跑步的过程就是让杂念慢慢过滤掉的过程。”
彼得·克劳福德也有相同的跑步经历。“通常我正面临困难,比如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一场必须要做的演讲,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或一个必须做的组织决策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跑步。跑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刻意去思考难题,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主意或答案会突然蹦到我脑海里——要么在我正跑步的时候,要么在我刚跑完之后,总之我的头脑变清楚了。”
退役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也同样通过独处来获得直觉。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曾任多项要职,2009到2010年担任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2003年到2006年担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著有自传《我在部队的职责》(My Share of the Task)。他是讲领导力的书《赋能》(Team of Teams)的合著者,同时还是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一家咨询公司麦克里斯特尔公司的成立人之一。
“独处对我来说只是提供思考的机会。”他说,“我不需要在很安静的地方,只需要在能够集中注意力的地方就行。”在被派到中东的时候,他经常在空中寻求独处时的宁静。“开直升机特别适合思考怎么做决定。我戴上耳机,没人打扰,不用收邮件,只要一直看着沿途脚下棕色的地面就行。心无旁骛。”运动的时候他也能找到独处的空间。“我不和别人一起跑步,也不和别人一起锻炼。”
麦克里斯特尔将军说:“技术改变了领导力。如今有了电子邮件,要联系到领导者几乎没有什么障碍。我不想对别人无礼,而且回邮件让你感觉自己完成了很多工作。但是当你在回邮件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
他认为自己“不善于以第一印象评价别人。我只有运用直觉才能评价别人,产生直觉需要花一些时间”。他成为管理者时候做出决定的过程也是相似的。“有时我必须一步步考虑问题,只有独处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独处让我始终记得什么才是重要的。”直觉告诉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某个决定是否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通过聆听别人的想法,我确实收获很多。乍一听完,我可能会形成一个即时的反应。但我的价值观可能无法每次都对这种即时反应进行管理。所以我最好还是不要立刻做出决定。最好消化消化接收到的信息,然后再做出决定。”他说,“如果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会儿,那么我就会发现我又回到自己的价值理念了。”
“我当团长的时候,在一次作战前,我们用一晚上的时间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回忆道,“为此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也做了很多分析论证。然后我睡了几小时,醒了,才发现这个计划完全是胡扯。计划是在我的指导下形成的,分析论证也是在我的指导下做出的,但直觉告诉我计划错了。”
他的经历说明,直觉的产生需要精神上的宁静。“当时,我只是对外部刺激做出回应。但后来,我的价值观通过直觉占了上风。如果我感到某个分析或建议不太对,那么我会遵从直觉。这种直觉正是通过独处激发产生的。”
霍华德·普林斯(Howard Prince)也在非常棘手的情况下运用过直觉的力量。如今他是美国著名领导力学者,是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伦理型领导学“劳埃德·哈克勒”名誉教授。早几年当过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杰森领导力学院首任院长。此前他当过陆军军官,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在西点军校(West Point)建立行为科学和领导力系,服役28年后于1990年以准将身份退伍。
普林斯认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是两相情愿、相互依存的。领导者选择信任追随者,追随者也选择信任领导者。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军队里,你也不能对别人颐指气使。领袖必须转变自我,不要只当指挥官或老板,而要成为领导者。领导者会和追随他的人互动,让他们相信这个人是值得追随的,他去哪他们就愿意跟着去哪。”普林斯说:“独处能让领导者如虎添翼,但人们往往认为领导者必须要活力四射、非常外向的。而且人们也片面地认为多做就是好的,所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拿出行动来!’然而有时候更重要的事是停下来整理一下你的思绪。”
普林斯就是这么做的。当他还是军队上尉时,在一次战争新春攻势期间担任连长。三周前,对方军队打破停火协定,在春节假期进攻。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了夺回这座城,就在城内开展激烈的巷战。普林斯是“空中骑兵”营的一员(骑兵一般驾驶UH-1“休伊”直升机飞来飞去),2月初的时候,该营驻扎在这座历史古城西北约10英里处。空中骑兵营有4个连,每连125人。普林斯指挥B连,上级营长是中校吉姆·沃特,他是南卡罗来纳人,体格强壮,当列兵的时候曾参加过二战。沃特几天前才奉命接管普林斯所在的营,上一任营长在火箭攻击中阵亡。普林斯回忆道,沃特是个一流的领导者。“他与部下共担责任,并营造一种实话实说的氛围。沃特给自己挖散兵坑,还教我们怎么挖。他和我们一样经受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而且不等伤员全部撤离他是不会离开战场的。”
至于实话实说这一点,普林斯回忆起他和沃特的第一次见面。“他一大早就来了,全副武装。他走到我面前,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其实怕得要死,我想你也是吧。现在我们已经说开了,那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几天后,空中骑兵营在古城外遭遇了第一次战斗,然后普林斯的无线电接线员和旅总部连线对话,商量死亡人数统计,也就是估算一下交战中敌军死了多少人。“让统计死亡人数实在是可恨。”普林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杀了对方多少人。大家都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伤亡人员。当沃特听到我的接线员在和总部商量死亡人数怎么算的时候,他大步走过去,一把抢过电话,朝对方大吼:‘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滚!’这是非常关键的领导力行动。他在营造一种实话实说的氛围。”
2月5日,沃特的营收到命令,要徒步前往古城。“第一天我们就和对方交火了。”普林斯说,“敌军击落了一架休伊直升机。沃特让我去找机组人员。我们没找到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了。”2月7日,空中骑兵营到达古城西北约四英里处的通拉村(Thon La Chu)。敌军在林区边界击落了另一架休伊。沃特的营在林区里驻扎起来,这片林区叫作通寮古常(Thon Lieu Coc Thuong)。“树木是新种下的,才刚刚开始生长。”普林斯说,“在里面可以通行无阻。”在广阔干燥的稻田(“当时是旱季,没有种水稻”)东南300米处,是另一片林区,叫作通桂村(Thon Que Chu)。在通寮古常边缘的一个观察哨,美军看到敌军在通桂村一个大型混凝土掩体周围密集活动。“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在那里,但我们发现确实数量庞大。”普林斯说。
第二天,2月8日,沃特命令普林斯的连队在从稻田到通桂村的路上进行战斗侦察。“稻田非常开阔。没有可用来掩护或隐蔽的地方。”普林斯说。下午1点,他的部下呈一路纵队前往通桂村,他们在丛林中行动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穿过稻田时什么也没发生,但进入通桂村林区时,他们受到了三面伏击,先头分队的士兵都倒下了。沃特的部下谁也没有想到,敌军有一整个团埋伏在那里,兵力是沃特营的五倍。普林斯的部下当然寡不敌众,毫无胜算,他们花了三小时奋战终于甩掉了敌军,退回通寮古常。
四天后,2月12日,沃特营的另外三个连攻打通桂村,普林斯的连留下备用。“他们被击退了,无法突破敌人防线。”同时,美军和敌军日夜用迫击炮火拼。“感觉我们一直在被打。”普林斯说。单单一个下午,普林斯手下就有13名士兵被迫击炮击中。2月20日,普林斯的连里,除了他自己和一个刚到越南两周的少尉,其余军官全部阵亡或负伤。
2月20日下午,沃特把手下的连长聚集到一起,向他们简要说明第二天的进攻计划。“我们收到的命令是拿下敌军阵地——不惜一切代价。”沃特告诉他们。副营长、少校查理·巴克驾驶小型侦察机在敌军阵地上空侦察后制订出进攻计划。这个计划非常复杂:三个连从不同方向攻打敌军,普林斯的连打头阵——该连人数由于伤亡已经损失一半。此外,普林斯的连不是呈一路纵队穿越稻田,而是肩并肩形成横排,其中两个排在前方推进,另外两个排在后方抵抗敌军的火力压制。然后,后排机动至前排,原先的前排抵抗火力压制,如此交替前行。一旦沃特的营进入林区,另外两个营就会前来支援。
那天晚上普林斯把四个排长叫到一起,向他们介绍这个计划。一个排长就是那个新来的少尉,另外三个排长都是中士,因为之前指挥这几个排的少尉要么阵亡要么负伤了。普林斯告诉他们第二天早上要采取的行动,然后解散。那时正是傍晚。
不一会儿,那名少尉回来了。
“长官,他们不照办。”他说。
“你说他们不照办是什么意思?”普林斯问。
“他们就是不肯照办。”
想到这里,普林斯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他们不肯照办是什么意思?这个计划在战术上天衣无缝!而且合情合理!’”普林斯把少尉打发走。“我简直火冒三丈。但我其实很害怕,只是这种害怕以愤怒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我想跑过去朝他们发一通火,但不知怎么的,我控制住了。”
那一刻,普林斯面临领导力的终极危机。“我扪心自问:‘你现在要做什么,上尉?’我的训练或实战经验没法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而且有两样东西妨碍了他清晰地思考。一个是情绪干预:像普林斯一开始那样如此恐惧且愤怒是不可能清晰地思考的。另一个是支离破碎的信息: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排的兵就是不肯按照计划行事。
普林斯没有立即做决定,他选择一个人静静。“我独自怒气冲冲地在树林里走了半小时,就在我们营区范围内。黑夜慢慢降临。我试着整理思绪。”普林斯试图分析问题,但他分析不出来。“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想了一个可能的原因,然后又想了一个。没有一个说得通。”最后他的怒气渐渐消散了。普林斯换了一种方法。“我让思绪沉淀下来,让我自己自由思考。”最后,他平静下来,一个直觉浮现了。“我需要和他们谈谈。好好谈谈。不是朝他们大声嚷嚷。不过我还是不知道去了他们那里具体该怎么做。”
普林斯去了那名少尉带的排。所有士兵以及那个少尉都低着头。“没有人与我对视。”
普林斯开口了:“我说,你们怎么了?”
刚开始没有人回答。后来一个士兵说:“长官,我们在想明天你是要让我们都去当炮灰,这样你自己好得到荣誉勋章。”
普林斯大吃一惊。“你什么意思?”
“长官,我们以前从来没这么行动过。”
普林斯回忆道:“现在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效实施领导力的第一步是了解你的受众,在那一刻普林斯了解了他的部下。“他们习惯了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敌人,以一路纵队行进。每个人除了先头侦察兵外都感到相对安全,我们每30分钟换一次先头兵。而对于我们第二天要做的行动,他们没有受过战术上的训练。排成一行穿过开阔的稻田,这个主意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朝敌军阵地行进的每一步都岌岌可危。”“我蹲下来,在泥地上画出我们明天的战术。我们在2月8日遭到伏击就是因为排了一路纵队。我跟他们解释说明天的方案是最好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打到敌军阵地。”
普林斯的部下站在那儿听着,看着他在泥地上画出作战计划图。一些人互相看了看对方。最终其中一个人代表整个队伍开口了。
“好的,我们会照做的。”
普林斯解决了问题,第二天他的部下成功拿下敌军阵地(普林斯本人在战斗中几乎受了致命伤,后来在美国一家医院住了七个月)。“所以还要回到两相情愿、相互依存这个关系上。”普林斯说,“问题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我需要引导他们,而不是命令他们。”在越战中,有时候,如果士兵觉得长官无能或好高骛远,要让部下都去送死,那么这个长官会“被弄死”:有人会半夜把手榴弹扔进他的帐篷里。普林斯说:“如果我做得过火了,朝他们大吼大叫,以上级身份压他们,我相信我肯定会在进攻前一晚遭到报复。”
领导者应该努力让自己头脑清晰,不仅要清楚了解所面临的挑战,也要清楚地认识自我,知道自己有哪些强项和不足。内特·菲克认为“自知之明和自我意识是有区别的”。菲克认为,应该警惕自我意识,这是一种外向的思维,会导致装腔作势,让我们以别人的看法来做出决定。而自知之明是需要培养的,自知之明就是对自身力量的认知,这种认知决定了领导者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会如何理解以及采取何种做法。这种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内省的思维,通过长时间思索,领导者可以获得洞见。因此,菲克说:“我认为独处对培养自知之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获得自知之明的另一种方式是使身体受苦。“痛苦能打开人身体潜能的大门。”超级马拉松选手莉莎·霍华德说,“身体上的痛苦让你低到尘埃里,让你卑微。你在苦难面前无处躲藏。你必须决定你是谁,你要做什么。”彼得·克劳福德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从小就爬山。”他说,“爬到高处,你就会觉得自己洗尽了日常生活的铅华,让你返璞归真,你也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本性,然后加以锻造。”
获得自知之明的另一种方式是反思。比尔·乔治在哈佛商学院教导研究生要“咀嚼你生活中的故事。你需要反思生活带来的考验,反思自己是如何应对的。这些经历可以让你了解自己的性格,知道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高”。
内特·菲克将乔治的教导付诸实践。他对比了自己被派到国外执行公务后的两次回国旅程。“任务结束后,我们坐飞机回家。从出发地回到洛杉矶只要72小时。我们没时间来消化变化,难以调整自己。”但是另一次的回国旅程不同。“我们是坐船到那里的,也坐船离开。船很小,船尾有个给直升机用的飞行垫。船上有1000人,但是船的上层很大,我们可以一直待在舱外。我每天待在外面两三个小时,经常是独自凭栏。我们距离海面有50到70英尺。环顾四周,水天相接,遥遥在望。我们离陆地有1000英里。夜晚星空绚烂。这次回家之旅消除了我们的疲惫,令我们心旷神怡。”
菲克的海上之旅说明了领导力的精神层面。领导者从日常生活的狭隘中脱离出来,与某种超凡的目的或意义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有时候就是人与壮美自然的和谐统一。彼得·克劳福德在旧金山附近太平洋沿岸塔玛佩斯山(Mount Tamalpais)上的两小时越野跑中找到了这种共鸣。“那一刻我失去了自我。”彼得说,“我和周围的自然景象融为一体,返璞归真。”彼得每年独自背着行囊去山间旅行的时候也找到了同样的共鸣。“我爱山的巍峨。”他说。四周重峦雄伟。“渺小的自我融入了伟岸崇高的自然。你感到离上帝很近。我其实不是特别虔诚的信徒,但我感到一种欲望,对神祇的渴望。我会有疲惫、透支、挫败的感觉——但是在大山里待了两天后,回去的时候我又精神焕发了。”
萨拉·迪拉德用她所谓的“在大自然中的独处”来重新找到与自我价值理念的共鸣。“我在大自然中做出的决定是最好的。”她说,“在城市里,有很多能量,其中有一些会侵扰你,让你始终无法接近自己的内心,比如你要完成什么目标,做出哪些成绩,给周围人留下了什么印象。”这些东西可以让人受到外部动机的驱使,以他人的看法来衡量自己的成功。“而在大自然中我遵从内心的召唤。”她说,“大自然令人敬畏,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她举了个例子。“我和一个伙伴创业,还在初创阶段,然后他不干了。我必须决定是否要独自继续下去,因此我订了去科罗拉多州的单程票,在博尔德市(Boulder)法拉提隆斯(Flatirons)山间一座小屋里待着,在那里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孤独。”她每天早上在小屋工作,下午则爬山六英里。“在科罗拉多,外部刺激更少了。但独处不仅仅是帮助减少外部的嘈杂,还有认知、情感、精神上的效果。就像别人去教堂做礼拜一样,我在山中独处也会带来同样的益处。而我获得的益处是永久的。我明白了如何正确认识我面临的问题。”最终,她意识到:“这个我以为能办成的项目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不可能成功。当局时感觉混乱,旁观时亦觉无从下手。”但是在攀登法拉提隆斯山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苏珊·凯恩用独处找寻提升领导力的方法。苏珊著有超级畅销书《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最近,她建立了安静革命公司(Quiet Revolution),教导全球的组织机构要让内向型的员工遵从他们爱思考的天性,这样组织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苏珊本人非常内向,有时候会觉得难以胜任高调的领导者角色。“我从没觉得独处的空间是刻意去创造的。”她说,“我只是自然而然去寻找平和的状态。”
苏珊说:“内向的人通常不想为了当领导者而当领导者。地位高、受人关注等都不是大多数内向者所关心的。当内向者成为领导者时,通常是因为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对他们真的非常重要。”她举了自己在安静革命工作时的例子。“我们开展了一个叫安静大使(Quiet Ambassadors)的计划,这些大使是热衷于传播我们的理念的人。我们向他们传授理念,教他们如何把我们关于内向者力量的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我们公司对组织机构和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让我非常乐意去做这份事业。”
莉莎·霍华德在2011年5月的长跑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当时她在听关于超级马拉松跑者迈克尔·欧文的广播,广播里说他刚刚建立起一个叫红白蓝团队的组织,旨在通过体育运动和社会活动帮助退伍老兵融入集体。迈克尔的话让莉莎萌生了建立老兵越野跑营的想法。那时,莉莎和丈夫刚搬到圣安东尼奥市。“圣安东尼奥是个大城市,没有大型户外团体,我感到很孤单。我也没几个朋友。”所以她觉得,建立一个由红白蓝团队赞助的越野跑营“可以把大家都聚到一起”。“长距离越野跑有个传统,年长、更有经验的越野跑者向新手传授知识。年长者会告诉新手长跑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情况。”老兵越野跑营“可以让老兵融入我们的集体,让大家交朋友”。
但是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不知道谁会来,他们有什么能力,但是我们需要弄明白如何兼顾不同健康状况的人。一些人不能跑太远,但我们也不想给那些善于跑步的人造成限制。我们也必须弄清楚在一周内可以教会人们什么。”莉莎自己跑了几次长跑后,得出了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考虑清楚了其他困难。“我想要达到思路清晰的状态。”她说。
今天她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她在得克萨斯州罗克斯普林(Rocksprings)建立了雄鹰营(Camp Eagle)。“这是原来在山区乡村的教会营。”她说,“最近的镇离这里45分钟路程。没有电话,要上网也很不方便。”所有营友被分成四组,“根据健康状况和跑步能力,他们在原有的宿舍里休息,12人一间,大家都在大起居室里吃饭”。雄鹰营每年在10月的一个周末开办,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一中午。通常有约50名老兵参加,他们不需要花钱,还有几十名群众付费参与,再加上几十个志愿者。
志愿者指导员——被称为导师,都是资深越野跑者。“我们每年都向导师发出邀请,还没有人拒绝过。”参与者需要学习专业跑姿、场地礼仪、急救、受伤预防、营养、体温和水分调节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莉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想到的。雄鹰营带来的好处超越了跑步本身。一方面,通过参加活动,参与者能获得一种体验独处的方式。另一方面,“营友之间互相交流联系,与导师交流联系。大家都融入了一个集体”。莉莎认为,这与红白蓝团队的使命相呼应。“活动结束后,大家都满载着兴奋与喜悦而归。”
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自由攀登运动员”。在自由攀登中,运动员徒手徒步登上山岩——通常是一座悬崖,途中依靠裂隙和突出的岩块来稳定自己或借力蹬离。登山者身上系根绳子,是为了在摔跤的时候不至于跌落。现年37岁的考德威尔16岁时就赢得了人生第一个国家登山冠军。独处是他人生的中心。“独处对我的意义在于让我静静地把生活的碎片编织到一起。”
在独处中,汤米重拾了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中一条是强烈的共情心理。“独处让我的心变得柔软起来。”他说。正是这种心态让汤米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寻求独处的慰藉。“我人生中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独处中做出的。所以如果我正面临重大抉择,我就会创造独处的机会。”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决定要成为大岩壁攀登运动员。这个决定是在开了17小时车后做出的。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大岩壁攀登运动员,但这段旅程结束时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不是汤米自己选择的。21岁,正当汤米攀岩生涯要走向巅峰的时候,他在一次意外中不慎用台锯割掉了自己的左手食指。这次受伤威胁到了他的职业生涯:攀登运动员向上攀爬的时候要经常使用手指,尤其是食指。“医生把断指接上了,并试着激活。但接下来几天,它变黑了。”最终医生告诉汤米需要把断指截掉,他再也不能爬山了。“我悲痛欲绝。”他说,“接下来四天,我在医院里回顾自己的人生。小时候我是个小矮子,手眼不协调。登山是我觉得适合自己的第一件事。然而现在我觉得我可能再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了。”但是他慢慢坚定起来。“那些日子,在反思中我意识到登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形成了一种将登山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虽然很盲目,但是我决定不管那么多。”五个月后,汤米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伊尔酋长岩(El Capitan)自由攀登了3000英尺的萨拉瑟壁(Salathe Face)。
接下来几年,汤米成功登上了伊尔酋长岩上几乎所有的岩壁,除了一面黎明之墙(Dawn Wall)——这座墙由表面光滑的花岗岩构成,几乎垂直于地面,被认为是自由攀登者无法登上的。但2007年末,在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后,汤米开始考虑攀登这面墙。“我的生命中有个空白。攀登黎明之墙可以帮助我填补空白,这是我决定实现的目标。”汤米2010年首次尝试攀爬黎明之墙。当时他和凯文·约格森一起攀爬,凯文非常强壮但经验不足。他们失败了。接下来四年,两人又尝试了四次,但也都失败了。
2014年12月27日,他们又尝试了一次。这时他们的事迹已经引起了全国关注,一个大型媒体代表团到现场去报道。和前几次一样,两人把3000英尺高的墙面分为32“层”,他们的目标是登上全部32层,中途不得返回地面。如果一人在一层跌落——会先往下掉50英尺然后被绳子吊住——他就必须从头开始。白天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攀登。夜晚他们睡在一个6英尺长4英尺宽的“单点吊床”上,距地面2000英尺高,用尼龙绳拴在陡峭花岗岩墙面的支点。每天一个攀岩运动员朋友通过绳索上升1200英尺给他们送水和补给,汤米或凯文用滑降下去跟他碰头。
攀岩过程开了个好头:头6天,两人都顺利登上了前14层。之前他们从没超过12层。虽然进展顺利,但汤米总感觉他们无法到达目的地。“在上面的时候媒体把我们团团围住,闹哄哄的。”摄像师从山顶悬吊下来,拍摄两人的一举一动。更要命的是,在伊尔酋长岩,汤米和凯文手机有信号,还能上网,所以汤米觉得有义务要每天发推特动态报告进展。他很讨厌这样。“我真的很懊丧,因为手机让我们如此分心。”他说。前一年,汤米和另一个朋友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攀登了5天,当时没有手机信号。“阿列克斯和我在攀登的时候全情投入。”他说,“很奇怪为什么这次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分心了。我们没有在思考攀登的意义。”
然后凯文遇到了大麻烦。接下来7天,汤米成功登上15到20层,但是凯文在攀爬15层的时候跌落了10次。“我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凯文,白天爬山的时候指点他,晚上休息的时候在吊床上探讨。”凯文尝试攀爬15层的第6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而这场意外预示了事情的结局。“那天晚上我回到我们的吊床。”汤米说,“凯文刚完成一系列尝试,已经心力交瘁。我把我们的手机放在前胸口袋,往绳子上夹些东西,一边对凯文的失利十分心痛。我探过身子去捡东西。然后意外发生了:手机从口袋里掉出来,掉到2000英尺下的岩石上摔得粉碎。”原来他忘了把口袋拉链拉上。汤米的第一反应是:“糟糕!”但他马上想到:“这真是太棒了!现在我可以全心投入到这场非凡的体验中了。”
两天后,1月9日,凯文成功登上15层。从那层开始,两人都精神焕发地向上攀登。“没有了手机,我就可以坐下来静静思考。”汤米说,“每天只有几个小时适合攀爬。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2000英尺的高处看着群山,思考攀登的意义。独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我来说是精神力量。”
四天后,两人都成功到达32层,并登上顶峰。“在高处的吊床上思考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比到达顶峰更重要的是情感共鸣。”汤米说,“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这就是攀登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