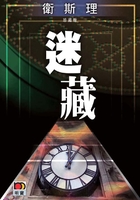献给夏洛塔
“再来说说我的这个新同伴,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
丹尼尔·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
从上路之后,艾德一直处于极度的警醒状态,在火车上他根本睡不着。火车东站在新的列车时刻表上已经改叫火车总站,这里的两盏灯,一盏挂在斜对面的邮政大楼前,一盏悬在车站大门上方,那儿停着一辆货车,车没有熄火。这种夜晚的空寂完全不符合他对柏林的想象,不过话说回来,他对柏林又知道多少呢?不久后,他就返回了售票大厅,拣了一个宽阔的窗台蜷缩着躺下。大厅里一片寂静,从他躺着的地方,外面那辆货车发动时的嗒嗒声清晰可闻。
他梦到了一片沙漠。从天际飘过来一头骆驼,悬在半空中,被四五个阿拉伯人拽着,看样子拽得挺吃力。这几个阿拉伯人戴着墨镜,对他不理不睬。艾德睁开眼睛时,看到一张被雪花膏涂得油亮亮的男人面孔,脸凑得太近,让他一下子竟没法看清这个人的模样。这是个老头儿,嘟着一张嘴,像要吹口哨,也像是刚刚吻过谁。艾德猛地向后一缩,像是刚吻过谁的那个人举起双手。
“哦,对不起,对不起,很抱歉,我……真不是要吵醒您,小伙子。”
艾德用手蹭蹭濡湿的额头,把自己的东西扒拉到一起。老头儿散发着一股芙蕾蓉娜牌雪花膏的味儿,棕黑色的头发油光锃亮,纹丝不乱地梳在脑后。
“就是有件事,”他尖锐的小嗓音开腔说,“我正在搬家,东西很多,现在已经晚上了,大半夜的,已经这么晚了,真是麻烦,我的家具里还有一个柜子,特别好、特别大的一个柜子,还放在外面的马路上……”
艾德坐起来的时候,老头儿用手指着车站的出口那里。“就在附近,我住得一点也不远,不要害怕,离这儿就四五分钟的路,拜托,谢谢啦,小伙子。”
他差点就把老头儿的话当真了。老头儿的手拽着艾德拖吊得长长的毛衣袖子,像是要给他引路。“来吧,拜托啦!”说着,老头儿在他的毛衣袖子里慢慢向上拨弄开一条通道,悄无声息,仅在面团一样虚软的手指尖活动范围所及之处,后来,艾德感到手腕处温柔的、画着圆圈的抚弄。“你是想来的……”
艾德推开老头儿,几乎掀翻了那个人,他用的力实在是太大了些。
“问问总成吧!”刚刚吻过谁的人尖着嗓子说,但是声音并不大,咝咝的,几乎听不见。他的踉踉跄跄也像是装出来的,仿佛一小段熟练的舞蹈。他的头发滑到了后脖颈上。艾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倒是被突然露出来的秃脑壳吓了一跳。那片脑壳就像一个小小的、未曾见过的月亮浮在昏暗的售票大厅里。
“抱歉,我……现在没有时间。”艾德把“没有时间”说了两遍。急匆匆穿过大厅的时候,他发觉犄角旮旯里随处都有些怯生生的人,一边试图用微小的信号引起别人的注意,一边又像是在努力掩饰自己的存在。其中一个人举起个棕色的尼龙袋子,指指那个袋子,对他点点头,那张脸热情得一如正准备派发礼物的圣诞老人。
铁路餐饮公司的餐馆里有股肉的焦煳味儿。玻璃餐柜的灯管发出细微的、仿佛歌唱般的声音。空荡荡的餐柜里只剩下保温盘上放的几碗俄式蔬菜肉汤。肉汤上面结了一层油膜,里面几块油乎乎的香肠和黄瓜如同矗立的礁石,在不间断涌来的热浪中微微地浮沉,仿佛正在工作的内脏,或者,艾德心里想,像生命行将结束时的脉搏跳动。他不由按住了自己的额头:或许,他还是跳下去了,这一切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铁路警察走进餐馆,头盔上半弧形的窄帽檐闪闪发亮,身上的制服是矢车菊的浅蓝色。他们牵了一条警犬,警犬低着头,仿佛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害臊。“请出示车票、证件。”不能证明自己还要继续乘车的人必须马上离开餐馆。脚步沙沙,推椅挪凳,几个好脾气的醉鬼仿佛专等这句最后通牒似的,一声没吭就摇摇晃晃走出了餐馆。两点钟时,铁路餐饮公司的车站餐厅几乎损失了所有的客人。
艾德明知道不应该做那种事,但他这时还是站起身,去拿了一杯别人喝剩的酒,站在那里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桌旁。这是第一步,艾德心想,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他把头埋在胳膊里,在旧皮子的霉味里一下子就睡着了。那几个阿拉伯人还在费力地拽着那头骆驼,但不是朝一个方向,朝哪儿拽的都有,看样子他们的意见完全不一致。
那个被举起的尼龙袋子——艾德之前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在火车站过夜。尽管他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柜子并不存在,但眼前还是出现了老头儿放在马路中间的那件家具,让他感到抱歉的不是那个老头儿,而是从现在开始和这件事挂起钩来的东西:芙蕾蓉娜雪花膏的味道,光秃秃的小月亮。他看到老头拖着脚步走回柜子旁边,拉开柜门钻进去睡觉,一时间,艾德仿佛感受到老头如何蜷起身子,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那感觉非常强烈,竟让艾德产生去跟他躺在一起的想法。
“请出示您的车票。”
他们这是第二次查他了。或许是因为他的长头发,或许是因为他的打扮。他身上那件沉甸甸的皮夹克是舅舅留给他的遗产,五十年代的那种摩托车手夹克,非常显眼:巨大的翻领,柔软的内衬,还有硕大的皮扣。懂行的人买卖时把这种夹克称作台尔曼[1]夹克(这个名字并没有贬义,而是带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或许是因为这位工人阶级的领袖在几乎所有老的影像里都穿着类似的皮夹克。艾德还记得那些影像:人群的涌动奇怪地一顿一跳,台尔曼站在台上,上身一顿一跳地前后摇摆,拳头在空中一顿一跳地晃动。每次看到这些老的影像,他总是身不由己,不能自已,不觉就泪流满面……
他费劲地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德意志帝国铁路的大字下面,几个细线框分别框着目的地、日期、价格和里程数。他的车是3点28分的。
“您去波罗的海做什么?”
“看朋友。”艾德重复道。那个铁路警察这次什么也没说,他于是补充说:“度假。”不管怎样,他的声音是沉着的(台尔曼式的声音),尽管他自己当下就觉得这个“度假”很牵强,站不住脚,简直就是愚蠢至极。
“度假,度假。”铁路警察重复道。
那是一种口述机要的声音,他左胸前用皮带拴着的灰匣子一样的步话机马上轻轻发出了嗞嗞声。
“度假,度假。”
显然,这一个词就足够了,他们想知道的有关他的事尽数包含在里面,他的所有弱点和谎言。所有与G有关的事,他的恐惧与不幸,他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开了十三次头写就的二十首笨拙的诗,以及连艾德自己都还不太清楚的有关这次旅行动机的所有真相。他眼前出现了警察局,铁路警察的办公室,远远地在空中的某个地方,架在仿佛钢梁铁架一般的六月夜之上,那个铺着地毡的玻璃匣子一尘不染,正从他内心无边无际的不安中穿行而过。
他感到非常疲倦,平生第一次,他有了逃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