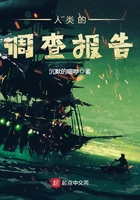6月9日的清晨下着微雨,今天天亮得比往常晚,暗沉的天仿佛让人怎么也睡不醒,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睡眼惺忪中。山路潮湿却不显得泥泞,黑色的土地还很松软,一脚踩过去就会陷下去一个不深不浅的脚印。
零零散散的水滴顺着松针滴落,落在三对大小,深浅都相同的脚印里,六只脚的人?
茂盛的草丛中,三个背着竹篓的身影行走在一条由人踏出来的小路中,发黄的斗笠和老旧的蓑衣,军绿色迷彩劳保全套,手套倒是白色的,上面染着点点污渍。
付家三兄弟行走在祭奠母亲的路上,在这个朦胧的山林中时隐时现。
顺着回环曲折的阶梯往上走,汉白石砌成的公墓死寂,肃穆,不过比起山路倒是亮堂不少。
斩洋:“大哥,有人来的比我们还早呢?”都说瞎子耳朵灵。他虽听不见,眼神却极为敏锐。
走在最中面的斩朝没有回答,他知道他说什么他那个二弟也听不见,但其实他比斩洋更早发现那个人的存在,毕竟在这样的环境,耳朵可能比眼睛更有用。
三兄弟跨着一致的步伐一阶又一阶,在这雨天格外的沉重。斩隆“一言不发”。
细雨划过他银色的发丝,流过高挺的鼻梁,脸颊,淡薄的嘴唇,滴落在汉白石板上。
水滴在银色发丝上流连,闪烁着圆圆的亮光,灰色的眼眸空灵又神秘,几颗水星挂在他的睫毛上,沉重了他的眼皮。
没有打伞,任由雨亲吻着,纯白的衬衫被完全打湿了,来了有一会了吧。
他一动不动得盯着墓碑,先父白振立,先母映江月。
另一边,付家三兄弟已经摆好了碗筷,斟好了酒。
“爸,今天是你忌日,我和斩洋,斩隆来看你了,您吃好喝好。”斩朝说罢便是一杯酒洒在墓碑前,三人有各上了三炷香。
良久,斩朝:“咱也去看看爹吧。”又背上了竹篓。
此时已不见那个身影,只留下墓碑前的两束白菊花。。。。。。
。。。。。。
舟海市石龙街两个打着小花伞的女孩在街道口跳着“下个路口见”,淅淅沥沥的雨丝打到伞面上,水潭里,溅起一个又一个小泡泡。
两人都是白色的短裙,一个露肩,一个露挤;一个头上戴着一顶白色鸭舌帽,一个头上别着珍珠发卡。
“淼淼,玉姐买奶茶怎么还没回来?”露挤的女孩说。
露肩女孩:“再等等吧!”
终于,一个一头大波浪,身穿黑色吊带的女子从前面路口的拐角处走来,紧身牛仔裤包裹着她修长的腿,黑色的高跟鞋十分精干。
“你的金桔蜜柚,”把奶茶递给杨伶俐,“还有淼淼的芒果布丁!”
接过喝了一口,“有姐姐的味道,玉姐买的就是好吃。”张淼淼说道。
凌雁玉只是温柔一笑。
“妈妈的味道!”
伶俐的声音让凌雁玉有些紧张,她是发现了什么吗?
“很幸福!”
凌雁玉松了一口气,吸了一口手中的北海道奶茶。当然妈妈的味道指的是奶茶的味道还是。。。。。。就无从而知了。
蜘蛛巢红背区一户独门独户的小院子里
一位老妇人端坐在阳台上,手里织着一件红毛衣,就差一个领子就完工了,老人有些发福,手指粗短但极其灵活,麻利得一针又一针,显然深精此道。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绵绵细雨,今天的阳光很暖,清新又明媚,照在老妇人微笑着的脸上。她脸颊上的浮肉有些塔拉,眉目温和,浅浅的月牙眉,很可爱。
但是谁又能想到这竟是这蜘蛛巢之主“血蜘蛛”夫人,臭名昭著的老鸨。
阿蛛站在她后面,鼓起勇气:“奶奶,小丑先生,还有蚂蚁先生。。。。。。”
老妇人没有理她,只是慈爱得看了她一眼,继续织毛衣,就像蜘蛛吐丝那样慎密,疏而不漏。
依偎在老人身旁,良久,才道:“奶奶,我们换个地方吧!”
老人只是笑:“那我们住到哪里去啊,奶奶老了,走不动了。”她笑得很慈祥,很和蔼,就像普通人家的奶奶看到自己孙女一样开心得笑着。
阿蛛有些焦急,可不知道如何表达,她不敢说那天晚上小丑先生的事,她怕老人家担心。这几日小丑先生,麦麦,老板一如往常,可这分安静却让她跟显得慌张,她害怕,害怕这表明宁静,实则暗藏汹涌。想到年迈的奶奶,不禁有些潸然泪下。
血蜘蛛:“乖孙女,哭什么,别哭了。”说着伸手抹去孙女的眼泪,把她抱在怀中。
接着手握着阿蛛的左手,抬起,轻柔得抚摸着食指关节上那只黑色的黑寡妇说:“这里是蜘蛛巢,蜘蛛们的家,我们的家,从来只有我们赶走别人,哪有别人赶我们的道理。”说着也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同样的位置也匍匐着一只蜘蛛,黑色的,张牙舞爪,蜘蛛的背部有一道深深的红线,泛着血液流动的光泽。
“奶奶啊,什么都知道,让你去马戏团酒吧打工都是我一手安排的,蚂蚁也是我安排在你身边的,多和他亲近,他可是你这一代人的护道者啊,你留洋在外的姐姐身边也有一位蚂蚁跟随着呢。”血蜘蛛侃侃道来,“蚂蚁什么都跟我说了,乖孙女别怕,”有抹了一把阿蛛的眼泪,“在这蜘蛛巢乃至整个舟海市还没有人敢和我老婆子作对,那小丑也只敢吓吓你,终究上不得台面,在我的地盘谁敢伤害我的孙女!有蚂蚁跟着我也放心,小丑他还伤不到你。”老妇人眼眶布满皱纹,眼睛闪过一丝阴狠的光泽,但悄然而逝。看着孙女时,眼里只剩下温柔,只剩下温柔。
“你可是黑寡妇啊,是比奶奶的红背毒性更强的黑寡妇啊。”这是血蜘蛛最后所说。
阿蛛比起一半女孩是还是很高的,168的大长腿御姐一位在矮小的奶奶怀里,说不出的温馨。
阿蛛的心里却惊涛骇浪,她眼中的奶奶不过是一个收收房租,再给那些失足女提供工作平台罢了,虽不是光彩的事,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灰色地带太正常不过了,可今天,却彻底刷新了他的认知。
直到傍晚时分,阿蛛才离开奶奶的家,回到了黑寡妇区,换上衣服,戴上面具,马上就要上班了。
夜色降临,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墙壁攀爬者登上血蜘蛛夫人的阳台。
“妈,您找我。”黑影说。
“咱家的黑寡妇被那马戏团酒吧的老板欺负了,你说你这个做叔叔的天狼卫是不是应该去好好敲打敲打,嗯~”老妇人淡淡道。
没有再多说什么,默默俯首,一道黑影越出阳台悄悄隐匿于夜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