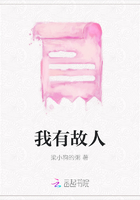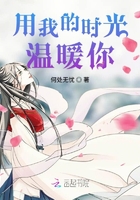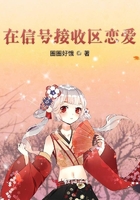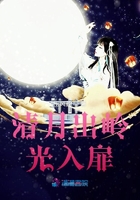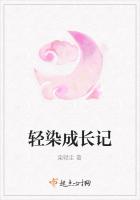——读《红楼梦》有感
读《红楼》,《红楼》是书,是戏,更是人间现世。看似写的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奢靡享乐,夹着官场的风谲云诡,有市井小民的辛酸无奈,实则更是人世的千红万紫和兴亡成毁。
年华是一篇骈俪词赋,我掌着日月这盏灯默默诵读。寒塘栖鹤影,冷月葬花魂。大观园中,闲来静处,将诗酒猖狂,逢时遇景,拾翠寻芳。花枝堆锦绣,鸟语弄笙簧。三五密友,沁芳溪旁,或琴棋适性,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因果报,或论些今古兴亡;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令世人百转千回、眷眷难忘的应是宝黛的前世今生,未了情缘,纵是山河动荡,春风失色,亦要涉水而行,与之相逢。初见那日,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却笑道:“虽然未曾见过她,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盛世山河,粉黛春秋,殊不知林黛玉的前世,乃离恨天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仙草,得赤霞宫神瑛侍者灌溉之恩,下世还泪,“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比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方有这段旷世绝恋。
带着还泪之说,她对宝玉,至死不渝。泪洒相思,焚稿断痴,魂归离恨。为情而生,也为情而死,世人皆道黛玉含恨而死,可她当真有恨吗?她为还泪来,如今债了却,不过是返回天界做回绛珠仙草,冷看人世烟火,过客往来,离合悲欢。
黛玉之美,在于她病如西施的柔弱之美。书中这样描述,“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绿竹幽雅,潇湘馆内整日药香弥漫,百草尝尽,依旧柔弱病骨,惹人爱怜。
黛玉另一种美,在于她浓郁的诗人气质。于她眼中,万物有灵,草木有情。她的菊,“孤标傲世携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不入俗尘,与世无争,她的咏絮词,一句“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读罢令人黯然神伤,似咏柳,写尽自己飘忽之身世,渺渺不定的爱情。她的《桃花行》《题帕诗》《秋窗风雨夕》《五美吟》皆意蕴深刻。诗如其人、文如其心。
而黛玉一生之悲剧命运,莫过于那《葬花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她以诗歌,低诉现实的无情,人世的薄凉,“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亦是在感花伤己,知自己最终的结局,不外是花落人亡,渺渺无踪。
黛玉最为绝代出尘的美,为叛逆之美。她一生向往自由,惧怕凡尘束缚,将自己沉醉在诗的境界里,愿爱所爱,喜所喜,薛宝钗却认为诗词不宜过于耽溺,莫要移了性情。那是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而林黛玉却用生命来爱文字。《五美吟》她赞扬红拂私奔之壮举;她读《西厢记》,欣赏莺莺追爱之勇气;她以《牡丹亭》中的词句引为酒令并为之神颠魂倒;她与被称为混世魔王的贾宝玉认作知己,同住同修,同情同心,共历风雨。
树对花,月对乡,戎马对红妆。天涯路,对咫尺荒凉。金玉良缘抑是木石前盟,前者是循规蹈矩的世俗,后者是离经叛道的爱情,其实贾宝玉早有判词:“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而薛林二人也早已批了宿命,一个是玉带林中挂,一个是金簪雪里埋。黛玉魂归离恨,宝玉遁入空门,携着他对世俗的最后一丝反叛,葬于世海荒径,古刹山林。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然红楼里描绘的悲情,不仅是悲金悼玉,也不只是贾史王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有那个时代的人文与政治交织的一种悲情。日出月落,起伏几轮。
年年祸不分,人人自分。岁岁情亦不困,人人自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许多人穷尽一生想要抵达那朱墙碧瓦的府邸,而身处其间的人,耗费半世华年,却走不出来。世间阴晴圆缺的故事,冷暖交织的悲喜,皆落其间,春夏是平,秋冬为仄,诺大的篇章,摆在历史的书案上,演绎了浮生世情,唱尽了光阴离歌,时光易老,繁华如戏。总要有曲终人散、盛宴离席之时。
沈复《浮生六记》中说:“看那秋风金谷,夜月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机关参透,万虑皆忘,夸什么龙楼凤阁,说什么利锁名僵。”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盛极必衰,慧极必伤,所谓大道至简,当是如此。
红楼中隐喻了浓郁的诗性气质,有佛家之空灵、道家之玄运、儒家之忧世,更融入了先秦的蒙昧高远、秦汉的古朴疏阔、盛唐的豪迈博大、两宋的婉约雅致。最后,“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渺渺红尘,漫漫河山,当真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中人,执于名利声色,执于营营利利,执于春风秋月,浩荡情场。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潇湘馆内那隐于绿竹深处的七弦该落满了尘埃,蘅芜院里的杜若萝薜可是牵藤引蔓,栊翠庵那年埋于地下的梅花香雪,是否还够煮一壶情茶?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曾经锣鼓喧天的倾城故事,声势煊赫的四大家族,随着金陵遗梦,被写成了对文,淹没于滚滚风尘,不知所往,半吟半唱,亦真亦假: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